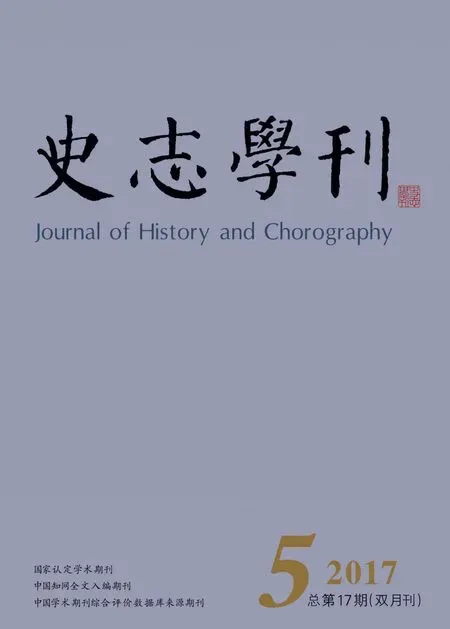中西方文化語境中“方”與“志”的比較研究
吉 祥
(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南京210004)
中西方文化語境中“方”與“志”的比較研究
吉 祥
(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南京210004)
地方志或方志可以分解成“方”+“志”。由于歷史上社會文化制度的不同,中國和西方社會治理結構的“方”有著不同的含義,在中國,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區性的“方”,在西方則表現為封建莊園采邑和教區性的“方”。地理大發現后,伴隨著殖民主義所產生的西方人類學民族志將視線轉向異國異族的“他鄉”“他方”,由此產生了各自相對應的實證記錄文獻。文章考察了中西方語境中“志”與“方志”的語言轉換和文化理解,比較了中國方志與西方地方史(志)、西方人類學民族志背后的文化生成機制及其特征特點,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全球化戰略,提出建立中國版人類學民族志,并提出適應走出去戰略的中國方志發展轉型,將相對于以中國為天下的“地方”志改造為相對于以世界為天下的“方”志,方志既要吸納人類學“走出去”的外向思維,也要吸納人類學“走下去”的田野思維,以此改造傳統封閉的地方志,增強方志的活力及其文化學術價值。
地方志 文化比較 語言翻譯 人類學民族志 全球化
一些從事方志史研究的學者認為,地方志是中國所特有的文化傳統,倉修良先生就轉引臺灣學者陳捷先教授的話稱,方志為“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項特有瑰寶”[1]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修訂本).方志出版社,2003.(P11)。除了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曾經存在過方志外,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是不存在方志這種文化形式的。既然是如同國粹般“特有”,那么中國的方志也就成了“自說自話”,別人只能當看客,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如此,地方志哪里還有國際文化交流的空間?
事實上,造成地方志難以進行國際交流的障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語境中對“方”與“志”的觀念及其語言轉換,“地方志”可以拆解為“地方”和“志”,漢語中的此類文化術語在西方語境中如何被表達,以及西方語境中的類似的術語如何用漢語表述。只有弄清楚中西方對這些術語的觀念及其文化生成機制,地方志的國際文化交流才能成為可能。
一、中國和西方歷史上對于“方”的不同觀念
以今天習以為常的觀念來看中國地方志,這里的“地方”已經基本被定型為國家內部中央以下的省市縣地方行政區,所謂的地方志基本是指地方行政區志。
但是,追溯漢語中“方”的語義本源,則發現中國古代的“方”原本包括了天方、地方、人方等多種空間內涵,而并不限指地方行政區。所謂“天方”,就是以天文星宿的方位來對應定位地上的地理空間。古代舊志中很多都有星野(分野)的內容,其“基本思想是在天上的區域與地上區域之間建立其對應的關系”[1]陳美東.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P735)。最初所謂的“地方”,原本是一種自然地理空間的概念。而“人方”則是方國和聚落部落的概念,如夏商周三代就有鬼方、土方、邛方、羌方、虎方、人方等稱呼方國和聚落部落的名稱。隨著秦王朝統一天下,原先建立在周朝分封制基礎上的分散諸侯國被中央集權制統一管控下的郡縣所代替,地方行政區逐漸成為“地方”的主體。社會結構呈現為天下=中央+地方(地方行政區)+四夷(邊疆社會),地方成為與國家、中央相對的概念。即便如此,國家內部不同自然地理區域、邊疆的少數民族區域以及域外等不同的地理空間的“方”依然存在,只不過被標以不同的稱呼,不是直接稱“地方”或“方”而已,而這一點往往在中國方志史上是容易被人忽視的一個領域。
而在西方,近代以前歐洲的社會結構背景長期是以封邑城堡為主的封建制和天主教、基督教為主的教區制,也因此,西方文化語境中的“方”或“地方”,帶有教區、封邑、城堡(城市、城邦)、地理區域等多種意義內涵,包括進入現代后,西方社會發展也主要是將城市化為主的城市作為地方認知單元。吉爾茨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識》中所講的地方性,既指特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又包含著特定的歷史文化條件所形成的立場、觀念和價值等,地方性就是地域性和非主流邊緣性,這是一.種相對于全球化、主流普遍性文化而言的地理和文化概念。由此可見,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地方”表現形式以及地方觀與中國以地方行政區為主的“地方”是有很大不同的。
二、中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志”及其語言翻譯轉換
作為一種文獻文本,“志”或“地方志”在中文語境中是一個特定的文化術語。志在不同的外延層面上,其涵義可作不同的理解。廣義上的“志”,泛指實證資料性文獻文本,相當于史。方志學的鼻祖章學誠早就作過“志乃史體”的論述,“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其意一也”,也就是說,不同層面的史書文本有不同的術語標稱,宋代史學家鄭樵在《通志·總序》中對其書名解說稱“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為紀,今謂之志,本其舊也。”“志者,記也”,可以包含各種表現形式和體裁編纂的資料文獻。2005年國務院頒布的《地方志工作條例》對地方志的定義是:“地方志,包括地方志書、地方綜合年鑒。地方志書,是指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地方綜合年鑒,是指系統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情況的年度資料性文獻。”不論是志書還是年鑒,其最后也是最本質的關鍵詞都是“資料性文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方志史上,在宋代方志定型之前,志就有地記、風俗傳、圖經、地志多種形式,即使在宋代方志定型后,志書仍然有“乘”“錄”“書”“鑒”等不同提法。“資料性文獻”是一種很寬泛的提法,為此曾有人就提出“廣義方志學”的概念[2]張尚金.開創廣義方志學之我見——張尚金文論集.珠海出版社,2007.。中觀意義上的“志”,特指以橫排豎寫的“志體”為主編纂的資料性文獻,但這一類稱“志”的未必就是方志,而是包括了國家總志、地方志、專志不同范圍的志書,如《抗日戰爭志》《汶川特大地震志》《北京奧運會志》《中國長城志》《中國大運河志》都是國家層面上的專志,嚴格地說它們并不是地方志或“方志”。狹義的“志”,才是針對“地方”主要是地方行政區而編纂的實證資料性文獻,尤其是以“志體”為特征而編纂的資料性文獻,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方志”。
近代以來,由于西方傳教士的進入和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文化了解的需要,中國文獻被翻譯傳入西方世界,其中對于“志”和“方志”術語的翻譯出現了多種情況。從廣義的志即記的層面進行翻譯,志就是一種實證記事、記載的文本,可以翻譯為record、history,那么方志就是local record、local history,如現在的《中國地方志》雜志的英文翻譯就是《CHINA LOCAL RECORDS》。西方史學界研究過程中,閱讀方志最多的何炳棣,也稱方志為“地方史”,使用的是Local history(地方史)。除此之外,還有四種翻譯,一種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漢英大詞典》中的翻譯為:方志:local chronicles,“chronicle”一詞的意思是“編年史”的意思,《朗文當代雙解詞典》上的英文注釋是:“a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s,arranged in order of times,without any judgment as to their cause,effects,nature,etc.”,意為“記錄的歷史事件,按照時間先后排列,對所記載的歷史及其原委、本質等不加任何的評論。”中央編譯局英文處對“方志”的翻譯也是使用“local chronicles”一詞[1]沈思睿.“地方志”英文該如何翻譯?上海地方志,2000,(6).。第二種是chorography,百度翻譯中作地志、地方志、地勢圖解。choro和graphy均來源于希臘語,分別指“地方、地區”和“書寫”。第三種是遠東出版社梁實秋主編《遠東漢英大辭典》中的翻譯:方志:a geographic account。從字面意思上理解,“geographic”是“地理的”的意思,“account”是“書面及口頭的報告、賬目”的意思,兩個單詞連起來的意思就是地理報告。第四種是local gazetteer,gazetteer這個詞有兩個釋意,一是地名詞典、地名索引,二是〔古語〕公報記者。大部分西方學者遵從19世紀的傳統將方志譯為Local gazetteer。在西方研究應用大量方志的ChangChung-1i用的是“gazetteer”[2]Alitto.中國方志與西方史的比較.原載臺灣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漢學研究,(第三卷第二期).。19世紀英國學者初譯此詞時顯然認為方志是地理。西方的史家及在西方的中國史家,隱然認為方志是地理性的材料。
和中國文獻的漢譯英相反,西方文獻著作在漢譯中也同樣碰到術語的使用和表達問題。我們發現一些西方文獻著作在漢譯中被譯稱為“志”。如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于公元98年完成的《De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拉丁語),意為“關于日耳曼人的起源和分布”,這部著作詳細記述了公元1世紀左右的日耳曼部族的分布情況,包括西日耳曼人的社會制度、政治組織和物質文化生活,日耳曼人的特征及生活狀況和宗教信仰狀況。中文文本翻譯時被譯為《日耳曼尼亞志》。美國人尼爾·R·彼爾斯與杰里·哈格斯特洛姆合著《The Book of America:Inside 50 States Today》,1987年中文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編譯室董樂山翻譯為《美國志——五十州現狀》,從英文書名和中文書名的比照看,對應“志”的只有一個詞“book”,為什么翻譯者會將這里的book翻譯為“志”?其實這里的book相當于“概略”“概況”的意思,翻譯者出于對“分區概略”類似于中國的分區簡志,所以意譯為《美國志》。2017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方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程洪在單元點評時,同樣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認為美國各個州都有對州各方面情況介紹的文獻,他認為這其實就是各州的簡志。是否翻譯為“志”,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基于翻譯者對“志”的理解。除了這些個別的西文著作書名翻譯為“志”外,西方語境中還有兩類術語翻譯為中文時被譯為“志”,一類是Geography Records即地理學的地志,另一類是ethnography即人類學的民族志。如果將英語的詞根作分解,graphy表示音素、詞素等,相當于是一種書寫單位、書寫符號,實際上類似于文獻記錄文本的意思,也就是中文語境中的廣義上的“記”“志”。
通過對漢語和西方語言兩種文化語境的考察,可以發現中國文化的“(方)志”,在西方人看來和他們的(地方)編年史、地理詞典有部分接近的成分。而西方的地理學地志和人類學民族志,以中國人的眼光看,又含有類似中國的“志”的意義。這種文化翻譯,恰恰體現了中西方對“志”和“方志”的雙向理解,正是這種理解構成了中西方關于“志”“方志”文化學術交流的基礎。
三、中西方地方文獻的生成機制比較與西方地方志
地方志這樣一種地方資料文獻,從表象看,似乎是一種知識體系的體例分類,而從深層來透視則是社會結構的折射。
歷代中國方志在體制和內容上,基本上是為滿足統治官員的需要而設。除了純地理的綱目外,如職官、公署、鄉宦、流寓、選舉、學校、關隘、堡寨、道里、驛站等等,都反映了官吏的關心與需要所在。現代史家對方志的上述性質多有所認識,如顧頡剛:“每地修志,主要標的,在于備行官史之鑒覽,以定其發施政之方針。”方志不但不是非官方地方社會或地方社會創制底產品,而是中央政府官吏所促生及應用的文獻。它的存在本身,其內容、體例、以及興衰歷來都取決于中央的政策。其首要目的在于為統治的官員提供地方上的情報,這個目的也決定了方志的內容。方志的這種本質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形式及內涵[1]Alitto.中國方志與西方史的比較,原載臺灣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漢學研究,(第三卷第二期).轉自杭州地情網,http://hzfzw.hz.gov.cn/szyd/zgxc/201705/t20170524_696565.html.。
由于中國和西方社會治理制度和社會結構不同,歷史上中國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主要表現為中央集權制下國家官僚對地方的治理,這些地方行政區劃的國家治理單元,執行著中央朝廷的使命,對下進行分口治理,這就造成了志書橫分的若干門類。直到今天,新修方志依然是官修和政府修志,志書的主體結構基本對應地方政府國家部門的若干相應領域和相應工作。所以,中國地方志的本質是國家對地方分門別類的地方治理文獻。
而在歐洲歷史上,其封建制并不是像中國這樣的中央集權制,而是貴族封邑制加上教會管控的教區制,社會的基本單元不是像中國這樣的行政區劃,而是采邑和教區。因此,歐洲歷史上的法國和英國,其地方史文獻主要是貴族莊園承嗣的譜牒、家族樹文獻和教會的教區文獻,諸如教會的葬禮、婚禮、洗禮等禮儀登記,教會裁判記錄,修院、教會的史錄,或上述建制所持有的地契、租約、賬冊等,加上其他教會及不同單位留下的文獻;此外,還有地方圣人和名僧的年志。19世紀中葉以前,如果沒有宗教建制的種種文獻,西方地方史是不會存在的[1]。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教區教會代行了類似中國地方政府地方治理的職能。換一種說法就是,中國沒有西方教會的對等組織,西方教區裁判,圣事主理等文化對等的功能,在中國是由中央政府的各級行政單位擔任的。西方也沒有類似中國的國家地方官僚體系。在兩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中,中國國家官僚相等于西方教會官僚。
用這樣的視角來理解,中國方志文化語境中的“地方”是地方行政區,所對應產生的實證資料文獻就是“方志”;而西方文化語境的“地方”則是采邑莊園和教區,所對應產生的實證資料文獻如何被冠名,則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你可以稱之為地方史,也可以像中國人的說法一樣稱之為歐洲版的西方地方志。所以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教授Van der Loon就認為,和中國學者所持的意見相反,歐洲有自己的地方志。仔細閱讀《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各郡史》,就可以發現,它們并不差于與之相對應的中國典籍。在某些方面,如古跡和地方風俗,它們的記錄還遠勝于中國的方志[1]Alitto.中國方志與西方史的比較.原載臺灣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漢學研究,(第三卷第二期).。
哲人們說,世界上沒有兩條同樣的河流。過分強調絕對的同,那么世界上就沒有同。我們可以說“他們那種地方文獻根本不能和我們的地方志相比”[2]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修訂本).方志出版社,2003.(P14),從而否定西方“方志”的存在;但是同樣,西方(教會)地方史志中不也同樣有若干內容是中國的地方志所沒有的嗎?
四、內視的中國方志和外視的西方人類學民族志比較
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區別在于,東方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安土重遷,社會的流動性相對較小,人穩定地生活在一個相對固定的鄉土區域中。而西方是以海洋貿易為主的重商社會,商業貿易和物流輸運帶來的流動性較大。特別是地理大發現以后,歐洲人向美洲、亞洲、非洲不斷拓展,伴隨著資本原始積累,英國等主要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亞非拉地區實行殖民主義統治,世界開始進入歐洲主導的全球化時代。出于對海外世界和殖民地認識與統治的需要,西方誕生了以歐洲為主體觀察異民族的人類學及其民族志。1771年和1787年,德國歷史學家先后提出ethnography和ethnology,這種在19世紀的歐洲大陸開始流傳的知識觀,重在對不同人群(people)、民族(nation)和種族(race)等文化人群的研究。“ethnography”一詞的詞根“ethno”來自希臘文中的“ethnos”,意指“一個民族”“一群人”或“一個文化群體”[3]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P25),graphy意為書寫文本或記錄文本。“把關于異地人群的所見所聞寫給自己一樣的人閱讀,這種著述被歸為‘民族志’”[4]高丙中.寫文化與民族志發展的三個時期(代譯序).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爾庫斯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高丙中,吳曉黎,李霞等譯.商務印書館,2006.(P6)。
20世紀初,中國學人開始翻譯傳播西方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雜志上發表《說民族學》一文,認為民族學有記錄和比較兩類,“偏于記錄的名為記錄的民族學”,還說ethno源于希臘文ethnos,就是民族,graphie源于希臘文graphien,就是記錄,因而ethnography指的就是“記錄的民族學”,后來林耀華、凌純聲等人開始使用“民族志”來區別ethnology(民族學)的ethnography[5]娥滿.人類學的方志學淵源.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第11卷第16期).。這就是西方語境的ethnography轉換為漢語語境的“民族志”的由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內重建人類學時,曾專門召開“民族研究屬于譯名問題座談會”,當時參考的港臺地區基本詞典的譯法都是“民族志”,表明了華人漢語圈對“民族志”術語譯法的高度認同。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出生、生長在新中國一直習慣使用“調查報告”“民族調查”“實地調查”等名稱,在寫法上還延續過去模式的學者開始頻頻使用“民族志”來為自己的新作品命名。中文翻譯ethnography為“民族志”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界的約定俗成。
盡管現在中國人類學界對“民族志”術語有不同的看法,如主張用“文化志”“生活志”取代舊的“民族志”的稱呼[6]徐新建.從文學到人類學——關于民族志和“寫文化”的答問.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但是這些術語中已然保留了“志”。從20世紀初,西方人類學傳入中國以來,西方術語翻譯轉換為中國漢語,一直保留著“志”的稱呼,都表明了中國知識界對中國文化術語“志”的理解和在西方學術語言轉換中的運用。
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和學術規范,西方人類學民族志和中國地方志知識體系中的民族志顯然不是一個概念。和中國方志相比較,西方人類學民族志有著諸多的特點。
中國的地方志本質上體現的是國家內部本土的由上而下縱向管理以地方行政區為范圍而進行記載的文獻思維,迄今為止,以現行行政區范圍為界“越境不書”依然是一條基本的記事原則。這種封閉的畫地為牢的地方政區觀本質上是一種內視的文獻思維,眼睛向內看。而最初的西方人類學民族志恰恰相反,是歐洲人以自身的歐洲文明為中心,眼睛向外,對異國他鄉、異邦異民族、邊緣文化觀察的記錄,體現的是由內而外的觀察視角和思維。
中國的地方志是東方文明地區自己人對本土的記載,很大程度上是對既有的文獻資料整合加工編纂記錄的結果;而西方人類學民族志是歐洲“文明人”對“蠻荒”“不開化”無文字的民族,以參與其中的方式直接通過田野調查觀察記錄的結果,更多的不是依據現成的文字性文獻,而是人類學家自身的觀察和對被觀察者的口述、行為所體現的人類活動,他們強調到田野現場搜集第一手資料,注重提供地圖、圖表和照片作為“真的到過那里”的象征物。民族志的文本特性是通過人類學方式對特定文化進行的描寫,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類,它有幾個規定性的要素,有著某種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客觀化承諾,民族志向讀者承諾:我寫的這個東西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一個客觀性和事實性的存在。
中國地方志強調用編纂者第三者的視角,而西方人類學民族志則強調田野考察者與被考察對象的“互為主體”的關系,里面大量運用第一人稱的表述,因為是以“我”的視角直接參與接入,其描述往往給人身臨其境之感。這樣的視角今天被非虛構紀實文學和紀錄電視專題片所采用。
中國的地方志就內容而言強調一方之全史,對行政區范圍內地方治理相關的自然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進行從歷史到現狀的全面記述,尤其是新方志注重政府治理各種制度實施運行情況的記錄。而西方人類學民族志體現的則是從民間底層觀察的現存的各種社會文化,并不十分強調歷史性的全面,其敘述結構是全貌的民族志(total ethnography),逐一分類考察文化的組成部分或社會組織,提供關于地理、親屬關系、經濟、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詳細圖表。其基本內容包括文化與生存(語言信息交流、兒童養育、生命延續)、群體(婚姻與家庭、親屬與繼嗣、年齡集團、共同利益社團、社會分層)、社會一體化與社會生活經濟體系(資源、生產、分配與交換),政治組織與社會控制,宗教與巫術,口頭、音樂、雕刻等藝術等[1]張小軍,木合塔爾·阿皮孜.走向“文化志”的人類學:傳統“民族志”概念反思.民族研究,2014,(4).。所以民族志的作品更多體現了社會性和文化性,而不是官方體制性內容。
中國地方志強調文約事豐,作系統化概括性的表述,強調“述而不作”;西方人類學民族志以解釋和分析作為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察者對該社區個人的借鑒和提升,在注重力求客觀描寫“淺描”的同時,也進一步對文化事項后面的意義進行挖掘和闡釋“深描”,分析時空坐落或發生的事件,從而來表述真實生活細節,以問題為思路將田野細瑣零碎的描述資料加以整理,并尋求文化網絡的解釋,田野數據經過分析解釋形成有系統的主張[2]威廉·A·哈維蘭著.王銘銘等譯.當代人類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格爾茲認為人類學家的工作主要在于通過了解“土著的觀點”(native’s point of view)來解釋象征體系對人的觀念和社會生活的界說,從而達到對形成地方性知識的獨特世界觀、人觀和社會背景的理解[3]楊殿斛.從方志到民族志:中國民族音樂研究的現代進程.小說評論,2008,(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殖民主義逐步走向終結,西方人類學民族志也開始發生轉向,從對殖民地異族的觀察研究轉向本土化以及整體的人類文化的研究。西方人類學傳入中國、印度等非西方世界后,同樣也被進行了改造,從歐洲為主體的外視視角轉換為本國內部的本土觀察視角。以中國為例,人類學民族志被運用于國家內部的中心對邊緣、內地對邊疆民族地區,上層對社會底層社區的觀察。但是與地方志所不同的是,人類學民族志在中國仍然保持了“他者”的視角和田野調查的傳統。
比較中國地方志與人類學民族志,可以發現這兩種文獻都具有“志”的實證記錄特征,都強調客觀性。所不同的是,地方志主要是針對地方政區的“地方”,強調從歷史到現狀各個領域的記載,而人類學民族志的對象則是針對“文化人(族)群”。盡管有時候人類學民族志很多是觀察研究的地方社區,和方志的“方”有一定的復合性,但是其研究出發點主要是社區文化人群的“點”上,而不是落在“政區”的面上。由于現在的人類學強調闡釋性,民族志較之地方志具有更強的學術性。
五、中國全球化戰略思維下的人類學民族志對方志轉型的啟示
1978年后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中國進入全球化貿易體系,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人們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不再是以往相對固定的鄉土化生活。近年,由于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逐步取代了美國成為全球化的新的倡導者和領導者,對外開放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的引進來逐步轉向走出去,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人正在把視角向外延伸,由中國引領世界的中國版全球化正在到來。
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伴隨著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當下的中國需要重新睜眼看世界,看外面的世界,看除了歐美以外的世界。整個中國都需要用“他者的眼光”研究外部世界,理解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全球化的中國時代需要構建中國思維的人類學民族志。
在這樣由內而外看世界的視角轉變進程中,中國地方志迫切需要跳出傳統的國家內部地方政區“坐井觀天”式的視野,將眼界從封閉的政區轉為“地方+外部世界”,從孤立的地方政區轉向區域一體化,從內地中心轉向邊緣邊疆,從中國轉向跨國的“一帶一路”區域。
適應這種視野的轉變,地方志的觀念迫切需要轉型。有必要將原先局限于相對于以中國為天下的國家內部政區性的“地方”概念拓展為以全球世界為天下的新的區域空間觀念的“方”,將“中國”方志向境外延伸,拓展一帶一路志、列國志等新的空間志。在這種視野拓展的過程中,向外開放的中國方志與發現“他者”的人類學民族志有可能實現高度融合,合二為一。
當下的中國方志從人類學那里汲取的不只是向外拓展“走出去”的思維,同時也需要吸收人類學的思維“走下去”,行走在大地上,吸納人類學民族志直接參與田野觀察調查的方法,改變單純地從文獻到文獻的編纂方法,運用當事人口述史、影像志的手段,從現實中采集第一手資料,更真實真切地表現,改變志書那種概觀式記錄泛泛而談的僵化的記載方式。同時,地方志可以采用人類學側重社會文化觀察的視角,從政府工作為主的記述轉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史記錄,就像浙江《象山縣志》運用人類學方法所做的那樣,如此,方志才能被賦予更鮮活、更文化、更學術的意義。
(責編:張佳琪)
Comparative Analysisonquot;Chroniclequot;andquot;Gazetteerquot;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Ji Xiang
吉祥(1963—),男,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處長,研究方向為方志文化、區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