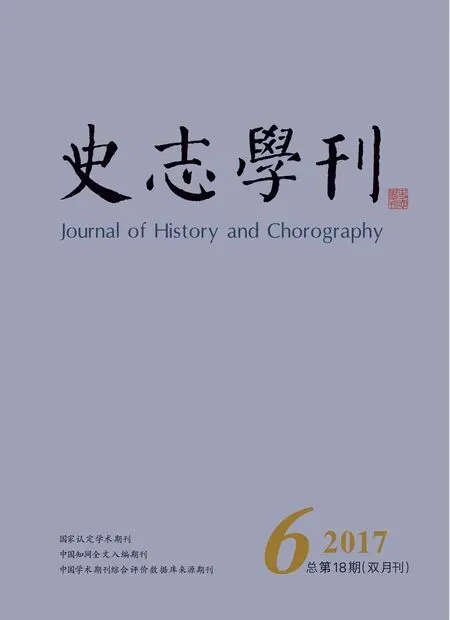兩晉南朝時期的黃紙
李正君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在紙張被廣泛應用之前,古代官僚上呈皇帝的奏疏,一般書寫在簡牘上,而簡牘是十分笨重的,“按照邢義田教授的測算,如果司馬遷的《史記》如江蘇東海尹灣漢簡《神烏賦》和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的書寫方式,每簡38字左右,則全書130篇,52.65萬字,需要竹簡13855枚。以木簡的重量計,則達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鮮的竹簡計,則達58.33公斤;用新鮮紅柳簡則更重達101.62公斤。”[1]王子今.秦始皇的閱讀速度.博覽群書,2008,(1).可見簡牘作為主要的書寫載體,其書寫運輸和閱讀都是十分不便的。到了西晉時期,政府公文書寫的載體發生了變化,白簡開始大量應用,“傅玄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靖踴不寐坐而待旦。”[2](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一二)·憲官部.中華書局,1960.(P6135)萬繩楠和韓樹峰兩位先生都認為,這里的“白簡”不應該是指白色的簡牘,而是與黃紙相對應的白紙[3]萬繩楠.論黃白籍、土斷及其有關問題.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韓樹峰.漢晉時期的黃簿與黃籍.史學月刊,2016,(9).。而到了東晉時期,政府開始提倡用黃紙取代白簡,作為公文書寫的載體。《太平御覽》(卷六百五)《文部二十一·紙》引《桓玄偽事》記載:“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4](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六百五).文部二十一·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557)從這段材料不難看出,因古時無紙,才使用簡,而此時東晉政府提倡以黃紙代替簡。這里的簡不可否認當指簡牘,而前揭傅玄所捧“白簡”恐也非白紙,而是簡牘。
一、黃紙的制作
黃紙與白紙相比,區別在顏色。所謂黃紙,是指將白紙在“潢”中浸泡過的紙,曬干會呈現黃色。《說文解字》引《釋名》曰:“潢,染書也。”《齊民要術》中記載有黃紙的制作方法,“染黃及治書法: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特宜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也。人浸檗熟,即棄滓,直用純汁,費而無益。蘗熟后,漉滓搗而煮之,布囊壓訖,復搗煮之,凡三搗三煮,添和純汁者,其省四倍,又彌明凈。寫書,經夏然后入潢,縫不綻解其新寫者,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爾,入則零落矣。豆黃特不宜裛,裛則不全入潢矣。[1](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雜說第三十.商務印書館,1930.(P41)有學者認為“潢”指的是潢鳩汁,并指出將白紙浸泡“潢”制成黃紙是為了紙張防蟲,便于保存[2]丁春梅.淺談黃紙與我國古代官府公文.文獻,1995,(2).。然《齊民要術》中有關于紙張防蟲的做法,“水浸石灰,經一宿浥取汁以和豆黏,及作面糊則無蟲,若黏紙寫書入潢,則黑矣。”[1](P42)可見當時以石灰和豆黏面糊是常見做法,黏紙浸泡“潢”則會發黑,正如前揭“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暗也”。
二、黃紙的用途
從東晉開始,政府提倡使用黃紙作為公文書寫的載體,但不是說東晉之前黃紙尚未使用,翻閱史籍我們發現西晉時期黃紙已開始在政府部門廣泛使用,并有以下三種用途。
1.選案。即有關士人官品品狀、選任的文書。《晉書·劉卞傳》載:“卞后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怒,言于中正,退品二等,為尚書令史。”[3](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十六)·劉卞傳.中華書局,1974.(P1078)史學界普遍認為訪問應是中正的屬官,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長孺先生、張旭華先生以及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先生,而近年來通過陳長琦教授的考證,他認為訪問應該是與中正聯系密切的尚書臺吏部的屬員[4]陳長琦.官品的起源.商務印書館,2016.(P126)。陳教授的這一研究,不僅推翻了前人固有的觀點,還在論證的過程中通過排比史料向我們展現了九品官人法實施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中正官與司徒府、尚書臺的關系。而黃紙在兩晉時期人才選任實施過程中也充當重要的角色,黃紙應是書寫士人官員品狀的載體。又《北堂書鈔》卷五十九《設官部十一》引臧榮緒《晉書》云:“朱整,字偉齊,為尚書仆射,領吏部。以公清為性,持直厲意,內外郡縣州鄉士人,皆見物卿乃不開其黃紙。”朱整仍為西晉時人,吏部的選案仍用黃紙。劉宋時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南齊時,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僅盡。”[5](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二)·褚炫傳.中華書局,1972.(P582)吏部尚書是兩晉南朝時期負責官員選任的主要官員,其主要公文都是以黃紙書寫。
2.彈文。即監察官吏彈劾其他官員的文書。南齊時御史中丞袁彖彈劾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6]南齊書(卷三十六)·謝超宗傳.(P683)而在袁彖彈劾謝超宗之前,治書侍御史司馬侃已經彈劾過了,“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可見司馬侃彈奏謝超宗時使用的應該是黃紙。又南齊御史中丞沈約彈奏王源,“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7](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四十)·彈事.中華書局,1977.(P563)梁代御史中丞任昉彈奏曹景宗,彈文最后寫道:“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任昉彈劾范縝,“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另南陳御史中丞徐君敷彈奏寧遠將軍、散騎常侍方泰,御史中丞宗元饒彈奏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蔡景歷,御史中丞徐君敷彈劾武陵王伯禮時都使用白簡。而在南陳使用白簡的這三個例子中,可能并不是因為被彈劾者官品低下,而是故意使用白簡來表達一種貶低之義。
3.戶口文書。《太平御覽》卷六○六引《晉令》:“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名。”[1](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六○六).文部二十二·札(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P562)學術界對于黃籍的研究多認為其是戶籍,黃籍是與白籍相對應的,書寫在黃紙上而得名,近年來通過韓樹峰先生的研究,他認為“西晉時期,一些重要的文書以黃紙為書寫材料,面對此種壓力,政府以簡牘書寫重要文書時,將非黃色簡牘如白色木牘染成黃色,黃籍之‘黃’因此也具有了具體顏色的含義……西晉黃籍指書寫于黃色簡牘之上的重要簿籍,戶籍只是其組成部分之一。《晉令》中的黃籍甚至不包括戶籍,而指戶籍以外的其他戶口文書。”[2]韓樹峰.漢晉時期的黃簿與黃籍.史學月刊,2016,(9).雖然對于黃籍的性質,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爭論,但其主要書寫戶口文書的認識是一致的。
三、彈文中黃紙和白簡的使用
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彈文的書寫是有白簡和黃紙的區分的,這種區分應與被彈劾人的官品高低有關。謝超宗時任征北諮議參軍,其官品并不具備使用黃紙的待遇。征北諮議參軍在南齊時的品級不詳,在南梁時為第六班。王源官職為南郡丞,《通典》未載南齊官品,但郡丞在劉宋時期列第八品,而在陳代,萬戶郡丞列第七品,萬戶以下郡丞列第八品,似地位不顯。曹景宗時任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第九班。范縝時任尚書左丞,第九班。從此至少我們可以判斷蕭梁官班在第九班以上者,被彈劾時彈文可以使用黃紙。而從王源擔任南郡丞的事例可以看出使用黃紙的范圍應該很大。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以上所舉諸例中,沒有一例使用了黃紙,白簡成為彈劾時彈文書寫的主要載體,使用白簡的主要目的在于貶低被彈劾者。
萬繩楠先生在《論黃白籍、土斷及有關問題》一文中引出沈約《奏彈王源》,認為“黃案又為左丞上署,則凡尚書左丞所掌事務應立文案的,均用黃紙,均為黃案,之所以用黃紙,稱黃案,據沈約與《南齊書》之說,與官品及文案性質有關。白案是右丞上署……可知白案在南朝,為有關兵士、百工、民戶及犯官的文案,立案用白簡(白紙),因稱白案。”[3]萬繩楠.論黃白籍、土斷及其有關問題.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查《南齊書》卷十六《百官志》載:“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黃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左丞掌“宗廟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諸彈案、選用除置、吏補滿除遣注職。”右丞掌“刺史、二千石、令、長、丞、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4](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十六)·百官志.中華書局,1972.(P321)按照萬先生的說法,“諸彈案”是尚書左丞職掌,故彈文應用黃紙,但彈文又是犯官文案,所以才使用白簡。對于這一觀點,筆者認為還有商榷的余地。前揭幾起彈案中,或曰“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或曰“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或曰“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明顯可以看出白簡和黃紙的區別不在于文案性質,而是官員品級。另外,前引謝超宗先被治書侍御史司馬侃彈劾,后又被御史中丞袁彖彈劾,稱“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可見司馬侃在彈劾謝超宗時應使用的是黃紙,同樣是對謝超宗的彈劾卻使用了兩種書寫載體,可見使用黃紙和白簡的區分并不在于文案的性質,而在于官品的高低。在謝超宗案例中之所以出現兩種書寫載體,筆者認為前彈劾者治書侍御史司馬侃為御史臺御史中丞署吏,據實上奏,也按照謝超宗的官品給予黃紙的待遇,而后彈劾者御史中丞袁彖為御史臺長官,是全國最高的監察官員,故在彈劾謝超宗時對其刻意貶低,而使用白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