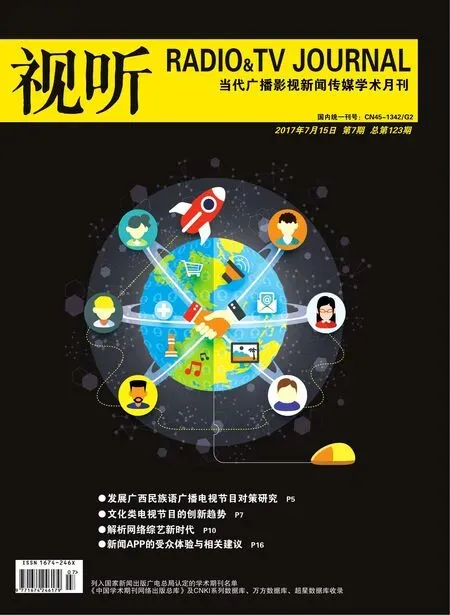電影本質(zhì)下對(duì)亞洲青春片中“物哀”與“純愛(ài)”意象分析
——以《七月與安生》《情書(shū)》《假如愛(ài)有天意》為例
□ 喬淑一
電影本質(zhì)下對(duì)亞洲青春片中“物哀”與“純愛(ài)”意象分析
——以《七月與安生》《情書(shū)》《假如愛(ài)有天意》為例
□ 喬淑一
近年來(lái),中國(guó)青春題材電影方興未艾,但是也因同質(zhì)化傾向嚴(yán)重等問(wèn)題而口碑不佳,這就需要從電影本質(zhì)出發(fā)去真正理解青春電影。本文通過(guò)電影本質(zhì)理論,對(duì)中、日、韓的三部青春電影《七月與安生》《情書(shū)》《假如愛(ài)有天意》中的“物哀”與“純愛(ài)”意象進(jìn)行分析,為中國(guó)當(dāng)下的青春電影創(chuàng)作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電影本質(zhì);亞洲青春片;物哀;純愛(ài);宿命
伴隨著青春題材電影類型的成熟,這種原本只是小眾的電影類型卻在電影平臺(tái)上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春題材電影多以對(duì)青春的追憶為主線,對(duì)愛(ài)情的認(rèn)知為主題,以友情與愛(ài)情沖突、三角或多角人物關(guān)系為公式化情節(jié),以其娛樂(lè)化的內(nèi)容、準(zhǔn)確的受眾定位和良好的市場(chǎng)營(yíng)銷而廣受歡迎。青春題材電影可以分為青春片、青春偶像片、青春勵(lì)志片。近年來(lái)亞洲青春偶像片比比皆是,但青春片卻相對(duì)較少。戴錦華曾在其著作《電影批評(píng)》中指出,青春片“在于表達(dá)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諸多的尷尬和匱乏、挫敗和傷痛。可以說(shuō)是‘無(wú)限美好的青春’的顛覆。‘青春片’的主旨,是‘青春殘酷物語(yǔ)’”。因此,青春片不同于青春偶像片的風(fēng)格與基調(diào),而是展現(xiàn)出一種淡淡的“物哀”情緒與“物哀”中的“純愛(ài)”意象。①
一、物哀與宿命——電影是時(shí)空的藝術(shù)
“物哀”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日本,是一種悲劇式的美學(xué)意識(shí)。齊藤清衛(wèi)把“物哀”歸結(jié)為“哀憐的情趣”“對(duì)對(duì)象的情愛(ài)”“控制情緒的一種心情”“與靜觀諦念相聯(lián)系”四個(gè)方面,認(rèn)為“物哀”是一種與開(kāi)發(fā)性的積極情感相遠(yuǎn)離、比之情緒更接近于熱情的、屬于感情范疇的一個(gè)概念。②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lái),這本獨(dú)屬日本青春片的“物哀”也漸漸滲入到亞洲其他國(guó)家的青春片中,形成它們自己的風(fēng)格。宿命論作為一個(gè)哲學(xué)學(xué)說(shuō),強(qiáng)調(diào)各種事件、行為都必須服從于命運(yùn),也就是說(shuō)除了我們實(shí)際做的事,我們無(wú)力去做任何事。“物哀”和“宿命”這兩點(diǎn)可以傳達(dá)青春片的敘事特點(diǎn),尤其是“宿命”一詞,必然帶著時(shí)空的轉(zhuǎn)換的特點(diǎn)。
電影《七月與安生》是一部典型的關(guān)于愛(ài)、分享、記憶、離去的青春片,講述了安生在回家的地鐵上遇到了自己和閨蜜七月多年前愛(ài)過(guò)的蘇家明,家明的名片被安生帶回家并放在自己珍視的“記憶”的盒子中,安生孩子陰錯(cuò)陽(yáng)差打開(kāi)并撥打家明電話而由此展開(kāi)的兩個(gè)女孩從13歲到27歲的關(guān)于成長(zhǎng)、友情和愛(ài)的故事。與很多青春片著眼于愛(ài)情不同,《七月與安生》更多的著眼于“愛(ài)”與“情”,故事開(kāi)頭帶有一些宿命或帶有命運(yùn)安排的意味。七月安穩(wěn)的家庭環(huán)境注定了她是典型的“乖乖女”:遵從媽媽的話穿著保守的內(nèi)衣,留著乖乖的學(xué)生頭或者是披肩發(fā),按照父母的路線學(xué)習(xí)—工作—談戀愛(ài)—結(jié)婚。復(fù)雜的家庭則使安生放縱不羈愛(ài)自由,人生晃蕩而顛簸,她不愛(ài)穿內(nèi)衣,覺(jué)得是束縛,在青春期時(shí)弄了象征另類與反叛的爆炸頭。蘇家明的出現(xiàn)使她們分裂你我,過(guò)上截然不同卻又殊途同歸的生活。七月和安生的人生在27歲到來(lái)之際更像是二者的轉(zhuǎn)化,七月成為安生,安生變成七月。然而,當(dāng)經(jīng)歷了人生種種,安生萬(wàn)水千山走遍,終于回歸她所向往的卻不曾擁有的安穩(wěn)生活,她進(jìn)入課堂學(xué)習(xí),也留起柔順的直發(fā);七月在習(xí)慣了波瀾不驚的安穩(wěn)生活后,決心剪短頭發(fā)出去體驗(yàn)安生的漂泊。不論是安生早有預(yù)設(shè)的希望自己27歲死去卻沒(méi)有死去,還是七月在宿命中于27歲死去,都像是一種“循環(huán)”,一種宿命,從童年到少年到成年,從現(xiàn)實(shí)到回憶到臆想再到現(xiàn)實(shí),而在這種層層鋪墊的宿命中,又帶著些許的無(wú)奈與感傷。這種生命無(wú)情的嘲諷與無(wú)法改變命運(yùn)的哀嘆,恰恰也表現(xiàn)出“物哀”的情緒。
“青春電影教父”巖井俊二的電影《情書(shū)》也是一部關(guān)于愛(ài)、記憶與離喪的優(yōu)美青春片。博子對(duì)未婚夫藤井樹(shù)(男)的死無(wú)法釋?xiě)眩谑峭?dāng)年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可是,博子卻奇跡般地收到了回信,她既帶著無(wú)法相信的感受又帶著難以自拔的喜悅。觀眾作為全知的主體,自然已經(jīng)知道博子寄出的信其實(shí)是寄給了“自己”,那個(gè)外貌特征與自己幾乎一致的“自己”。雖然并沒(méi)有看見(jiàn)彼此,卻能夠意識(shí)到彼此之間的鏡像關(guān)系,影片交替的時(shí)空中,一個(gè)是現(xiàn)在時(shí),一個(gè)是過(guò)去時(shí),卻隱含著宿命的悲涼之情。“物哀”要求敏銳感受人生無(wú)常以及瞬間的微妙感覺(jué),命運(yùn)的無(wú)常總是被巖井俊二有意地凸顯出來(lái),而在這種無(wú)常中,宿命無(wú)疑是最為不可琢磨的。
在韓國(guó)電影《假如愛(ài)有天意》中,梓希收拾房間時(shí)無(wú)意中發(fā)現(xiàn)一個(gè)神秘的箱子,里面都是她母親初戀時(shí)的信件。在不斷對(duì)母親的青春愛(ài)情回憶的同時(shí),梓希也在經(jīng)歷著與母親頗為相似的愛(ài)情。從敘事結(jié)構(gòu)上來(lái)看,這部電影是分段交叉式結(jié)構(gòu),一條線索是母親桔希與吳俊河的感情,另一條線索是梓希與尚民之間的感情;一個(gè)是過(guò)去時(shí)空,一個(gè)是現(xiàn)在的時(shí)空,卻因?yàn)闀?shū)信與項(xiàng)鏈串聯(lián)在一起,母親的“悲戚”愛(ài)情在女兒的身上實(shí)現(xiàn)了歸屬。母親的愛(ài)情段落中始終彌漫著“物哀”的情緒:母親出身高貴,與俊河的普通身份有著巨大差距;泰宇在兩人感情上有過(guò)介入,后來(lái)卻為了成全兩人而試圖自殺;俊河為了桔希不再糾結(jié)而去參加戰(zhàn)爭(zhēng),最后一次見(jiàn)面千方百計(jì)不讓心愛(ài)的人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失明,并謊稱自己結(jié)婚。尤其是很多年后在飯店的約會(huì),桔希與俊河“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wú)語(yǔ)凝噎”,“物哀”情緒在升華。在導(dǎo)演看似隨意的時(shí)空轉(zhuǎn)換中,卻因?yàn)椤皶?shū)信”“彩虹”“項(xiàng)鏈”“照片”這些隱喻式的視覺(jué)符號(hào)形成了一種宿命,人生兜兜轉(zhuǎn)轉(zhuǎn),有緣起有緣落。
《七月與安生》《情書(shū)》《假如愛(ài)有天意》同屬于青春片,它們不同于“青春偶像片”通過(guò)美好的愛(ài)情、甜蜜的往事給觀眾制造的“白日夢(mèng)”幻想,這三部影片運(yùn)用電影的時(shí)空表達(dá)了青春中的“物哀”與人生中的“宿命”。三部影片都沒(méi)有回避死亡,正如村上春樹(shù)所說(shuō)的“死并非生的對(duì)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這使三部影片增加了哲學(xué)的意味。
二、純愛(ài)與美學(xué)——電影是視聽(tīng)的藝術(shù)
“純愛(ài)”作為一種藝術(shù)形態(tài),始見(jiàn)于日本文學(xué)作品,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文風(fēng)寡淡平和、潔凈唯美、悲傷寂寥的川端康成。純愛(ài)電影本身并沒(méi)有明確固定的定義。
在《七月與安生》中,安生的現(xiàn)在時(shí)大多是采用一種冷色調(diào)。而安生在少女時(shí)代是一個(gè)愛(ài)自由的小姑娘,她穿著明艷的紅色,涂著明艷的指甲,有火一般的熱情。如果沿著安生的成長(zhǎng)線看,安生相關(guān)的視覺(jué)構(gòu)造是一點(diǎn)點(diǎn)在發(fā)生變化的,從最初的少不更事,到外出漂泊,無(wú)論是她出場(chǎng)時(shí)的光線還是衣著都有著一個(gè)從明到暗的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還有細(xì)微的變化,那就是只要七月在,安生就是明亮色;七月不在時(shí),安生就是暗光、暗調(diào)。在七月與安生的童年時(shí)代,她們?cè)陉?yáng)光下踩著影子,無(wú)憂無(wú)慮,明媚而溫馨;少年時(shí)代,因?yàn)樘K家明的出現(xiàn),她們經(jīng)歷了心理上的一絲波瀾,在“酒吧”“寺廟”這幾個(gè)壓抑、局促的地方,影片對(duì)光影也是作暗色處理。光線色彩的變化,詮釋了人物心理的變化和劇情的走向。
青春片大師巖井俊二還有著“映像詩(shī)人”的美譽(yù),他對(duì)鏡頭和光的應(yīng)用形成了“巖井電影美學(xué)”。同時(shí),巖井俊二在人物設(shè)置上喜歡通過(guò)“自我”分裂,將自我的不同性格分裂在一部電影之中,這種分裂是通過(guò)不同的色調(diào)和光影來(lái)表達(dá)的。在《情書(shū)》中,渡邊博子和藤井樹(shù)(女)容貌相似,性格卻不盡相同,博子安靜、內(nèi)斂,藤井樹(shù)(女)活潑、可愛(ài)。博子的出場(chǎng)時(shí)多數(shù)是逆光攝影,人物語(yǔ)言也不多;而藤井樹(shù)(女)出場(chǎng)時(shí)的光線色彩是明亮溫馨的。不僅“視”,“聽(tīng)”也體現(xiàn)著“巖井美學(xué)”的特點(diǎn)。美國(guó)電影作曲家赫爾曼曾說(shuō):“音樂(lè)實(shí)際上為觀眾提供了一系列無(wú)意識(shí)的支持。它總是不顯露的,而且你也不必要知道它。”《情書(shū)》中的音樂(lè)淡雅而迷人,用鋼琴聲貫穿整部電影。影片一開(kāi)始,博子躺在雪地上時(shí),觀眾可以明顯地聽(tīng)到鋼琴聲,但隨著博子漸漸遠(yuǎn)去的身影,鋼琴聲好似不再那么明顯。這并不是說(shuō)鋼琴聲消失了,而是觀眾會(huì)沉浸于電影與音樂(lè)的融合,體會(huì)導(dǎo)演營(yíng)造的意境。
電影的色彩結(jié)構(gòu)有兩種,一種為客觀寫(xiě)實(shí),一種為主觀表意。“純愛(ài)”的標(biāo)簽下,《假如愛(ài)有天意》在母親的愛(ài)情故事中,用的是偏黃的色調(diào),整體呈現(xiàn)暗色調(diào);在梓希的愛(ài)情故事中,則主要用粉色奠定浪漫的基調(diào)。偏黃的色調(diào)不僅表示了對(duì)過(guò)去的回憶,代表著過(guò)去時(shí)空,實(shí)則也暗示了情感的不美滿;粉色代表浪漫、美妙、純純的愛(ài)戀,暗示了有情人終成眷屬。這種導(dǎo)演主觀表意的方式,給了觀眾提前預(yù)知的能力,但是又包含具體情節(jié)上的懸念。
畫(huà)面和聲音都會(huì)影響電影的視聽(tīng)表達(dá),也會(huì)影響影像整體風(fēng)格的構(gòu)建。在“純愛(ài)”這一標(biāo)簽下,青春片的視聽(tīng)語(yǔ)言顯現(xiàn)出一定的類型模式,而且此種類型模式會(huì)幫助觀眾有意識(shí)地去理解劇情的發(fā)展走向。但對(duì)于《七月與安生》《情書(shū)》《假如愛(ài)有天意》這三部?jī)?yōu)秀的青春片來(lái)說(shuō),它們顯現(xiàn)出創(chuàng)作上一些表現(xiàn)風(fēng)格的相像性,但絕不是照抄照搬,而是“作者風(fēng)格”下的有益探索。
三、青春殘酷與哀而不傷——電影是作為現(xiàn)實(shí)的映像
意大利作家莫里亞克說(shuō):“你以為青春是好事嗎?青春如同化凍中的沼澤。”在《七月與安生》中,青春的殘酷就在于開(kāi)始不分你我的姐妹走到了互分你我、相互指責(zé);《情書(shū)》中,青春的殘酷在于“我愛(ài)你,你卻愛(ài)著像我的她”;《假如愛(ài)有天意》的青春殘酷在于“我愛(ài)你,你愛(ài)我,我們卻不能在一起”。在青春片中,總有摯愛(ài)離去,總有“傷逝”之悲,總有茫茫宇宙中冥冥的生命的輪回。
電影的本質(zhì)是其作為現(xiàn)實(shí)的映像。德國(guó)著名心理學(xué)家、電影理論家阿恩海姆認(rèn)為“電影并不是機(jī)械地記錄和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工具,而是一門(mén)嶄新的藝術(shù)”,“一切罪愆全在于人類永遠(yuǎn)企求在藝術(shù)上達(dá)到逼真化,人類為力求控制這些自然物質(zhì),使設(shè)法塑造這些形象,這種原始的欲望是促使人類去創(chuàng)造逼真形象的動(dòng)機(jī)之一,在實(shí)踐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推動(dòng)人們不僅止于抄襲,而且還要?jiǎng)?chuàng)造、解釋和塑造的藝術(shù)要求。”③以上三部影片雖分別傳達(dá)出了“物哀”情緒,但也始終體現(xiàn)著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懷,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卻是“哀而不傷”的。《七月與安生》的最后一幕,安生站立在玻璃墻前看到了自己,她對(duì)鏡子報(bào)以微笑,鏡子中的她在移鏡頭中變成了微笑的七月。七月與安生個(gè)性鮮明迥異,卻最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互相為之滿意。《情書(shū)》中渡邊博子穿著紅色的毛衣對(duì)著雪山大喊“你好嗎?我很好!”這其實(shí)是對(duì)感情的一種釋放。《假如愛(ài)有天意》中,雖然母親沒(méi)能和心愛(ài)的人在一起,但是梓希卻與母親心愛(ài)的人的兒子、自己的愛(ài)人走到了一起,這不能不說(shuō)是對(duì)命運(yùn)無(wú)常的些許慰藉。
四、結(jié)語(yǔ)
李銀河在觀看完《七月與安生》表示“中國(guó)電影終于可以看了”,這不得不說(shuō)是對(duì)青春片這一類型電影的莫大肯定。固然,每個(gè)人的青春年華都終將逝去,可是這并不意味著記憶會(huì)隨著年齡的增長(zhǎng)而化為烏有;即使青春時(shí)代有諸多的青澀、純美、殘酷、尷尬、幼稚甚至夢(mèng)想迷失,但是這并不等于記憶會(huì)隨風(fēng)煙消云散。青春、愛(ài)情其實(shí)是人性的舞臺(tái),是社會(huì)人生百態(tài)的一個(gè)窗口。《七月與安生》《情書(shū)》《假如愛(ài)有天意》這三部極具代表性的青春片,不論是在口碑、質(zhì)量還是商業(yè)上均比較成功。面對(duì)國(guó)產(chǎn)電影青春片的泛濫、“叫座不叫好”的現(xiàn)象,如何從豐富多彩的生活出發(fā),去除概念化、表面化,如何把電影與電影本質(zhì)聯(lián)系起來(lái),把實(shí)踐與理論結(jié)合起來(lái),是值得導(dǎo)演們思考的問(wèn)題。
注釋:
①戴錦華.第五章精神分析的視野與現(xiàn)代人的自我寓言:情書(shū)[A].電影批評(píng)[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
②蔣俊俊,吳曉敏.論巖井俊二《情書(shū)》中的“物哀”意識(shí)[J].湖北經(jīng)濟(jì)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8).
③程英.阿恩海姆電影美學(xué)思想中的格式塔心理淺析[J].安徽文學(xué):評(píng)論研究,2008(3).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xué)傳媒與影視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