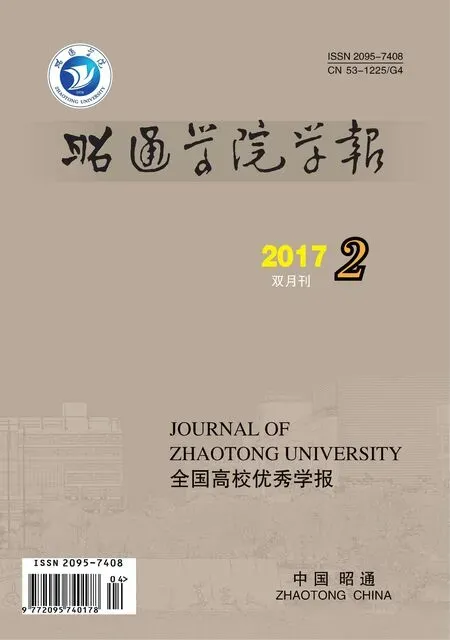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碰撞下的思考
——淺析賈平凹《商州又錄》中的情感體驗(yàn)變化
李 榮
(新疆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2000)
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碰撞下的思考
——淺析賈平凹《商州又錄》中的情感體驗(yàn)變化
李 榮
(新疆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2000)
《商州又錄》是賈平凹的散文代表作。文章用細(xì)膩的筆觸將陜西商州地區(qū)的地域風(fēng)貌、傳統(tǒng)文化、以及商州人樸素的生活場(chǎng)景進(jìn)行了描繪,并對(duì)在現(xiàn)代文明沖擊下商州的變化進(jìn)行了觀察記錄。同時(shí)作者也將他對(duì)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糅雜在其中,并通過(guò)審美意象的苦心營(yíng)構(gòu)、生活場(chǎng)景的細(xì)膩描繪等,將這份特殊的拳拳之情詩(shī)意地書寫表達(dá)。在文本細(xì)讀的基礎(chǔ)上,分析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明碰撞下,商州發(fā)生變化時(shí)作者的情感體驗(yàn)變化,并深挖隱藏其中的原因。
賈平凹;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碰撞;情感體驗(yàn)
賈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發(fā)表于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是在經(jīng)歷了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成熟后,將筆觸轉(zhuǎn)向散文領(lǐng)域而創(chuàng)作發(fā)表的,是其散文創(chuàng)作的巔峰。他用獨(dú)特的視角、飽含深情的筆觸將陜西商州地區(qū)的原始風(fēng)貌、傳統(tǒng)文化、商州的精神面貌等繪聲繪色地展現(xiàn)給了讀者,不僅為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同時(shí)也給新時(shí)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增添了新的氣象。
《商州又錄》的寫作,賈平凹更是擯棄了浮躁的思想和虛假情感的做作表達(dá),沉靜下來(lái),用熟悉的姿態(tài),仿佛一個(gè)老者站在商州山頂慈愛(ài)地俯視著商州的一切。用熱愛(ài)而又不直白外漏的情感態(tài)度描繪著這片土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在這里出生成長(zhǎng)的一個(gè)個(gè)商州人。也正如賈平凹在小序中所寫:“之所以我還能初錄了又錄,全憑著一顆拳拳之心。……否則,我真于故鄉(xiāng)‘不肖’,大有“無(wú)顏見(jiàn)江東父老”之愧了。”[1]95-96基于此,《商州又錄》既是賈平凹對(duì)商州記憶的開掘重現(xiàn),又是對(duì)這片土地在現(xiàn)代文明沖擊下發(fā)生悄然變化的發(fā)現(xiàn)和思考。
一、對(duì)商州拳拳之情的流露
作為 20 世紀(jì)重要的散文作家,賈平凹生長(zhǎng)于古樸的陜西商州大地,雖然后來(lái)他成為城市中的一員,但他的散文仍然顯露著一個(gè)鄉(xiāng)村知識(shí)分子對(duì)于土地的依戀。商州是他在喧囂城市中經(jīng)歷并目睹了現(xiàn)實(shí)激烈競(jìng)爭(zhēng)后的心靈棲息地,使得他對(duì)故鄉(xiāng)的山水、親朋、鄉(xiāng)鄰,以及他們的悲歡苦樂(lè)有著更為真實(shí)的觀察與理解。因此在創(chuàng)作《商州又錄》時(shí),他用真誠(chéng)的態(tài)度在與這里的一切感應(yīng)和交流著,并將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匯在一山一洼、一人一家之中,并在其中傾注了自己深厚的情感。
《商州又錄》首先是用電影的廣角鏡頭向讀者呈現(xiàn)著這里的全部場(chǎng)景。文章以自然景觀作為切入點(diǎn),用細(xì)膩的筆觸呈現(xiàn)了一幅商州山間田園風(fēng)景圖,有商州的大山、清水、綠草、人家。這些景物在他筆尖的陡然描摹中,一草一木似乎也被賦予了生命,充滿了生機(jī)與朝氣。首先進(jìn)入畫面的場(chǎng)景是普通人家日常動(dòng)態(tài)生活,女人在炕頭做針線、男人在地里務(wù)農(nóng)、女孩子在河邊嬉戲打鬧,都是普通的場(chǎng)景卻在賈平凹的筆下陡然生出一份親切的溫存;接著是生孩子的場(chǎng)景,生命的誕生是最為神奇和緊張的,這一場(chǎng)景是作者將每一個(gè)在這里生長(zhǎng)的山里人的一生進(jìn)行的觀照縮寫,在這里出生、長(zhǎng)大,傳承和繼續(xù)著和父輩相似的人生,這既是對(duì)山里人傳統(tǒng)生存模式的再現(xiàn),同時(shí)也是思考,思考山里人祖輩傳承的生活方式是否還能維持、是否還要繼續(xù)下去,這也為后來(lái)商州在新的文明沖擊下,新一輩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發(fā)生改變做了鋪墊。接著是婚娶場(chǎng)景。婚俗是最能折射傳統(tǒng)文化的三棱鏡,首先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中意味著家族血脈的延伸,婚姻不僅僅是兩個(gè)新人的結(jié)合,更是兩個(gè)家族的連接;其次婚嫁又能體現(xiàn)出濃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北方淳樸,婚宴突出熱鬧和排場(chǎng);南方喜水,多了一份活潑俏皮的歡樂(lè)。在婚姻嫁娶中我們是可以觀測(cè)到這一地域傳統(tǒng)文化的很多方面,作者在這里對(duì)商州人傳統(tǒng)的嫁娶場(chǎng)景的描寫,生動(dòng)有趣,不禁流露出了一份欣喜之情。在這份情感的背后,則體現(xiàn)的是賈平凹對(duì)于自己生長(zhǎng)的商州文化的自豪和欣慰。
文章的前六部分可以在賈平凹的字里行間感受他到對(duì)商州大地的深厚情感,是對(duì)他記憶深處那片安靜棲息地的再現(xiàn)描繪。通過(guò)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賈平凹對(duì)于商州不僅有深厚的拳拳之情,更是在這份情感中包含著對(duì)于這片生養(yǎng)自己的土地上生長(zhǎng)出來(lái)的文化的認(rèn)同。
二、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碰撞下發(fā)生變化的呈現(xiàn)
《商州又錄》寫于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那時(shí)的中國(guó)正在發(fā)生著許多變化,正經(jīng)歷著一個(gè)由自我發(fā)展到融入世界發(fā)展潮流的開啟階段,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發(fā)生了改變,外來(lái)的經(jīng)濟(jì)運(yùn)作方式?jīng)_擊著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模式,并帶來(lái)了現(xiàn)代文明。
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說(shuō)到:“資產(chǎn)階級(jí)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chǎng),使一切國(guó)家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過(guò)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guān)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lái)的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成了公共的財(cái)產(chǎn)。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xué)成為了一種世界文學(xué)。”[2]115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式的改變不知不覺(jué)地也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人們的生活從內(nèi)容到方式都發(fā)生著悄然的變化。而這一改變也將觸角延伸到了商州這片土地上,而賈平凹作為一個(gè)對(duì)時(shí)代發(fā)展方向有著敏銳洞察力的作家,通過(guò)家鄉(xiāng)身邊的點(diǎn)滴變化已感覺(jué)到這些些微變化背后的深層次改變,因此他用作家特有的方式——寫作,將這一變化記錄并呈現(xiàn)在讀者的面前。
文章到了第七部分所描寫的內(nèi)容較之前已有所不同,前六部分作者描繪的都是山中如詩(shī)如畫的原始自然風(fēng)貌和生活場(chǎng)景,而到了第七部分則出現(xiàn)了不同以往樸素的山里人,而是打扮時(shí)髦的寡婦、她的店鋪以及哈巴狗等新事物,這些新事物都是傳統(tǒng)新經(jīng)濟(jì)沖擊下帶來(lái)的產(chǎn)物,他們作為新事物的出現(xiàn),所體現(xiàn)的價(jià)值是和山村傳統(tǒng)文化價(jià)值觀的一種對(duì)立。文章中對(duì)于狗有一番頗具意味的對(duì)比描寫,對(duì)于寡婦店鋪里養(yǎng)的狗是這樣描寫的,“十幾條狗都沒(méi)有剪尾巴,肥得油光水亮。”[1]115在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狗只是看家護(hù)院的牲畜,而且是不留尾巴的,而在這個(gè)風(fēng)流寡婦的商鋪里的狗卻和傳統(tǒng)的狗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第一點(diǎn)是它留著尾巴,再就是它不僅有尾巴,而且也和這里的土狗不一樣,成了和人作伴有“洋狗”性質(zhì)的閑養(yǎng)之物。通過(guò)這一細(xì)節(jié)的呈現(xiàn),作者已經(jīng)捕捉到了在鄉(xiāng)村山間發(fā)生的一些改變,并且作者也并沒(méi)有急于對(duì)這一改變做出評(píng)判,而是將目光繼而又轉(zhuǎn)向了山里,借采藥人之口說(shuō)出了山里人的生活本質(zhì),“山上是太苦。正是太苦,不是才長(zhǎng)出了這苦口的草藥嗎,采藥的人成年就是挖著這苦,也正是挖著了這草藥的苦,才醫(yī)治了世上人的一生中所遇到的苦痛嗎?”[1]122這既是作者對(duì)山里人生活的認(rèn)識(shí)同時(shí)也包含著作者對(duì)山里人生活的悲憫情愫。山里人的生活確實(shí)辛苦,但也正是這份辛苦造就了山里人辛勞踏實(shí)的性格,而山里人祖祖輩輩也正是靠著這樣寬厚韌性的品性才能一代人接著一代人繁衍生存下去,是大山養(yǎng)育了山里人,賦予了他們生命力,也是大山教會(huì)了山里人生活的道理。大山對(duì)于山里人是有著母親般的生養(yǎng)之情,外來(lái)人自然不能理解這其中的情結(jié)。而山對(duì)于商州人的恩情,也是作者對(duì)于商州這塊土地質(zhì)樸情感的來(lái)源,這塊生養(yǎng)他的土地,告訴了他生活最質(zhì)樸的道理。大山也就成了他精神的棲息地。
但接著作者似乎也看到了這一變化暗含的時(shí)代發(fā)展潮流,在表達(dá)了對(duì)大山深厚的感情后,他也清醒地看到了傳統(tǒng)文化中存在的糟粕部分,例如一些不合理而且無(wú)科學(xué)性的迷信,對(duì)于生老病死的不科學(xué)認(rèn)識(shí),“熟人死了一個(gè),新鬼多了一名”。[1]124女人懷孕肚子疼懷疑是陰間的男人在勾他兒子的魂,晚上燒酒給他死去的丈夫,這些迷信的都是傳統(tǒng)文化里的糟粕部分,作者不僅看到了文化中需要剔除的糟粕部分,而且也意識(shí)到這些糟粕的剔除必須依靠科學(xué)理性的認(rèn)識(shí)。而在作者的情感態(tài)度也開始發(fā)生變化,繼而他又重新去審視了新闖入的新文化,并用了最具代表性的電影來(lái)發(fā)聲。
“‘這電影真好!’幾個(gè)女孩子看完電影后,嬉笑著回家,說(shuō)著剛剛看完的電影。”[1]129電影是第二次工業(yè)文明帶來(lái)的產(chǎn)物,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新事物。作者也看到了新的事物也不是全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破壞,而是也有它的價(jià)值和帶給人們的新奇和價(jià)值,只是作者在新事物一開始闖入時(shí)看到的更多的是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沖擊和改變。作者在認(rèn)真地觀察后,也客觀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了這種“變化”的必然,以及這種變化背后的時(shí)代趨勢(shì)。傳統(tǒng)文化固然重要,但時(shí)代的發(fā)展更離不開現(xiàn)代文明的力量,新的文化也許在剛剛闖入時(shí),部分方式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它卻是時(shí)代發(fā)展的新生力量。
三、對(duì)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化下碰撞的沉思
當(dāng)新事物闖入并打破原有的秩序和規(guī)則時(shí),勢(shì)必要受到很多阻礙,代表當(dāng)下新文化的現(xiàn)代文明沖擊著商州大地時(shí)也是如此,并且新、舊兩股力量甚至在暗自對(duì)抗摩擦。
在文章的最后一小節(jié)中,奶奶和孫子兩人形象的設(shè)計(jì)以及祖孫兩輩人之間的相處方式是耐人尋味的。孫子是這個(gè)家唯一的男人,她希望孫子可以守住這個(gè)家,而孫子卻總是在這個(gè)家里坐不住,“他喜歡看電影,十里外的地方演也去,回來(lái)就呆呆癡幾天。他不愿留光頭。衣服上不釘口門兒。兩年前就不和她一個(gè)炕上睡,嫌她腳臭。早晚還刷牙呢。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一起說(shuō)話、笑,她聽不懂。”[1]130孫子的一切行為都讓老婆子不能理解和接受,讓她感覺(jué)她的孫子不像山里人,以后會(huì)從她身邊飛走。而奶奶面對(duì)這些變化,是不知所措的,并選擇用迷信的方式來(lái)抵抗——在門上掛鏡子辟邪。
祖孫倆一老一少的形象也正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化的兩個(gè)代表,奶奶代表的是傳統(tǒng)的價(jià)值觀念,而孫子則代表的是新生力量,這一老一少的不能融合,也體現(xiàn)著當(dāng)時(shí)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的相互對(duì)立。傳統(tǒng)的文化價(jià)值觀正如奶奶一樣還存在,雖然充滿了智慧但已不能跟上時(shí)代的潮流;新的文化就像孫子一樣是新生的,而且還在不停地成長(zhǎng),而奶奶和孫子的現(xiàn)狀也像這兩股文化的力量一樣,在交鋒之初,是對(duì)立和無(wú)交流的,奶奶不能理解孫子的行為和做法,而孫子也完全不想給奶奶解釋自己的行為,同住一個(gè)屋檐下的祖孫兩人卻沒(méi)有任何的交流和理解,甚至是有意的相互不溝通。
而這也是作者對(duì)著一變化做出的深沉思考,但作者也沒(méi)有一個(gè)明確的答案,而是以一句“越來(lái)越不像山里人了!”[1]132來(lái)表明自己的情感態(tài)度。在面對(duì)這種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擔(dān)憂還是多過(guò)新喜之情的,擔(dān)心還未成熟的新文化以野蠻生長(zhǎng)的方式?jīng)_擊根植于我們內(nèi)心深處的傳統(tǒng)文化,并在這些還未成熟的新的文化面前被否定失去傳統(tǒng)文化的作用和生命力,就像還未長(zhǎng)大的孫子已經(jīng)開始不接受山里人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而奶奶面對(duì)這樣的關(guān)系卻絲毫無(wú)能為力。而這在他后來(lái)倡導(dǎo)的尋根文化中是有著明顯的體現(xiàn)的。
四、結(jié)語(yǔ)
作家畢飛宇曾說(shuō)過(guò):“作家最大的本事就是還原他所見(jiàn)到的世界,誰(shuí)還原的好,誰(shuí)就是大家,文學(xué)不是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是科學(xué)家的事。”[3]181而賈平凹也不例外,從《商州又錄》樸素、精準(zhǔn)的描寫中,能讀出關(guān)于生命的本真與人類生存的價(jià)值。從商州人普通的生命常態(tài)中能獲得一種可靠而真實(shí)的價(jià)值判斷和情感寄托,以自身深切的情感體驗(yàn)去呈現(xiàn)商州大地發(fā)生的悄然變化。并且他還將這種變化用文字的方式進(jìn)行記錄,既書寫了在現(xiàn)代文明碰撞前的記憶中的商州大地,又將這份沖擊帶來(lái)的變化巧妙地融入了他的情感和思考。并在這份深厚的拳拳之情的浸潤(rùn)下,使文章表現(xiàn)出了復(fù)雜特殊的情感體驗(yàn),并呈現(xiàn)出了獨(dú)特的審美效果以及深刻的現(xiàn)代性思考。
作家永遠(yuǎn)都是一個(gè)敏銳的發(fā)現(xiàn)者而不是一個(gè)改變者,所以面對(duì)這些變化,賈平凹也是無(wú)能為力給不出答案的,但在他的筆觸間我們還是能感受到他對(duì)于兩種文化的態(tài)度傾向,新舊文明交鋒之初,那種對(duì)抗和無(wú)交流,表現(xiàn)出了一個(gè)有社會(huì)責(zé)任感和長(zhǎng)遠(yuǎn)眼光作家的深刻思考。野蠻入侵的新的文化沖擊著我們傳統(tǒng)的文化價(jià)值觀,并且他們之間沒(méi)有和諧的相處方式,這樣的現(xiàn)狀是令人擔(dān)憂和思考的,“是否傳統(tǒng)文化就該在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下垂垂老去、被人遺忘,還是應(yīng)該平衡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到一個(g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能夠兼容并蓄的相處方式?”無(wú)疑作者也是疑惑和思索的。而賈平凹也將這一深刻的思考融入散文中,賦予了文章更加深刻的意義和內(nèi)涵。
[1]賈平凹. 商州三錄[M]. 陜西:陜西旅游出版社,2001:95-132.
[2]袁行霈. 文學(xué)理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9-118.
[3]姜廣文. “我們是一條船上的——畢飛宇方談?wù)摗盵J]. 花城,2001,(3):180-196.
[4]廉文澂. 賈平凹的散文觀及其藝術(shù)風(fēng)格[J]. 唐都學(xué)刊,2006,(02):21-27.
[5]孫際垠. 論賈平凹散文中的生命體驗(yàn)[J]. 求索,2008,(07):194-195.
[6]史玉梅.不同的視域 相同的情思——論《商州又錄》與《離別西海固》的創(chuàng)作特征[J]. 作家,2012(8):4-5.
Reflections on the colli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On the change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Jia Pingwa 's Shangzhou you lu
LI Rong
(Literature Institute,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2000,China)
ShangZhou You lu is Jia Pingwa's prose masterpiece.The article used the delicate brush strokes to describe the regional styl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imple life scenes of Shangzhou people in Shaanxi area,and observed the changes of Shangzhou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 civilization.On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also put his thinking and deep feelings into it,and through the aesthetic image of the painstaking structure, the delicate scenes of life scenes, etc to present this special complex love.On the basis of the text rea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in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digs out the reasons.
Jia Pingwa;Traditional culture;Modern civilization;Emotional experience
I207.6
A
2095-7408(2017)02-0046-04
2017-03-06
李榮(1992- ),女,新疆庫(kù)爾勒人,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