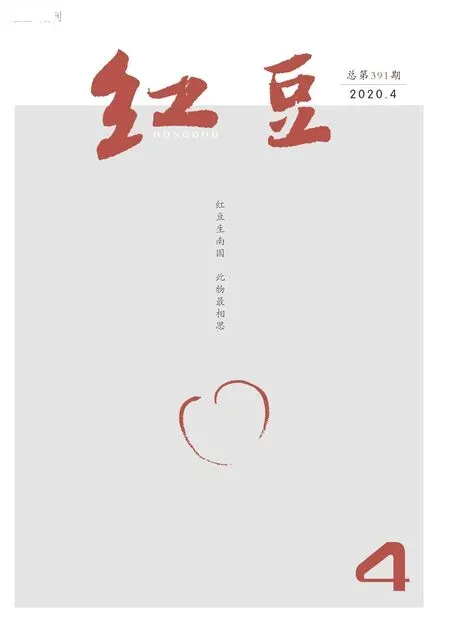好夢留人醉(短篇小說)
譚巖,本名譚興國,中國作協會員,在《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小說選刊》等刊發表作品多篇。
葉好夢和她的男朋友在江心花園購了一套房子。說好了,房子一裝修完,倆人就結婚。目前房子的裝修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隔一天,男朋友朱一民就會打來電話,說又買了什么高級廚柜,或者哪里進口的便盆,語氣中多少有些顯耀、表功的意思。葉好夢知道,與其說是在討好她這個未婚妻,還不如說在討好自己的媽,他未來的岳母——他是想借自己的口向母親匯報房子裝修的進程。在婚姻的問題上,全是媽說了算,房子裝得滿不滿意,婚期定在什么時間,全憑媽一時的高興。頭幾天,朱一民的電話打得讓人耳朵發麻,他的高嗓門兒仿佛是在向全世界宣布又買了一件什么高檔商品,可今天上午的電話卻打得吞吞吐吐,聲音低得像蚊子,原來裝修超過了預算,房子才裝到一半,錢已經用完了,問她能不能想想辦法。葉好夢知道自己這幾年節吃儉用,也存了好幾萬塊錢,可是這錢她卻不能完全做主,要回去跟媽商量。她的生活是媽管著,她的錢也都是媽給存著,在媽的眼中,她好像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什么,要你拿錢?!那先是怎么說的?房子都弄不好,還想娶老婆?!
中午時回去一說,搖著扇子扇風的母親就跳了起來。一個芭蕉扇在茶幾上拍得啪啪響:
一分錢都不能給!還說是借,那是一借永不回!你這么大了也不自己想想,他說借你就答應了?我看你是豬腦殼——
無端地受了一頓母親的臭罵,葉好夢又急又惱,腳一跌,飯也沒吃就回學校了。一人在辦公室,想了又想,還擦了一下鼻子,好在別個老師都忙,沒有注意到她的狼狽樣兒。放在屜子包里的電話響了好幾遍,她知道是男友朱一民打來的,他的一個電話就惹得自己挨了母親的一頓罵,正惱他呢,所以就任它在屜子里響,懶得理。
直到放了學,她要看時間,才從屜子里掏出電話,一看果然是四五個未接來電。可沒想到再一按鍵,那電話上顯示的號碼卻讓她很覺意外,那不是男朋友朱一民的熟悉的號碼,是一串陌生的數字,一個從沒有接過的陌生電話。
是誰?還打了四五遍?莫不是打錯了?
正在疑惑,那個號碼又打來了。
喂,請問您找誰?葉好夢禮貌地問。
你好!是葉好夢吧?
對方完全是熟人的語氣。這是一個非常——磁性的男中音!葉好夢身心一震,可仍是不相信似的遲疑:
請問您是——
哈,怎么,大教授聽不出我的聲音來了?
哎,我們小學沒有教授的。你是——
你的老同學啊——范、中、遠。
果然是他!葉好夢的心突然跳起來:
怎么會是你?!你怎么會有我的電話?!
怎么不能是我?怎么不能有你的電話?哈哈,你不想我,也不允許我想想你嗎?
范中遠在電話里開起了玩笑。
你現在在哪里啊?還在水月寺中學嗎?葉好夢覺得自己太敏感了,有些不好意思地掩飾道。他們那一個年級的同學,不少是委培生,大多分回了山區的縣里,除了她這種本身是城市戶口的人。
哈,就知道你一點兒也不關心我——早不在那個爛學校了!
范中遠告訴她,他已跳槽到一家企業工作——那是一家非常有名的企業,各國各地都設有分公司,現在他已是一個部門的經理,來聊城參加那個企業的中層干部培訓班的。
晚上有時間嗎?想請你坐坐——
電話那頭,范中遠熱情萬丈地邀請道。
還有誰?葉好夢的意思是說,還請了哪些同學。畢業后,也有幾個同學留在了聊城,可是葉好夢向來獨身自好,很少跟同學們來往。
沒有,就我們兩個!范中遠毫不遮掩地說。
如果只是一般同學,吃吃飯見見面也未嘗不可,可是,范中遠,她曾經的戀人,應該說是被自己拋棄的人,再見面能說什么?再說只有他們兩個人,搞得像約會似的,如果讓朱一民知道她還在和初戀的情人見面,他會怎么想?一時間很多的念頭蜜蜂似的在她腦子中轉著,電話那頭的人也明顯地感覺出她的猶疑來。
怎么,這么多年了,還是不想見我啊?
不不不——葉好夢急忙說。畢竟這范中遠是她的初戀情人,她人生的許多第一次都和這人相關相連,再說,她也不是那種能下得起面皮的人。
對不起呀,我差點兒忘記了,今天晚上我還有事,不能來。
是要到江心花園,看你們正在裝修的新房吧?
你怎么知道?!
電話那頭大度地笑了起來,說,也好,你先忙吧,我也不急,我在這里要待一個多月的時間——
那好,有時間我請你。葉好夢突然溜出一句,說過后又覺得很后悔,仿佛一下背上了什么責任似的。
算了,還是我請你吧,只要你肯賞光!
回到家里,一進門,葉好夢的老媽就心痛地說:
你看你!快三十歲了,還像個小孩兒,說你兩句就使氣!快,這碗銀耳湯,快喝了——餓了吧?還有一個菜,炒了就吃飯。
媽總是像個醫生似的,說要給她補這補那的,這銀耳湯她早喝膩了,就坐在客廳里,湯匙碰得碗砰砰響,那是告訴母親她在認真地喝,然后好抽個機會倒進廁所。正當她要站起身,裝作倒殘渣進衛生間的時候,電話響了,是男朋友朱一民打來的,他中彩了似的告訴她,他找朋友借到錢了。
我也沒想到,人家那么爽快!一下就是三萬,還不要息——你看我的哥們兒還夠哥們兒吧?
這朱一民就是這樣,遇芝麻大點兒事都要大驚小怪——她突然想起范中遠的成熟,什么事都處變不驚,又覺得這樣比較不好,就悶悶不樂地說:
今天晚上有點兒不舒服,看房子我就不去了。
不去了?你不是說哪里的設計要改一改的嗎?明天請的師傅就要來裝那個電視墻了——
葉好夢突然覺得很煩——簡直就跟自己的老媽一樣嘮叨,像個女人的嘴。
隨你便,你說怎么裝就怎么裝!說完,掛了電話。
圍著圍裙炒菜的母親拿著一把鍋鏟出了廚房,站在客廳那頭,警覺地問:
是不是朱一民打來的?還在說錢的事?
他說找到錢了——
這還差不多。母親警覺的臉放松了,笑著說,房子本就該他搞嘛。
這個范中遠的突然出現,一下打亂了葉好夢的生活,也擾亂了她寧靜的心。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她克制著不去接范中遠的電話,總是以自己正在上課和忙為由,在幾個電話之后,才禮節性地接聽一下。
不是說在培訓嗎?怎么不好好地聽課,又跑出教室了?她不得不多說兩句,以示熱情。
聽不進去!
請的不都是大學教授嗎?人家講得不好?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不是人家講得不好,我坐在那里心不在馬。
他有意說了一句笑話。
為什么?
想你啊!
哈哈哈,不會吧?話雖這樣說,葉好夢心里還是像吃了顆糖一樣,交流的興趣也高漲了。
說真的。我現在坐在這賓館花園里的一條長凳上,就跟我們原來學校里的那條長木凳一模一樣,也是綠色的——
葉好夢的某根神經突然被扯了一下。她仿佛看見一對學生、一對情侶,兩人都拿著書本,在含情相視,兩只手沿著那綠色的木凳,寒戰似的爬到了一起——陷入了某種往事里的女教師突然醒來似的,忙對電話中說:對不起,我要上課去了。
接下來的幾天,一天要打好幾個電話的范中遠,突然像消失了,一個短信也沒了。到了上課的時候,葉好夢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拉開抽屜,拿出電話,看有沒有什么漏掉的未接電話和短信,下課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打開電話來看。可除了男朋友朱一民匯報裝房的電話外,再也沒了那個人的任何短信。
自己畢竟是當地人,要盡地主之誼不是?不能電話也不主動跟人家打一個吧?葉好夢這樣安慰著自己。于是在放學后,辦公室里一片空蕩寂靜的時候,落寞的女教師拿起了電話。
過了半個小時,江邊小學的葉老師走出了校門。她沒像往常一樣,到停車棚去騎她的那輛自行車,而是朝校門走去。剛才,她在辦公室里看看窗外沒人,還悄悄掏出化妝盒來,對著那面小鏡補了個淡妝。她一出校門就朝馬路上張望,望那些紅色的出租車。正在她瞭望的時候,一輛銀白色的小轎車從她背后滑到了她的面前。她嚇得一讓,正惱火地想,誰開車不長眼,要壓到了自己的腳呢?車窗門卻搖了下來,露出一張多年不見的嘻笑著的臉:
葉老師好!
雖然她事前已經知道,他現在已是一個大企業的部門經理了,但仍然一時不能把眼前這個看上去事業有成,一身的名牌,開著自己的轎車來接她的人和原來的那個范中遠結合起來。啊,眼前的人變化太大了,變戲法似的。學生時代的那個范中遠,是多么的寒酸啊,一件衣服可以穿幾年,一雙球鞋可以從春天穿到冬天,請她吃個冷飲,多數是一毛錢一根的冰棒,還說那是純天然的,不含色素什么的,很少買貴一點兒的雪糕;頭發也是胡亂地搭在頭上,為了圖便宜,總是讓學校門前的那個老頭兒給他剪,剪得長一根短一根,難看死了,可現在一根根的發絲整整齊齊地排列在頭上,有條不紊,不僅是精心修理過,還保持得很好,讓人一看,就是個成功人士,在社會上是有地位的。變了,完全變了,與其說像個有錢人,但不如說像個儒雅的紳士。
看什么?不認識了?請上車啊。
范中遠見她盯著自己,便也把自己從前胸望到了后腳,見沒有什么不妥當的,便微笑著拉開了車門,一手便很自然地輕搭在葉好夢的肩頭,推她上車。
車里正放著鋼琴曲,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那首《秋日私語》。葉好夢一坐進車去,熟悉的旋律一下漫上身來,仿佛全身沉浸到往日的歲月里。
你怎么還喜歡這首曲子?幾年后出現在眼前的昔日戀人的形象,遠出于葉好夢所料,她感到很意外、很驚奇,心中涌起種種不能言狀的感覺。為了怕范中遠識破自己的內心,便總要無話找話。
范中遠一面盯著倒車鏡,熟練地倒著車,一面有意無意地說,我和別人不一樣,喜歡上的就永遠丟不了。
這話說得葉好夢臉上像被什么鉗了一下,感覺臉是紅了。她像個傻子似的又說,你什么時候還學會了開車?這真的是你自己的車嗎?
范中遠打著方向盤說,難道我不配有車嗎?
不不不,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真見鬼了,自己怎么老說錯話?葉好夢見了這扮相高貴和華麗的轎車,感覺自己一下矮了許多,說話也不靈便了。真像夢一樣,這世界完全倒了個個兒,昔日那個寒酸的男生哪兒去了?想到這個家伙昔日的那個寒酸樣,葉好夢仿佛找到了一份自信,說,想吃什么,我帶你去。
算了吧,范中遠說,還是我請吧——我不習慣女人請男人的。
這家伙還是這個脾氣。就是在他最貧寒的時候,遇到付錢的事情也總是搶在前面。這一點和她現在的男朋友朱一民不同,就是倆人出去吃一頓飯,朱一民吃完了也是坐在那里,悠閑地拿著牙簽剔牙,好像不記得還要埋單的。如果她實在坐得不好意思了,起身去付了賬,朱一民那一天就會顯得十分高興,像撿了什么便宜似的,話就會比平時多多了。嘿,怎么了,怎么老是拿朱一民和他比?葉好夢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不應該,便立刻打消了心底的那些讓人遺憾的想法,裝作輕松的樣子說:
行啊,你發達了,就該吃你的!
葉好夢現在也記不起了,多年前,準確地說是六年前,倆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可能和倆人都當學校廣播室的播音員有關吧。每次播音完,范中遠就要按上那個《秋日私語》的磁帶,校園里就到處蕩漾著那鋼琴曲的柔波。那是在大學畢業的前一年,播完了音,葉好夢一如既往地收拾桌上的那些播完的稿子,準備回家去吃飯了,說著話的范中遠突然按住了她那收拾著稿紙的手。
我們——談朋友吧。
那個時候,同學中談朋友的已不是一對兩對了,兩個人在廣播室里,還常常談論這個同學和那個同學的事情,可葉好夢從沒想到自己也會走到這一步。就在范中遠拉著她的手的時候,門外有人在喊著她的名字,約她一起回家。感覺到來人的腳步聲了,葉好夢便在慌亂中急得點了一下頭,扯出了自己的手,然后紅著臉跑出了廣播室。
不久他們便像很多同學一樣,并不遮人耳目地正兒八經地談起了朋友。學校樹蔭下的那條綠色長凳,成了他們相約相會的主要場所,有時是倆人坐在那里看書,一頭坐著一個,互不相擾,突然有一個聲也不作地離開了,過了一會兒,手里拿著兩根冰棍或者一根雪糕,笑瞇瞇地來了;有時談論修改著要播出的播音稿,倆人你一言我一語預播得繪聲繪色,有一個突然意識到對方的脈脈含情,便害羞地低下頭去。在一個月色如水、柔風輕拂的晚上,坐在那條樹影長凳上,規劃著未來、傾心長談的兩個年輕人緊緊地抱到了一起。
可是甜蜜的愛情并沒有維持多久。獨生的寶貝女兒談朋友的事兒,父母很快知道了。從她那總是回來過晚的亢奮情緒中,都是從這條道上走過來的母親首先嗅到了蛛絲馬跡。經過跟蹤和觀察,再一審問,毫無經驗的女兒什么都招了。
不行!母親武斷地說。
為什么?!女兒眼中含滿淚水。
他是委培生,從山區來的,畢業后要回到鄉下,你愿意跟他到鄉下去過一輩子?原來老媽像個克格勃一樣,什么都調查清楚了。
不是你教育我說,談朋友是會選的選人才,不會選的選家財嗎?
我看那個范中遠也并不是個什么會成器的材!會寫個廣播稿,能播個音,就算是人才?!母親教訓起女兒的目光短淺、孤陋寡聞。
一直沒有說話的父親,街道辦事處的主任發話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樣吧,抽個時間叫那個小范來一趟。
過了幾天,范中遠應邀到葉好夢的家,接受葉好夢的父母的考察。葉好夢注意到,衣著寒酸、舉止局促,沒了在學校時的自信和瀟灑的范中遠一跨進自己的家門,向來喜歡以貌取人的父親就首先皺起了眉頭,葉好夢心頭一涼,完了,自己唯一的支持者也轉變了立場了。
果然,考察變成了審察,詢問變成了審問。審問完畢,葉好夢承認,自己也很難受于自己的父母對范中遠露出的鄙夷神色。
以前的事情我們不追究了,希望你們的朋友關系就此而止——你們不會有什么結果的:不是我們嫌你家貧,是我們好夢不可能回到你那個山區,只有山區嫁到城市,哪有城里人睜著眼睛嫁到山區去的?我們跟夢兒說了,如果她不聽,我們就斷絕母女關系、父女關系——
聽完這最后的通牒,范中遠像望著救命稻草似的望向葉好夢,可是坐在她母親身邊的葉好夢低著頭,并不望他一眼。年輕小伙兒急切希求的目光漸漸暗淡了。他站了起來,朝葉好夢父母鞠了一個躬:
伯父,伯母,打擾了!
這個時候,電光一閃,窗外響起了雨點聲。
范中遠告辭出門,一直低著頭的葉好夢,抬頭見了窗外的雨點,本能地抓起雨傘要去送他,可是被母親厲聲喝住了:
送什么送?你給我站住!你不要再和他有什么瓜葛!
已走出門外的范中遠,聽見門內的聲音,只是站了一瞬,然后一低頭,走進了冰冷的雨水中。
怎么樣,伯父伯母都還好吧?葉好夢見了范中遠,與他學生時代的形象判若兩人,正在感慨萬端,回憶往事,駕車的范中遠突然問道。
嗯,都退休了——葉好夢一面應答著他的話,一面想:如果現在西裝革履寶馬香車的范中遠出現在自己的爸媽面前,他們會怎么想呢?會后悔嗎?她葉好夢就感到后悔,感到一種從心底泛出來的淡淡的酸味兒,怨愁。怎么那么聽爸媽的話呢?叫不跟他談朋友了,就不談朋友了;叫不跟范中遠來往了,就不跟他來往了。為了避免與他單獨相處,她聽母親的話,學校廣播室的播音也推辭不干了,說自己患了咽炎。一天要去坐好幾回的那個校園的長條凳,從此也讓它空寂在樹影下,起初還見范中遠一個苦苦等候的影子在那里坐著,不久,那里成了另一對戀人聚會的天下。在校園里走著走著,突然遠遠地望見范中遠站在過道上,明顯地是在等待著、期待著,她便繞一個道,繞一個大大的彎也不去見他,或者夾在一幫同學中,說說笑笑地一路走過,裝作沒有看見他那失望的面孔。范中遠給她寫的條子、寫的信,有時是看一眼就丟到一邊,有時是連看也不看就原樣退了回去。望著范中遠那段日子的失魂落魄和一臉憔悴,有時也很難過,可又一想,怎能丟下爸媽去跟他處朋友啊?再說,也不能真的就跟他到山區生活是不是?就讓他死了這份心吧。
可沒有想到的是,事過多年,他那一份執戀自己的心仍在燃燒。在范中遠那時而喃喃時而自我調侃的敘述中,葉好夢知道昔日的戀人一顆灼熱的心并沒有變,也知道了自己當年對他造成了怎樣難以彌補的傷害。這既讓葉好夢感動,更讓她一份虛榮的心感到滿足。這個看上去如此成功的男人仍然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依然是自己至死不渝的追隨者。或許那西餐廳搖曳的燭光、讓人心醉的音樂,適合追憶往事、談情說愛;或許出于自己當年那近乎殘忍的決絕,對人傷害后的覺醒和對眼前這個癡情人的憐憫;或許本身就是喜歡這個男人,只是由于父母的干擾才禁錮著自己的熱情,當幾杯紅酒下肚,臉上泛起了紅光,在一種追憶式的語調停下來的間歇,四目相對,女主人公害羞地低下頭去的時候,男主人公適時地伸出了手,握住了女主人公的纖纖玉腕。一種幸福的電流貫穿葉好夢的全身,她感到自己的心也在幸福又充滿期待地顫抖著,她仿佛回到多年前,那個月華如水的初戀夜晚。
好夢——男人捏著她依舊白嫩的手,深情呼喚著,喘息聲變得急促,他欲站起身來,將有所作為。
不——
葉好夢大叫了一聲,附近的客人都回過頭來。這一聲驚叫也阻止了范中遠的動作,他頹然地坐回到座位,不安地關心地問:
怎么了?
葉好夢意識到自己反應的過分和唐突,甚至缺乏修養。可是,自己是有男朋友的啊。她幾乎是痛苦地搖了搖頭,然后下了決心似的說:
對不起——不早了,你送我回家吧。
當范中遠開車送她到家的時候,葉好夢像是要急于擺脫他似的,推開車門就跳了下去,說了一聲“再見”,就穿著高跟鞋噔噔噔地跑向自己的家門,也沒有起碼的禮節性的揮揮手,站在那里目送人家的遠去,或者禮節性地問別人要不要進屋去坐坐,她只顧逃離這輛車,逃離這個男人。在車窗里的范中遠不解的目光中,啪的一聲,進屋去的葉好夢關上了鐵門。
不是說晚點兒回來的嗎?怎么這么早?還在廚房里收拾什么的媽見了問。
葉好夢不理母親,徑直進了自己的房,砰地關上了房門,給家人感覺是不要打擾,她要備課,要工作了。她坐到了電腦前,有些慌亂地掏出了電話。她要打給男友朱一民,要朱一民來陪陪她,陪她說說話,或者陪她到江邊去走走,總之今天晚上必須要和朱一民在一起。她仿佛已感到了什么危險,朱一民就是她安全的屏障。
可是,連打了幾個電話,他都沒有接。過了好一會兒,電話打回來了。
老婆,我在打牌,有什么指示?油腔滑調的朱一民,雖然倆人還沒結婚,但他已經覺得是板上釘釘,十拿九穩了。
聽了葉好夢的話,朱一民不解地說,這都什么時候了,還要到江邊去散步?!我說老婆,你今天就不去了吧,過一天我陪你行不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今天手氣特好,已經贏了一臺電磁爐了——
啪的一聲,那邊還在說,葉好夢已經關上了電話。庸俗,真庸俗!怎么攤上了這么一個庸俗的男人!葉好夢憤憤地想。接著她又想,自己難道不庸俗嗎?不庸俗,會有今天的后悔?
她突然感到一種難受。她的臉仍在發燙,心仍在亂跳。她雙肘搭在電腦前的那一片桌上,撐著自己發燒的臉,望著臺燈燈光外,那一片讓人舒適又暗淡的空間,心想:自己該怎么辦?
接下來的幾天里,男友朱一民單位組織出去旅游,臨走,他打電話問葉好夢要不要帶什么紀念品,平時熱情萬丈的葉好夢,這次卻冷冷地說,隨便!前戀人范中遠也打來電話,說留在本市的幾個老同學相聚,請她也參加。葉好夢略略沉吟了一下,爽快地答應了。那一次的酒,男男女女都喝得天翻地覆,熟悉他倆談過戀愛的人更是開他們的玩笑,讓葉好夢既覺得甜蜜,又覺得像針一樣刺著她的心。范中遠送她回家,上車的時候,她軟軟地搭在了他的身上。
以后便是經常的約請。
好多天都沒有回家吃飯,不知道情況的母親見了總要問:
又跟朱一民出去了?
葉好夢懶怠回答。當媽的又問,你們上館子,是朱一民出錢還是你出錢?
葉好夢沒好氣地說,都是人家請客!
媽便放心了:這個朱一民,怎么大方了——呃,你們那新房,裝得怎么樣了?你也沒去看看?
葉好夢更煩了:都是包工——有什么好看的!
一句話硌得媽一愣,不認識似的望著她:這閨女,現在怎么這么大脾氣?
是的,現在提起朱一民,提起房子,提起結婚,她都煩。不煩的是范中遠,一想起他,她的心就在笑,一直笑到了臉上。在她過生的時候,記性很好的范中遠請花店給她送去一束鮮花,送到了學校。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她男友朱一民送的。那一天,范中遠還帶她到名牌店買了一套昂貴的衣服,葉好夢推辭不要。范中遠說,他們戀愛時,他一直想送她一個什么紀念品,可是窮啊,除了送冰棍雪糕,什么也送不起,現在是將功補過。范中遠又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又說,你也穿得太——節約了。她知道,斟詞酌句的范中遠是在照顧她的自尊。的確,在同學們的聚會中,她穿的雖然說不上最低檔,但也絕對不是上檔次的,像范中遠一樣,一出場就惹人注目的。如果她是范中遠的妻子或者女朋友呢?她還會是那樣可以讓人忽視嗎?她不敢想。
在一個周六的晚上,倆人吃了晚餐之后,突發奇想,竟然開車穿了幾條街道,找到了昔日的師院,悄悄溜進了母校的操場。在操場的那一片樹林,那昔日放置長條凳的地方,他們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時光。他們又像昔日的戀人一樣,擁抱到了一起——不過不同的是,昔日人約黃昏、月上柳梢的那輪明月,是月華如水,了無輕塵,可現今,那柳上的月亮已是殘缺,并罩著一團烏云。
在當晚回家的路上,倆人都像余興未盡,興致勃然,都沉溺在追憶往事的興奮中。葉好夢已是身心如水,她如何堅硬的防線都被范中遠融化掉了。她已決定,既然范中遠還如此愛她,她就要嫁給他,后悔還來得及。
范中遠卻嘻笑著說,就怕你爸媽不認我這個女婿啊。
葉好夢聽了,有些難堪,卻堅決地昂起頭來,說,不怕,這回我自己做主!
范中遠聽了,臉上飄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
葉好夢的手搭在開車的范中遠的腿上,仿佛是要做什么強調:
中遠。
什么?
有一句話,我一直想對你說——好幾年了。
什么話呀?說你愛我?范中遠偏過頭來,仍是一臉的戲謔。
不是。我想就我的父母幾年前對你的不公平,表示道歉。真的,如果你不解恨,怎么樣對我都行!
范中遠聽了,漸漸收起了嘻笑的神情,專注地開起車來。夜色中,這輛銀色的轎車穿過一團團迷離的霓虹燈光。
現在是反過來,是葉好夢向范中遠求婚了,范中遠答應她要好好想想,過兩天再答復。葉好夢雖然有些不高興,但畢竟是自己先負于人,人家要考慮兩天,這要求也并不過分嘛。憑自己在范中遠心目中的分量,她也不焦急,知道他遲早會答應的。他的遲疑,在葉好夢看來,只不過是男人心胸的狹窄,嫌她跟朱一民談了兩年的戀愛。在這一點上,她明確地告訴他,她的母親管得很嚴,在與朱一民處朋友的兩年里,除了實在避免不了的擁抱親吻,并沒有什么實際性的接觸,要他放心好了。
葉好夢自己也放心地耐心等了兩天,第三天,葉好夢主動給范中遠打電話,可是電話通了,卻沒人接。發短信,可發出去也是石沉大海。葉好夢慌了,她找到他們培訓的地方,可是人家告訴她,他們的培訓一個星期前就提前結束了。
就在葉好夢心里充滿猜測和焦慮的時候,一天晚上,她正在電腦前強收心思,準備第二天的公開課,范中遠發來了短信,很長,三次才發完。看完了短信,葉好夢無力地靠在了椅背上。
原來,范中遠一直沒有忘懷由于貧窮受到她的父母羞辱的一幕,那一天從她的家門走出去,踏進冰冷的雨水中時,他就暗自發誓,一定要報這個仇,雪這個恥,并讓他們終身后悔。他所有的拼搏,都是為了這個復仇的計劃。他打算先與她以再續前緣談朋友為名,談個幾年,拖個幾年,然后再拋棄她,讓她的父母守著這個三十多歲的老姑娘著急。可是那天晚上,葉好夢真誠的道歉改變了他的想法,他突然覺得自己很無聊,所謂的復仇也毫無意義。他說,他雖然愛她,但是理智讓他不能愛,一個容易搖擺,沒有主見,更重要的是在他困難的時候可以一眼不眨地離開他的女人,不適合跟他一起打拼天下,不適合做他的終身伴侶。朱一民裝修房子借到的錢,是他有意指示朋友借給他的,原打算作為他實施報復計劃,讓他退出與他競爭葉好夢的籌碼。現在那三萬塊錢,他打算作為同學、朋友,送給她的結婚賀禮,并祝她生活幸福。
讀到了最后一句話,葉好夢感到手腳冰涼。她沒有想到,當年自己的家人是如此沉重地傷害了他,也沒有想到,自己的一句并不經意的話,化解了多年的仇恨,也挽救了自己。
真的是得到挽救了嗎?臺燈下的女子無神地望著那一片黃亮的燈光。她知道自己的這一生,不會再有什么讓人寢食不安的愛情了。
責任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