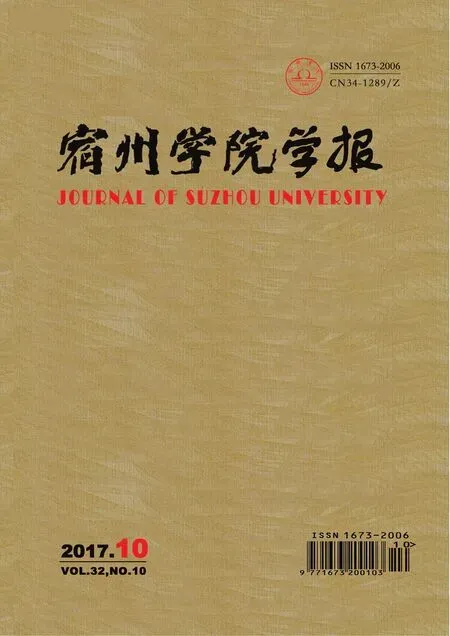男性形象視角下吉本芭娜娜作品中的女性意識研究
鄭科研,封 霄
1.宿州學(xué)院外國語學(xué)院,宿州,234000;2.華中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武漢,430079
男性形象視角下吉本芭娜娜作品中的女性意識研究
鄭科研,封 霄
1.宿州學(xué)院外國語學(xué)院,宿州,234000;2.華中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武漢,430079
戰(zhàn)后日本女性文學(xué)挑戰(zhàn)以男權(quán)為中心的傳統(tǒng)文學(xué),宣揚女性強烈的生命意識和主體意識,尤以吉本芭娜娜的文學(xué)作品更為突出,體現(xiàn)了強烈的女性意識。基于男性形象視角對吉本芭娜娜作品中展現(xiàn)的女性意識進行探究,將男性形象劃分為性格發(fā)生變化和性別發(fā)生變化兩大類,在此基礎(chǔ)上分析發(fā)生改變的性格特征及其變化過程,揭示男性形象發(fā)生嬗變根源于作家女性意識的不斷增強。從男性形象這一新視角表現(xiàn)女性意識確立和發(fā)展的過程,進一步豐富了對吉本芭娜娜作品中女性意識的研究。
吉本芭娜娜;男性形象;女性作家;女性意識
日本當(dāng)代女性作家吉本芭娜娜出生于1964年,本名吉本真秀子,1987年憑借作品《廚房》獲得日本第六屆“海燕”新人文學(xué)獎,之后再度獲得泉鏡花文學(xué)獎等多個日本文學(xué)大獎。作品《廚房》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在日本以及世界文壇掀起了一股熱潮,奇跡般地營造了一種“芭娜娜現(xiàn)象”。吉本芭娜娜的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nèi)發(fā)行,因其在國內(nèi)外的巨大影響被日本評論界稱作“當(dāng)代文學(xué)天后”。
1 女性意識及吉本芭娜娜作品中女性意識的表現(xiàn)
1.1 女性意識及其在日本的發(fā)展
研究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性意識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重大課題。女性意識是指女性在客觀世界中,作為主體所表現(xiàn)出的地位、作用和價值的自覺意識。女性意識的主旨是使女性認識“人”與“女人”的概念,使女性認識到女性與男性同為“人”的自然特征,是無差別的。女性意識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隨著女性運動的推進,女性意識得到了不斷地發(fā)展。自古以來,日本社會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特別是在男性的心中“夫是天”,“女人”只是丈夫的附屬品,只能在家老老實實地做“女人”。
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女性運動影響下,日本女性也開始了自我意識的覺醒,開始追求兩性平等和女性自身的權(quán)利。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占領(lǐng)軍進駐日本之后,多項法律條款迅速制定、頒布,對女性的選舉權(quán)、受教育權(quán)和工作以及婚姻中各項權(quán)利以法律的形式給予規(guī)定,保證了女性的權(quán)益[1]。20世紀(jì)60年代開始,女性的就業(yè)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并開始走上政治舞臺。盡管法律不能夠立即解決漫長的封建時代遺留的陳規(guī)陋習(xí),但是,女性的社會地位逐步得到了實質(zhì)性地提高。由此可見,在女性運動的推進過程中,日本女性受到女性運動的影響,思想上逐步走向覺醒,女性意識不斷增強。
在文學(xué)方面,女性意識經(jīng)歷了從有到無、從弱到強的發(fā)展過程,并在不同時期體現(xiàn)出不同的內(nèi)涵和表現(xiàn)形式。縱觀日本文學(xué)歷史的長河,日本的女性作家雖然也曾出現(xiàn)過創(chuàng)作高潮,留下不少佳作,但男性作家仍舊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男性作家進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時候,總是會不自覺地將體現(xiàn)“夫權(quán)”的思想意識帶進他們的作品中,在男性的文學(xué)世界中,有著大量的“出色”的女性們,她們溫柔善良、恭謹謙讓,被描繪、塑造成男性理想中的“賢妻良母”的形象。男性以這種方式塑造文學(xué)世界中的理想女性,又反之以這樣的女性形象來教育和誘使女性,使她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屈從于男性的價值體系。而在這個過程中,女性自身的意識、感受和愿望蕩然無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隨著日本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物質(zhì)生活的日益豐富,女性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日本文壇上出現(xiàn)了大批才華超群的女作家,女性作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出現(xiàn)了高潮。女性作家的作品題材涉及各個領(lǐng)域且數(shù)量繁多,同時也出現(xiàn)了許多優(yōu)秀著作。有評論家認為,這一時期的女性作家在日本文壇起到了先驅(qū)的作用[2]。女性作家在文本內(nèi)容、寫作方式等各方面對傳統(tǒng)日本文學(xué)都有突破,她們從不同角度沖擊以男權(quán)為中心的傳統(tǒng)文學(xué),用文字書寫日本女性的自覺意識和自我觀念,張揚女性強烈的生命意識和主體意識。
1.2 吉本芭娜娜文學(xué)作品中女性意識的表現(xiàn)
吉本芭娜娜作為一名新時期的女性作家,其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女性意識受到了研究者們的廣泛關(guān)注。由于她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都是女性,所以大部分研究者將研究視角專注于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描寫。吉本芭娜娜以其特有的女性的細膩,憑借自身敏銳的洞察力和對生活的切身體驗,發(fā)現(xiàn)了傳統(tǒng)女性的轉(zhuǎn)變,用女性特有的視角和筆觸,從女性的角度揭示社會和生活對女性的不公,塑造了眾多新時代女性形象,反映社會和生活對女性造成的不幸與創(chuàng)傷[3]。
在作者的筆下,女性的柔弱和情感被刻畫得真實而充分,女性的內(nèi)心世界被描寫得豐富而強大,體現(xiàn)了女性作家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女性意識。在女性運動的推動下,日本女性開始走出家門,走向社會。而在文學(xué)作品中,努力追求獨立和自由的女性、對封建社會制度進行反抗的女性和事業(yè)上不可或缺的成功女性等大量地涌現(xiàn)出來。 作家筆下的各式各樣的女性形象都不同程度地體現(xiàn)了女性的抗?fàn)帯⒎磁押妥詮姴幌ⅲ浞值乇磉_了女性意識逐漸強烈的自覺性和日益豐滿的內(nèi)涵。
筆者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作者筆下女性形象發(fā)生轉(zhuǎn)變的同時,男性形象也發(fā)生了一系列的嬗變,究其原因,依然是作家女性意識的體現(xiàn)。女性作家通過對女性形象新特征的描寫,直觀地展現(xiàn)了新時期女性發(fā)生的變化,表現(xiàn)了女性內(nèi)心的強大和高尚的人格魅力,體現(xiàn)出強烈的女性意識。但在大量的作品中還有一個顯著的創(chuàng)作特點不容忽視,那就是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嬗變也十分顯著。吉本芭娜娜的筆下就有大量的、失去傳統(tǒng)光環(huán)的男性形象,這些男性形象所具有的特征仍然能表現(xiàn)出作家對女性身份的認可、對傳統(tǒng)桎梏的推翻,體現(xiàn)了強烈的女性意識。
2 吉本芭娜娜作品中男性形象體現(xiàn)的女性意識
吉本芭娜娜的筆下,作品的主人公多為女性,并且多具有共同特征:年輕,經(jīng)歷過親友的離世,生活中令人壓抑的孤獨感等[4]。但同時這些女性主人公又表現(xiàn)出堅強,對生活的熱愛,找尋到心靈的救贖,對他人展現(xiàn)了自身積極向上的魅力。毋庸置疑,研究女性文學(xué)中的女性形象能夠透視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女性作家所表達的女性意識。但是,作為小說人物形象的另一半構(gòu)成,男性形象的特征變化也不容忽視。
在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較多的男性形象失去傳統(tǒng)的性別特征,發(fā)生了嬗變。芭娜娜用模糊性別界限的描寫來縮小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距離,強烈地體現(xiàn)了作家的女性意識。她在多部作品中向讀者展現(xiàn)了性格特征上帶有女性傾向的變“性”人和性別徹底發(fā)生改變的變“性”人兩大類男性形象。男性形象的這兩種變化都體現(xiàn)了芭娜娜滲透于文本的強烈的女性意識。
2.1 變“性”人——性格
職業(yè)實用性體育教學(xué)的重點就是保證針對學(xué)生所進行的體育鍛煉項目不僅僅是終身性的,而且是與自己的職業(yè)專業(yè)特點所相匹配的,同時對于鍛煉計劃的制定與執(zhí)行不僅僅是科學(xué)性的,合理性的,同時也是利于根據(jù)專業(yè)和身體的實際條件隨時進行調(diào)整的,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學(xué)生通過職業(yè)實用性體育教學(xué),能夠逐漸了解并掌握與職業(yè)病相關(guān)的預(yù)防與糾正,例如矯正操、保健操以及生產(chǎn)操等,最終為學(xué)生終身體育的踐行奠定堅實的基礎(chǔ)。
在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有這樣一類男性形象的描寫非常值得關(guān)注:雖然他們都是男性的身份,但是其行為特征大都帶有女性特征。傳統(tǒng)男性形象所具有的高大威猛、堅毅果決的性格,在這類男性的身上顯現(xiàn)得甚少。對于這些男性的描寫,芭娜娜在作品中過多地出現(xiàn)了近似評價女性的詞語和話語。
作品《廚房》中的雄一就是其一[5]。作品中“我”在祖母去世之后,失去了世上最后的親人,從此便孑然一身,孤獨于世了。就在這時田邊雄一意外地出現(xiàn),他“四肢修長,容貌清秀”,在“我”費了很大力氣之后才想起來,他就是奶奶常常說起的花店里的“可愛的男生”。僅因以前曾受到過祖母的照顧,就與祖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祖父的葬禮那天,雄一哭得十分傷心,眼睛腫了,眼淚不停地落下。而這樣的傷心、哭泣,通常更符合對女性的描寫。
在“我”深感絕望的時候,雄一真誠地邀請“我”去他們家住,得到我肯定的答復(fù)之后,他“笑著離開了”。在描寫雄一悲傷情緒時,他“連飯也吃不下去”,“傷心不已”,面對美影,他邊用手臂抹眼睛邊說:“好想聽你講的笑話,真的,想聽得不得了。”這樣的懇求方式似乎讓“我”看到了一個傷心的、無助的女性形象[6]。可以說,雄一從外表到內(nèi)心都透露著纖細、柔弱、敏感、多愁的性格特征。而以上這些性格特征的描寫通常更傾向為女性。
在作品《月影》中僅出現(xiàn)了兩個男性人物:阿等和阿柊。作品中的阿等是“我”相戀多年,在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的戀人。在這起事故中,還有一位遇難者就是阿柊的女朋友由美子。一次阿等出門的時候,順便開車送由美子去車站的途中,發(fā)生了意外。失去親人和戀人的痛苦讓“我”和阿柊都無法正視未來的生活。小說中兩兄弟的行為都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了女性的性格特征。
首先是“我”的戀人——阿等。小說開篇就交代了一個小鈴鐺,“我”和阿等相識時“我”送給他的。正是因為這個鈴鐺,“我”對僅僅相識幾天的阿等“大生好感”。“我”將小鈴鐺“極其無意”地送給阿等時,他小心翼翼地接過,放在手心,并且還用手絹將之包好。當(dāng)時“我”的反應(yīng)是“實在是太異常了”,“大為詫異”。相戀以后,阿等便一直隨身攜帶著小鈴鐺,他將鈴鐺懸掛在月票夾上,每次掏出來的時候,都能發(fā)出叮鈴鈴、叮鈴鈴的響聲。用手絹包好獲贈的鈴鐺,從此隨身帶著這一鈴鐺,并不時地發(fā)出響聲,這樣的行為多少都帶有些女性的特點。和阿等相比,阿柊的身上則表現(xiàn)得更加顯著。
“阿等有一個幾近古怪的弟弟,無論思維方式,還是待人接物,都稍有些與眾不同。”過去阿柊就一直使用女性的“我”來稱呼自己*日語中,在人稱代詞的使用上,男性用語和女性用語是顯著不同的。在稱呼自己時,ぼく、おれ等詞通常僅限于男性使用,而女性則使用あたくし、あたし、あたい、うち等女性的專用語。。而且,在行為上,阿柊自從戀人由美子死后,就一直穿著她的遺物——一身水兵服。雙方父母的勸告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雖然悲傷會讓人意志消沉,悲痛欲絕,但是,身著女性衣服,泰然出入公共場合,不理會家人和朋友的勸導(dǎo),著實罕見和怪異。
芭娜娜在描寫筆下這類男性形象時,并沒有表現(xiàn)出男性堅強、果敢等特征,相反更多的是柔弱、敏感等女性化的性格特質(zhì)。通過這些男性形象可以看出在芭娜娜的作品中,人物的性別特征模糊了。芭娜娜通過這種有意識地模糊性別界限,來消除男女差異,縮小他們之間的距離。
2.2 變“性”人——性別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出現(xiàn)在吉本芭娜娜的代表作《廚房》中的變性人——惠理子。她原本是田邊雄一的父親,之前作為男性時名叫田邊雄司。田邊雄司和妻子感情深厚,相戀時,不顧父母的養(yǎng)育之恩,一起私奔。在妻子因病去世后,雄司對亡妻的死無法釋懷,抱著“反正今后再也不會喜歡別的人”的想法,決定將自己變身成女性,并改名為惠理子。
小說中,從美影第一次見到惠理子開始,就不斷地、反復(fù)地強調(diào)她的美:“門‘喀啦啦’地開了,一個美極的婦人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一頭柔順的披肩長發(fā)”,“細長的雙眸深邃且神采動人,嘴唇形狀優(yōu)美,鼻梁高挺”。“那么修長的手指、優(yōu)雅的言行舉止、美麗的容貌,怎么可能?”“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美影再也裝不下去,再也不得不表現(xiàn)出自己的詫異。
初次遇見,美影被惠理子的美麗所震驚。當(dāng)美影從雄一的口中得知了“她”原來是“他”的時候,美影更加細致地觀察了惠理子,雖然發(fā)現(xiàn)了缺憾之處,但是仍然覺得這樣的一個人十分有“魅力”。美影認為自己從未見過這樣的人,不僅外貌美麗,所散發(fā)的女性魅力也是不可抵擋的。在美影看來,惠理子是一個樂觀、堅強和熱愛生活的“女人”,家里到處都是花花草草,利用上班前的短暫時間照顧它們; 一個人帶著年幼的雄一打拼,努力把雄一培養(yǎng)成心地善良的孩子,不依靠親戚,不依靠任何人。惠理子和美影聊天時曾經(jīng)提到:“做女人也很辛苦啊。……我也是在撫養(yǎng)雄一的時候漸漸領(lǐng)悟到的。那時候真得吃了好多苦好多苦。”美影對“她”的評價是“這個實力派的母親”。因此,透過美影的視覺與感受,都將惠理子描繪成一個美艷、充滿女性魅力、使用女性用語和樂觀向上的母親的形象。
在惠理子留下的遺書中,她這樣寫道:“我想,至少這封信要用男性用語來寫,也很努力地嘗試了,可還是覺得怪怪的。覺得不好意思,羞于下筆。當(dāng)了這么長時間的女人,本來還一直以為再說他的某處還有那個男性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存在,女人的皮相只是我的任務(wù)。現(xiàn)在看來,身心都變成女人了,是名副其實的母親啊。好笑。”雄司為了愛情,近乎以殉道的方式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同時,也以“變性”這種超自然的方式改變了兒子雄一的生活。而最終,在生命的最后,惠理子認為自己“身心都變成女人了”。
作品中還有一個變性人——知花,惠理子工作的店的負責(zé)人。作品中并沒有將這個人物形象描寫得像惠理子那樣“美艷”,那樣“充滿女性魅力”,“身材細長高挑,服裝十分華麗合體,為人也很溫和”。并且,從性格上更像是一個女性形象。例如,在地鐵站,一群小學(xué)生惡作劇,掀起了她的裙子,導(dǎo)致她一直哭,哭個不停。美影總覺得和知花在一起的時候“自己更具有男性氣概”。
因此,作者利用當(dāng)時科技水平無法實現(xiàn)的“變性人”這一虛構(gòu)的藝術(shù)形象完成了男性和女性在自然性別上的跨越,而且,兩個變性人的設(shè)置均是男性變性成為女性。傳統(tǒng)觀念中的男尊女卑、男性高高在上的思想受到了挑戰(zhàn)。
3 男性形象的改變與女性意識的關(guān)聯(lián)
在女性形象不斷發(fā)生改變的過程中,受到女性意識的影響,女性作家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同樣逐步在發(fā)生轉(zhuǎn)變。文學(xué)史中多數(shù)將男性塑造成英雄、榜樣或至少是帶有社會和家庭責(zé)任感的形象。幾乎所有男性都被打上了深深的男權(quán)意識烙印,被放大為響當(dāng)當(dāng)?shù)哪凶訚h,充滿英雄氣概。然而,伴隨著女性意識的發(fā)展,文學(xué)作品中的男性形象開始發(fā)生變化。吉本芭娜娜作品中的兩類“變性人”的出現(xiàn)均是作家女性意識的體現(xiàn):
第一,戰(zhàn)后時期,伴隨著女性意識的發(fā)展,文學(xué)作品中的男性形象開始發(fā)生變化。丑化男性、貶低男性也成為了一種謳歌女性的創(chuàng)作手法。“女性作家通過日常生活體驗,在自我意識的基礎(chǔ)上已經(jīng)認識到男性喪失自我、形象矮小化的社會百態(tài)。”[9]作品中,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共同構(gòu)筑成一個完整的藝術(shù)世界。女性意識的發(fā)展,促使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對女性形象的塑造發(fā)生改變。挑戰(zhàn)傳統(tǒng)、自我意識強烈的女性形象大量地出現(xiàn)在女性作家作品中。隨著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逐漸強大,男性不再是女性唯一的依靠,同時也不再那樣可以被“依靠”,傳統(tǒng)的男性形象被弱化、矮小化。
在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由于受女性意識的影響,作品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已然發(fā)生改變。男性變得具有女性特質(zhì),性格上缺少傳統(tǒng)男性的剛毅、果敢,變得柔弱、敏感,很多時候會從女性主人公身上汲取溫暖和救贖,最后才得以從困境中走出來。與此相對的,是作品中傳統(tǒng)女性形象的柔弱被打破,更突顯女性意識的強烈。
第二,在作家筆下,性別上男性特質(zhì)的消失成為表現(xiàn)女性意識的極端方式。吉本芭娜娜的代表作《廚房》發(fā)表于1987年,而在現(xiàn)實中,直到1998年日本才有了第一例變性手術(shù)。此時,小說已經(jīng)發(fā)表了 11年。因此,“變性人”只是作家當(dāng)時虛構(gòu)的一個藝術(shù)形象。在小說中設(shè)置“變性人”這一人物形象,既吸引了讀者眼球,滿足了大眾好奇心,同時,這樣的人物形象又表現(xiàn)了作家強烈的女性意識。在自然性別的分類下,男性和女性是截然對立的兩方。而在當(dāng)時科技水平下無法達成性別轉(zhuǎn)變的情況下,在作品中出現(xiàn)的“變性”的人物形象,承載著作家創(chuàng)作中大膽的想象和對性別的訴求。
在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中,出現(xiàn)了兩個變性人的人物形象,通過這種虛構(gòu)的人物形象,作者清晰地表明了男性不再處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再具有不可一世的“君王”般的形象。作家自然性別上的跨越,將男性形象的光環(huán)踐踏于腳下,體現(xiàn)了更為強烈的女性意識。
因此,女性作家用這兩種男性形象的轉(zhuǎn)變方式表現(xiàn)了男性傳統(tǒng)形象已然發(fā)生改變,男性和女性不再是傳統(tǒng)的對立面的關(guān)系,女性不再是處于男性統(tǒng)治下的卑微的階層,男性也不再有高高在上、令女性仰望的姿態(tài)。男性形象的這種轉(zhuǎn)變反映了女性的自覺意識和自我觀念,體現(xiàn)了女性作家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女性意識。男性形象的嬗變體現(xiàn)了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傳統(tǒng)男性形象的挑戰(zhàn)和推翻,體現(xiàn)了女性作家強烈的女性意識。
4 結(jié) 論
無論是性格特征的明顯轉(zhuǎn)變,還是自然性別的徹底改變,吉本芭娜娜在作品中都對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制思想發(fā)出了挑戰(zhàn)。在傳統(tǒng)社會制度中,男性的身體特征和氣質(zhì)模式都是高貴的、優(yōu)越的,而女性的身體特征和氣質(zhì)模式較之男性則是次等的。發(fā)生嬗變了的男性形象,失去了傳統(tǒng)男權(quán)制思想中男性所特有的高貴的性別特征。女性作家用模糊性別界限的描寫來消除男女差異,縮小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距離,體現(xiàn)出女性意識的增強。女性作家更是用現(xiàn)實生活中還沒有出現(xiàn)的虛構(gòu)情節(jié)——變性的方式,實現(xiàn)了對傳統(tǒng)意識的徹底反叛,進一步豐富了女性意識的表現(xiàn)。
[1]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與表現(xiàn)[M].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0:264
[2]王宗杰.試論當(dāng)代日本女性文學(xué)的特征[J].東北師大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5(5):139-144
[3]路邈.試論吉本芭娜娜的創(chuàng)作特點[J].日語學(xué)習(xí)與研究,2002(1):80-82
[4]郭燕梅.吉本芭娜娜文學(xué)的女性主義解讀[J].語文學(xué)刊,2012(2): 107-108
[5]吉本芭娜娜.廚房[M].李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113
[6]韓艷平.《廚房》中的人物形象分析[J].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4,33(1):70-73
[7]吉本芭娜娜.哀愁的預(yù)感[M].李重民,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143
[8]吉本芭娜娜.蜜月旅行[M].張唯誠,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9
[9]水田宗子,葉渭渠.日本現(xiàn)代女性文學(xué)集[M].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2012:39
(責(zé)任編輯:武艷芹)
2017-08-20
鄭科研(1984-),女,安徽淮北人,碩士,助教,研究方向:日本文學(xué)、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
10.3969/j.issn.1673-2006.2017.10.019
I106.4
A
1673-2006(2017)10-007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