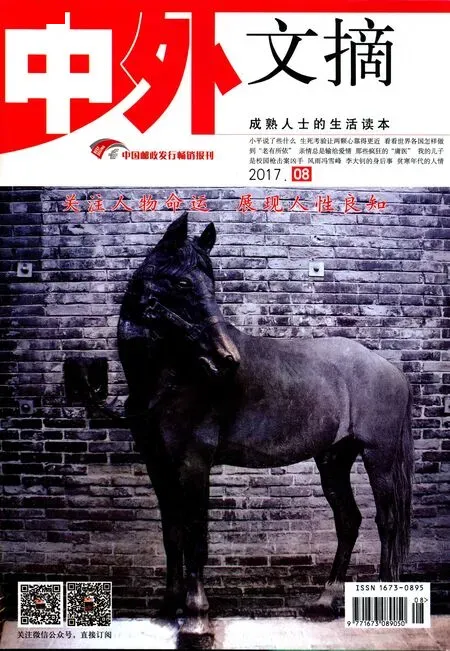新婚三日無大小的誤用
□ 李寶臣
新婚三日無大小的誤用
□ 李寶臣

“新婚三日無大小”作為俗語流傳甚廣,至今仍有人挾此觀念,在他人婚禮上恣意胡為,調戲新娘,丑態百出。往往攪亂喜慶祥和場面,甚至樂極生悲釀成慘劇。近些年來類似事件媒體報端亦多有報道。
兩性結合天生排他,即使一對新人受習慣觀念束縛盡量忍耐,但嬉鬧過度也很容易導致至友親朋反目成仇。清光緒年間的申報附贈畫刊《點石齋畫報》記載:康熙年間,上海寶山縣因一人在婚禮上調戲新娘而被新郎訴訟于官。同期的吳有如《風俗志圖說》記載了發生在寧波的悲劇,一男子潛入洞房偷聽新人私語被發現,新郎怒不可遏以剪刀將其扎得血肉模糊。
“新婚三日無大小”可能是原始掠奪婚時代的遺風,不過,早期戲謔的對象是搶婚的受益者新郎,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記:汝南人杜士娶妻,賓客戲弄杜士,將其捆綁捶打倒懸致死。《北史》“后妃”記:北齊文宣帝高洋娶段韶之妹,韶妻元氏沿用“俗弄女婿法”杖打皇帝,隨著歷史變遷,“杖女婿”逐漸被“戲新娘”替代。另一種可能是族外群婚制向對偶婚轉變期間形成的習俗,周作人認為“即初夜權之一變相”,同族青年失去群婚制時代親昵新娘權利,而通過“戲婦”游戲化得以補償。越是接近本能的行為,越可以追溯到久遠。
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規矩越來越多,因之,這一先民遺俗遭到愈來愈多的批評。《漢書·地理志》講:戰國晚期的燕國“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后稍頗止,然終未改”;晉《抱樸子》“疾謬篇”講:“俗有戲新婦之法,于稠眾之中,親屬之前,問以丑言,責以謾對。甚為鄙黷,不可忍論”;清康熙年間,福建巡撫張伯行頒《禁鬧婚示》講:“合婚之夕,親戚朋友,伙飲徹宵。擁眾入房,披帷帳、搜枕衾,名曰鬧房,褻狎瀆亂,傷風敗俗,此其甚也”;稍后的龔煒《巢林筆談續編》“嫁娶惡習”講:“今江浙間有嬲親之俗,亦何以異此。又聞山左州郡有所謂討喜者,穢褻益復不堪。士大夫生圣人之世,處禮義之鄉,有此惡習而不知革,亦可怪矣”。
說來也不奇怪,古代鄉村生活環境封閉,流動性極差,鄉民終日為衣食奔波勞碌,社交休閑聚會始終是奢侈之事,沒有多余資金與空閑用于這方面消遣。一般來說,鄉民經常性交際距離難以超過五公里,社交多局限在本鄉本村,最鋪張熱鬧的聚會莫過于婚喪嫁娶。這是辛苦勞作間隙中難得的消遣放縱機會。
傳統社會歷來同姓聚居,婚姻半徑很小,嫁娶區域相對固定,故而鄉村宗族譜系清晰。同村之人,大都沾親帶故,一家辦喜事,能做到傾村參與。
所謂“無大小”存在約定俗成的前提條件。首先,參與者基本上是同族近親的未婚青年;其次,大小絕非年齡大小,在宗族人群中,娃娃爺爺與胡子侄孫現象屢見不鮮,參與鬧婚之人盡管是長輩,卻可以暫時放下規矩盡情調笑新娘。無論糾纏拉扯新娘,還是聽房的青年都清楚日后自己也將受此待遇。在這一意義上,乃是預習與鍛煉承受應付能力的機會。
鬧洞房習俗是歷史的,同時又是散見的,并非禮制婚禮文化大傳統,更非都會與社會中上層的婚禮現象。儒學尊卑長幼、男女內外觀念與“三日無大小”格格不入。傳統婚禮拜堂一般在晚七時以后舉行,并非今日影視劇演繹的當眾大堂三拜。花轎進門直入私秘的新房成禮,公婆并不出現,更無一對新人攜手向來賓敬酒、致謝的程序。來賓也不一定要等新婦進門,隨時可以告辭。畢竟婚禮主辦人是新郎之父,發出邀請與接受祝賀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兒子。
“三日無大小”的社會記憶深刻久遠,但不代表其依托的文化背景都為人了解,隨著社會開放,人群流動,泛化亂用日漸增多。其實,鬧洞房無大小具有鮮明的血親界限,只局限在同族至親之內,即使在舊日封閉靜態社會中,異姓外人也難混于其中。因之,一旦走出熟人宗族社會,再執此觀念施及他人必飽受譴責。社會生活順勢為之,真的到了徹底告別這一舊俗的時候了。
(摘自《環球》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