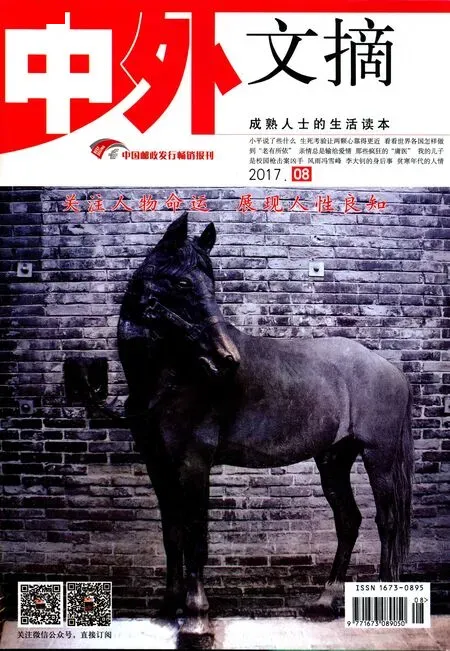李大釗的身后事
□ 劉曉艷
李大釗的身后事
□ 劉曉艷

1920年,李大釗與胡適、蔡元培、蔣夢麟在一起(從右至左)
暫厝妙光閣街浙寺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遺體被警方裝殮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門外北頭路西土地廟下斜街長椿寺內,派警察看守。當晚,其也遭囚禁的夫人趙紉蘭和女兒李星華、李炎華獲釋,回到灰廠豁子內朝陽里四號家中。
第二天早晨看到報紙時,她們才知道自己的親人已被施了絞刑。這惡耗猶如晴天霹靂,使李大釗夫人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大釗犧牲后,家中生活慘狀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晨報》《京報》《東方時報》等紛紛報道,就連日本人主辦的充斥著侵略色彩的《順天時報》都撰文說,“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李宅室中“空無家俱,即有亦甚破爛”。
對于手無縛雞之力的孤兒寡母,反動當局并沒有善罷甘休,仍繼續派人進行監視。李大釗妻小因經常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擾,只好闔家遷移到李青峰的宅中居住。
當此之時,社會各界同仁紛紛捐款,李大釗同鄉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也分別到李大釗家中看望趙紉蘭并到長椿寺準備領出李大釗棺木。大家在征求了趙紉蘭的意見后,決定為李大釗換棺,并募捐辦理后事。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壽山,講明要購買棺材重新裝殮李大釗遺體。伊壽山推薦了一口標價260塊大洋的柏木棺材,因為價格太高,李凌斗說明情況,請求伊壽山降價。伊壽山“生平不識李先生,并絕對反對共產主義,因連日看報,對于其個人人格確有相當欽佩,只索銀一百四十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舉動也”(《順天時報》1927年5月2日)。李凌斗走后,伊壽山又請師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十幾斤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給棺木上了五道漆。正是因為經過這樣精心的打造,1983年黨中央將李大釗的棺柩移至李大釗烈士陵園時,棺木出土完好,李大釗的遺骸得到較好的保護。
5月1日上午,伊壽山帶領16名工人扛著棺材到達宣武門外長椿寺,重新裝殮李大釗遺體。在場諸人,無不含淚悲憤,李星華、李炎華更是大聲哭喊著爸爸,扶父親入新棺,再三祭拜。11時左右,又由24人抬著李大釗的新棺到妙光閣街浙寺,暫厝浙寺南院,安放祭拜。寺主人因李大釗為政府絞刑不愿收留,經多方疏通,才允許暫時停放。由于政府迫害,加上時局變幻,這一放就是六年。就連幫忙入殮的伊壽山也被警察逮捕,后經保釋才得出獄。
周作人、沈尹默暗助子女求學
當年5月20日,在李采言的護送之下,趙紉蘭帶著幼小的孩子回到了大黑坨李大釗老家。不久后,趙紉蘭便請弟弟趙曉峰代筆修書一封給周作人,再次懇請周作人幫忙籌劃,解決李星華、李炎華等姐弟的讀書問題,以求完成學業,不負先烈。周作人接信后,即和北大同仁商議,可惜在反動政府的恐怖統治之下,各教授雖多次討論商議,終無能為力,直到1931年夏,才通過多方安排,接李星華和李炎華姐妹倆回北京復學,分別入孔德學校初中部和小學部讀書。李星華入孔德學校后半工半讀,周作人給她安排了為學校刻法文講義的工作來補貼生活。
而李大釗長子李葆華則是另一種情況。1927年4月6日清明節,也是當時的植樹節,李葆華隨同周作人等一起出城植樹,并于當晚住在城外沈士遠教授家里。4月7日,李大釗被捕的消息傳來以后,沈尹默立即打電話給大哥沈士遠請他保護好李葆華。但因為海淀偵緝隊就在沈家附近,不便久留,于是又請周作人借去燕京大學上課的機會,將李葆華帶回城里。4月28日,即在李大釗遇害當天,周作人將李葆華接到八道灣家中,隱藏在后宅小屋內,直至7月,在沈尹默等人的聯系之下李葆華赴日本留學。當時,李葆華還不滿18歲,但是他的沉穩與鎮靜卻如一位久經沙場的老兵,周作人等人深為折服。
是年,沈尹默為李葆華辦理了孔德學校的畢業文憑,離開北京到天津,從天津乘船到日本,進入位于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日文。翌年1月,李葆華考取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理化系。在日本的一切花銷全部是自費,臨行前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支援的生活費已全部用完,李葆華的生活處于極度的困窘之中。8月初,李葆華回國,暫住周作人家中,又于月底回日本。1929年,沈尹默擔任河北省教育廳廳長,費盡周折,把李葆華由自費改為公費,才使得他的生活和學業都得到了保障。1931年,李葆華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任中共東京特別支部書記。“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十七省留日學生代表集會,決議全體回國參加抗日斗爭。1931年11月,李葆華由日本長崎登輪回國。從此繼承父業,開始了革命生涯。

萬安公墓一度拒絕入葬
1933年初,李大釗的家鄉樂亭被日偽占據。3月,李星華回家鄉接病重的母親來京避難。而這時,李大釗的靈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為了讓逝者入土為安,趙紉蘭帶李星華姐妹又一次找到了周作人、沈尹默、蔣夢麟、胡適等北大同仁,懇求幫助,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4月10日,由北大校長蔣夢麟領銜,北大同仁王烈、何基鴻、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適、馬裕藻、馬衡、傅斯年、樊際昌、劉復、錢玄同13人聯合發起,共擔公葬重任,向社會廣泛地發起了捐款活動。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章廷謙到萬安公墓購置墓地時,公墓經營者、曾任過北洋政府交通部司長的浙江人蔣彬侯,因為害怕受連累,一度拒絕接納李大釗入葬。4月13日,蔣夢麟親自出面方才勉強辦妥。蔣彬侯非常小心謹慎,所以在說明一欄里,特別注明由蔣夢麟代辦。
為李大釗立碑,是13位發起人的心愿,大家推請語言學家劉半農撰寫碑文。可惜,因為反動當局的破壞,這塊飽含著北大同仁深情的墓碑并沒有能立在李大釗墓前。
1933年4月22日,在妙光閣浙寺內舉行了對李大釗的公祭。4月23日上午8時,蔣夢麟、馬裕藻等北大同仁及教育界人士,各大中學青年學生,工人及軍人700多人,陸續趕到李大釗靈前致祭,參加出殯儀式。
送葬隊伍由浙寺出發,一路之上,人們高喊著口號,散發著傳單,不斷地有人加入,送葬的隊伍越來越大,聲勢也越來越高,最終發展成為一場示威游行。這引起了軍警的禁止和破壞,將到西四牌樓時,國民黨憲兵出動,堵住路口,不許就地舉行公祭。送殯群眾提出抗議,引起激烈沖突,憲兵開槍抓捕,青年受傷,送葬隊伍被沖散。后經一番努力,直到黃昏時分才到達墓地,由北大同仁扶靈下葬。
中共北方黨組織碑文半世紀后始見天日
因為當時白色恐怖的殘酷環境,中共北方黨組織沒有公開出面組織這場活動,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濟會(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的公開群眾團體,專做援助被捕同志和撫恤烈士家屬的工作)的名義全程參與,在公祭之時贈送了花圈、挽聯,派人秘密保護靈堂,組織工人、群眾及軍人參加公葬,印刷并散發了《河北革命互濟會為公葬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李大釗同志宣言》等傳單,組織路祭、演講活動等,以宣傳李大釗先烈的英勇革命精神來激發群眾的斗志,點燃革命的熱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當局的黑暗統治。中共北方黨組織還以北平互濟會的名義為李大釗書寫了“革命導師李大釗之墓”的墓碑,由一輛騾車送達萬安公墓。但迫于當時緊張的政治環境,墓碑沒有立在李大釗墓前,而是因循六朝墓志的方法將之同棺槨一起埋入地下,直到1983年為李大釗修建烈士陵園移靈時才出土,得見天日。碑文如下:
李大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忠實最堅決的信徒,曾于1921年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運動,并且實際領導北方工農勞苦群眾,為他們本身利益和整個階級利益而斗爭。
1925-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爆發了,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竟無恥的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并且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之下,于4月6日大舉反共運動,勾結張作霖搜查蘇聯使館,拘捕了李大釗同志等八十余人,在4月28日被絞死于京師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難者八十余人。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國反帝與土地革命勝利的基礎,給無產階級的戰士一個最有力最好的榜樣。現在中華蘇維埃和紅軍的鞏固與擴大,也正是死難同志們的偉大犧牲的結果。
妻子隨他而去
因為連日的勞累和出殯時的驚嚇,趙紉蘭病倒在床,在公葬完李大釗一個月之后的5月27日,在協和醫院去世。北大同仁再一次出面,于5月28日將趙紉蘭安葬于萬安公墓李大釗的墓側。翌年6月6日,北大再一次請劉半農書寫碑文,為李大釗和夫人立碑。限于當時的環境,碑文十分簡略,僅說明了李大釗及夫人的諱字、籍貫、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
趙紉蘭生前最關心的李大釗文集,也交由周作人負責,先后聯系了上海群眾圖書公司的曹聚仁和北新書局的李曉峰,后由北新書局出版。魯迅為其撰寫了《題記》。不幸的是,1933年文稿送審時被扣,直到1939年《守常全集》才得以出版。也因為當局限制,出版后只當事人留有幾本,即全部被收回。1949年7月,上海解放以后,仍以原版改名為《守常文集》出版發行,并于1950年再版。
1982年,中共中央決定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翌年10月29日,在李大釗誕辰94周年之際,隆重舉行李大釗烈士陵園落成典禮。
(摘自《各界》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