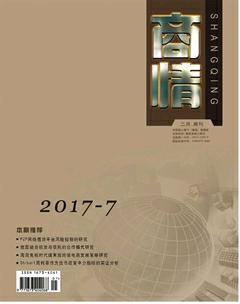淺議語言與思維的關系
楊艷玲
語言與思維緊密相連,兩者相互依存。對于語言與思維的認識,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是非常重要同時富有爭議的一個理論,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本文圍繞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進一步探討了語言與思維的關系。
語言思維薩丕爾-沃爾夫假說
一、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簡介
薩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是Edward Sapir和BenjaminLee Whorf對于語言文化與思維關系的認識。假說并不是由薩丕爾和沃爾夫所創立,而是后人對兩位偉大的語言學家的思想觀點的總結。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認為人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是通過語言實現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結構決定了人們的思考與行為方式,不同的語言提供給人們不同的表達世界的方法。同樣的物質證據,并不能使語言背景不同的觀察者得到相同的宇宙圖像。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有兩種版本—即“語言決定論”和“語言相對論”;語言決定論認為語言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而語言相對論則認為語言影響了思維而不能決定思維。
20世紀20年代早期,沃爾夫是美國一家火險公司的員工,通過分析火災原因報告,他發現人們頭腦中的語言概念是造成火災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人們會由于“空”字的概念而忽視了加油站旁空氣油桶的可燃性,由于“石”字的概念而忽視了石灰石的易燃性;甚至會認為吹風機是用來吹干濕的東西而忽視了它也能夠把火星吹出火災。這些案例研究發現使他對語言研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后來他遇到了他的老師—薩丕爾,薩丕爾當時已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沃爾夫在耶魯大學認真聆聽了薩丕爾的講座與他產生了極大的思想共鳴,隨后他們對霍皮語--一種亞利桑那州東北部印第安人的語言進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并與英語等歐洲語言進行對比。他們的研究中發現在霍皮語中時間是一種不可被分割的概念,不是線性的,是不可計量的,沒有速度,快慢這類表達,他們用類似于“He very run”來代替“He runs fast”,在霍皮語中也沒有像歐洲語言一樣表達時態的概念,歐洲語言是客觀的流動的,但是霍皮語卻是心理的,形而上的。由此我們知道霍皮語是非常簡單的語言,但是沃爾夫則認為語言結構越是簡化,其語言就包含越多的隱藏意義,就像兩個非常熟悉的人能用簡潔的語言清楚地交流一件事情,因為他們有很多共知信息。因此沃爾夫認為語言結構越是簡化的人,其思維可能在更高更復雜的層次。 (Whorf, 2012 )
二、語言與思維關系的其他視角
étienne Bonnot deCondillac(1975)是法國的知識學家,他認為語言是人類的感覺和知覺轉化為行動與精神狀態的工具,語言的結構是思維的結構,沒有語言,人將不能回憶起過去的事情,是語言使人類將自己的思維能力得以使用起來,他認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無法擁有回憶,他們所擁有的只是想象。這種觀點先于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出現,對當時的語言學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CarrollandCasagrande(1958)有一組實驗則有力地支持了薩丕爾-沃爾夫假說,他們選擇了其他條件一致的相同數量的納瓦霍語兒童和英語兒童,在他們每個人面前放置了藍色的繩子,藍色的棍子和黃色的繩子三樣物品,然后用他們的本族語言告訴他們選擇出與藍色繩子最相似的物品,絕大多數的納瓦霍語兒童選擇了黃色的繩子,而絕大多數的英語兒童選擇了藍色的棍子,.這兩組孩子都有辨別物體顏色和形態的能力,但是他們的選擇卻出現了兩級化,這個實驗表明孩子們會基于他們各自的語言編碼來認識事物和周圍的世界。
維果茨基(2010)是俄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主要研究兒童發展與教育心理,他在他的著作《思維與語言》一書中提到,語言與思維并不同源,他們是兩條不同的增長曲線,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相互交錯,最終可能會走向統一。他認為兒童的思維發展是由思維的語言工具和他的社會文化經歷所決定的,兒童的智力增長取決于語言。維果茨基接受了苛勒的類人猿實驗并發展了它,類人猿能夠使用工具,甚至創造工具來解決問題,因此我們說類人猿具有初級的思維,但是類人猿沒有言語,缺乏想象,這是其與人類顯著的不同,苛勒認為類人猿以及其他動物發出的聲音只是一種情緒的反映,不能像人類的語言一樣反映客觀現實。維果茨基認同這個觀點,并且在研究中發現在兒童的語言發展中存在一個前智力期,如同類人猿創造工具的時期,同樣的在兒童的智力發展過程中也存在前語言期。當語言的生長曲線與思維的生長曲線相交時,語言會變成理性的語言,思維則變成了言語的思維,孩子7歲以后開始從自我中心語言向內部語言(一種無聲的思維)過渡,正是這時語言與思想曲線開始走向統一,而這種統一的很重要的連接體是詞語的使用。一個詞的意義實際上是思維與語言的混合體,沒有意義的詞是一種空洞的聲音,從心理學上,每個詞的意義都是一種類化或一種概念,而類化和概念正是思維現象。維果茨基的這個觀點與沃爾夫的“意義不產生于詞或詞素,而是產生于詞或詞素之間模式化了的關系,而思維的本質就是這種關系”表述十分接近,只是他們的視角恰恰是互補的,維果茨基是一個縱向的歷時的視角,而沃爾夫則是一種共時的跨文化的視角。
福科(2009)是一位后現代主義哲學家,他認為語言總是動態的,意有所圖的;語言不能不加扭曲地反映事物的本質,福科式話語分析認為語言反映社會權力關系,社會被語言塑造。這種后現代主義的觀點值得我們深思。其實,從古到今,人類對思維和語言的思考從未停止。
三、思維與語言關系的再思考
偉大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If something doesn't exsit , there is no word for it. And if there no wordfor something that something doesn't exist.”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一直被討論卻也沒有一個固定的結論。在中國文化中,思維被分為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形象思維是一種直觀的思考方式,基于我們對這個世界直接的感覺和知覺。它涉外形,氣味,聲音等等在我們大腦中形成的圖像。而抽象的思維則是一種更高層次,更復雜的認知概念,以抽象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意味著人們能從表象中歸納總結出抽象的理論,抽象思維來源于形象思維,但抽象思維是我們解決生活社會中問題的更為重要的思維方式。(范曉,2003)形象思維類似維果茨基所提及的初級思維,它是可以脫離語言而存在的,比如孩子在不會說話之前通過肢體語言和哭聲來表達自己的需求。但是抽象思維卻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因為我們通過詞義形成概念,然后通過概念結合邏輯分析推論來形成抽象思維,比如如果我們想要比較兩種花的不同之處,那么我們首先要有“花”這個詞的存在。這與維果茨基和薩丕爾沃爾夫的觀點也是不謀而合的。
因此,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對生活的認識以及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認識,我們的思考方式隨著我們的語言結構一代代地傳遞下去,并融進我們周圍的文化。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思維和語言無異于給人類插上了振翅高飛的翅膀,讓人類在蕓蕓眾生中能夠脫穎而出,生生不息地發展下去。
參考文獻:
[1]Aarsleff,Hans.(1975)“Condillac's Speechless Statue,”Akten des II. International Leibniz-Kongresses (Volume 4), Wiesbaden: 287–302.
[2]Arribas-Ayllon, Michael; Walkerdine, Valerie (2008). 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3]Carroll, J B, & Casagrande, J B. (1958).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in behavior.
[4]范曉.關于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及其相關問題.語言科學,2003,2(6):73-85.
[5].劉永謀.福柯的主體解構之旅:從知識考古學到“人之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6].維果茨基.思維與語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7]Whorf,B.L.,Carroll,J.B.,Levinson,S.C.,&Lee,P.(1956).Language,thought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Vol.21, pp.44-45).
[8]沃爾夫.論語言、思維和現實:沃爾夫文集.商務印書館,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