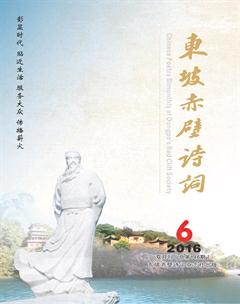檻外談詩(一)
夏元明
1.鐘嶸《詩品》云:“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也。”
賦、比、興之說,古已有之。鐘嶸此論,最給人啟發者,在于他對比興和賦在運用上的區別,不獨舊詩如此,新詩亦然。寫詩而專用比興,其意往往隱藏較深。隱藏的好處在于含蓄,在于余韻悠長。但如果處理不好,則容易導致過于隱晦,甚而至于晦澀。比如李商隱,喜歡他的人在于他的曲折含蓄,有不盡之意,富多樣解釋。而不喜歡他的人,也在于他的不易求解。林黛玉不喜歡李商隱,只稱道他的一句詩:“留得枯荷聽雨聲。”然“留得”一句,恰恰在于它的淺白易懂。比較而言,賦體則相對質直,但運用不好,又易流于浮淺,文字也易于散漫,仿佛飄蕩之舟,無所依傍。這也是初學者易犯的毛病。賦、比、興三種手法必須有所調和,要之在于“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既不能忽略風骨,也不能失之于文采,各種元素須得和諧。當今寫新詩者,所謂“先鋒派”則多用比興,病在晦澀;而“口語體”隨意舉事,病在淺俗。故新詩能動人的優秀作品極少。寫舊詩者往往自認為風雅,多瞧不起玩新詩的,殊不知兩者往往犯同一錯誤。詩非易事,新舊都當慎之。
2.鐘嶸評李陵:“其源出于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詩最忌諱的是無病呻吟。但古往今來,無病呻吟者多矣。詩應當是情動于中,而言行于外。所以非常佩服一些為詩者,遇事都可以來一首。其實,這大多不是詩,文字游戲爾。但文字而能成為游戲,從文字的把玩中獲得一種快樂,也是為之聊勝于無之事。所以,我們對某些只會排列平仄的人,也不能責之過苛。如果不是真的無聊和肉麻,玩一下平仄也無不可。但說到真正的詩,還是要有真正的生命。就如鐘嶸所說的,“生命不諧,聲頹身喪”,方能寫出真詩,真正打動人。當然,我們也不能都像李陵,有那種非同尋常的經歷,也不必非得“聲頹身喪”而后為詩。這只是一種特例,要義在于必須有真正的生命體驗和生活感受。這是真正詩歌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還有藝術修養和鍛煉。其實,藝術修養也有天才的成分,不是宵衣旰食就能解決問題的。這是另一話題,姑且放下。
還是說詩的內容。我們讀屈原,愛杜甫,除了他們的詩才,更重要的就是他們的精神情感,他們獨特的人生經歷,他們對生活和生命,對時代和人民的特殊感情。在當今的新詩人中,我們也特別推崇昌耀。讀昌耀的詩,我們不能不為之感動,也與昌耀苦難的人生密不可分。昌耀的成功,既有他的苦難,也有他的境界,也有他敏感的詩才。只有這樣的詩人能傳之久遠,能夠成為一個時代的典型。
3.杜甫《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杜甫到底是大師。杜甫的詩有些寫得非常細致,比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觀察非常之精細。但我更佩服杜甫的大氣。杜甫的詩,哪怕是寫眼前的景,境界也非常闊大,而且不是硬吼出來的。有些人寫詩,喜歡用大詞,裝腔作勢,“瘦豬婆屙硬屎”,這不是真正的大,是李鬼而不是李逵。就以這首小小的絕句而言,“黃鸝”“翠柳”“白鷺”“青天”“雪”“船”,都是眼前景,不會寫的人,頂多也只是一幅小畫面,清新雅麗而已。但杜甫卻寫得很有氣勢。這個氣勢有動態的,四個關鍵動詞“鳴”“上”“含”“泊”,不僅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事物的特征,更營造了一種氣氛。特別是“上”字,將白鷺和青天的關系表現得十分開闊,有游目騁懷之感。再就是靜態的,更是杜甫的拿手好戲。雪不是普通的雪,是“千秋雪”,是經年不化的積雪,給人一種時間上的久遠感。所謂“秦時明月漢時關”,自有一段思古之幽情。船也不是普通的船,是東吳的“萬里船”,又給人一種空間上的遼闊之感。眼前小景,輕松道來,卻是浩然曠渺,歷史時空。這是真正的大手筆。以小見大,《絕句》是很好的典范。
4.王安石《梅花》:“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香菱學詩,說有些詩句看起來沒有道理,比如“大漠孤煙直”,煙怎么會是直的?而有些卻又似乎完全不必說,如“長河落日圓”,有什么必要寫?但就是這沒有道理或不必說之中,讓人感覺到真切的畫面。香菱所言極是。不獨于此,舊詩中有些感觸簡直是虛構的,并不是真實的心理。比如王安石的這首《梅花》。王安石是不是被白梅所欺騙,將其誤認作了雪?但詩人又說得清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因為有暗香,大老遠就知道那不是雪。可這說了豈不等于沒說?說了有什么意思?加上前面兩句鋪墊,分明交待是梅花在那里凌寒自開,更不可能產生錯覺。所以,這首詩給人的感覺完全是“做作”的,并無詩意。拿來和李白的《靜夜思》比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種錯覺是切切實實存在的。而且后面的感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湊合。這樣的詩才有詩味,是好詩。可是王安石的這首詩歷來為人們所喜愛,看來讀者已經認可,詩的邏輯與日常邏輯是有區別的,不能拿生活邏輯要求詩的邏輯,否則詩沒法寫。常聽到一種說法:“這是寫詩!”如果批評《梅花》不是詩,人家就要說你是鉆牛角尖了。
5.袁枚《隨園詩話》:“少陵云:‘多師是我師。非止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隨園擔糞者,十月中,在梅樹下喜報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門,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園中梅花盛開,公帶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憐香雪梅千樹,不得隨身帶上船。”
很多作家談創作體會,都講向群眾學習語言,袁枚也懂這個道理。不僅向高于自己的人學習,更向普通老百姓學習,所謂“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但袁枚的境界終嫌狹小,“霜高梅孕一身花”尚可,“月映竹成千個字”就沒多大意思。這里似乎也觀察得細,但細得略近無聊。遠不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之類的句子來得有情趣。看來學習語言不錯,但如何學,學什么,還是取決于學習者的心胸和才情。尖細狹小之人,只看到了語言本身的一點趣味,而沒法形成生命和藝術的大境界。
(作者系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湖北作家協會會員、黃岡市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