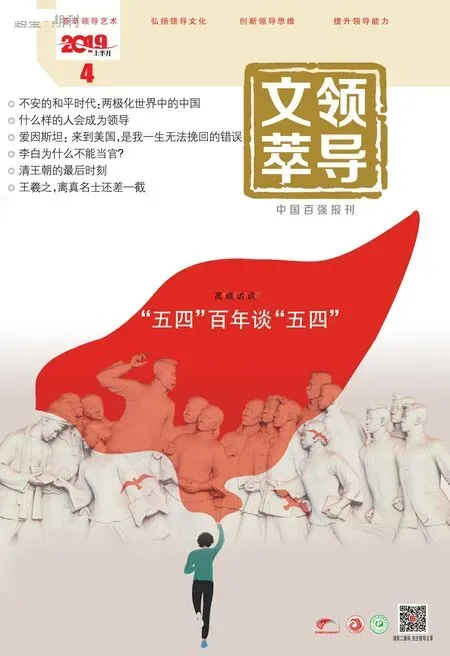歐洲三大頑癥待解
周弘
源自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危機,波及歐洲已8年有余。在多管齊下的猛藥過后,歐洲經(jīng)濟終于止住下滑,但難以擺脫增長緩慢、復(fù)蘇乏力的困境。難民危機又使歐洲社會面臨考驗。此外,英國脫歐給歐盟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劇了整個世界的疑歐情緒,來自各方面關(guān)于歐盟和歐元區(qū)將要壽終正寢的議論不絕于耳。歐洲和歐洲經(jīng)濟面臨的問題從根本上看均是其三大頑癥在不同層面的反映。
面對日益加重的市場失靈束手無策
市場失靈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制度與生俱來的頑疾。逐利的全球資本使各種規(guī)范市場的政治力量黯然失色。近幾年,歐盟在公開文件中多次提及市場失靈問題,它在與美國的“跨大西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談判中堅持市場規(guī)范的高要價。2014年,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歐盟委員會工作計劃的“十點優(yōu)先”工作目標(biāo)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歐盟的就業(yè)、增長和投資等領(lǐng)域出現(xiàn)的問題就是源于市場失靈。他提出,要投資于內(nèi)部市場建設(shè)、投資于市場缺口、投資于市場缺失的領(lǐng)域,通過投資引導(dǎo)、聚集更多的政府和資本力量共同彌補市場失靈造成的投資鴻溝。但問題在于,在不對資本主義經(jīng)濟制度進(jìn)行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建設(shè)歐洲共同市場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歐盟既缺乏針對市場失靈進(jìn)行投資和分配的權(quán)力,也缺少能平衡競爭性勞工市場和民主制度并且能夠同時維護(hù)資本利潤、經(jīng)濟發(fā)展?jié)摿蛣趧诱咦饑?yán)的有效治理體制,英國脫歐更是使本已進(jìn)展緩慢的歐洲共同市場建設(shè)瀕臨困境。在日益加重的市場失靈面前,歐盟治理捉襟見肘。
決策過程緩慢,治理效率低下
歐盟是民族國家自愿轉(zhuǎn)移主權(quán)、通過國際條約實現(xiàn)聯(lián)合的產(chǎn)物。歐盟成員國在轉(zhuǎn)移一部分權(quán)力給歐盟的同時,繼續(xù)保有一部分權(quán)力。國家治理權(quán)力的分割、民主授權(quán)的不足(或稱為“民主赤字”)是一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勢必造成歐盟的決策過程緩慢、治理效率低下、治理功能缺失。例如,歐盟的“決策不透明”和“行政官僚化”飽受詬病;同時,由于歐盟各成員國差異巨大、決策程序復(fù)雜、信息不對稱,民主流于程序化、符號化、簡單化、絕對化。在信息不對稱、責(zé)權(quán)利不匹配的條件下,所謂的“民主投票”成了政客免責(zé)的工具。
英國脫歐公投的結(jié)果引起歐洲知識階層反思,但歐洲對于民主的理論思考和實踐經(jīng)驗都不足以應(yīng)對其民主制度受到的巨大挑戰(zhàn)。因此,每當(dāng)歐洲出現(xiàn)危機,極端民族主義就會抬頭。
同時,目前的歐洲社會非常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方面,歐盟力促機構(gòu)改革和去官僚化;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的聽眾越來越多。歐盟經(jīng)濟越是不景氣,歐盟政治就越是沒有向心力;歐洲政治決策越是繁雜低效,歐洲經(jīng)濟就越是難以恢復(fù)發(fā)展。政治和經(jīng)濟的制度性錯位致使歐盟前行的道路十分坎坷。雖然所有的理性思維都指向歐洲一體化發(fā)展不可逆轉(zhuǎn),但如果歐盟不能有效地補足民主參與和有效治理的制度短板,那么,不斷重復(fù)的全民公投方式將會繼續(xù)給歐盟體制帶來致命打擊,促使歐洲滑向衰落。
民眾對社會政策缺乏認(rèn)同
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的深入發(fā)展和歐洲競爭力的持續(xù)下滑,歐洲的社會和諧機制受到嚴(yán)峻考驗。歐洲共同體建立以后,一邊快速擴大內(nèi)部市場,一邊延續(xù)歐盟一些發(fā)達(dá)成員國的“社會伙伴關(guān)系”,在歐盟范圍內(nèi)鼓勵“最佳社會實踐”,帶動了南歐成員國社會福利水平的向上趨同,這成為其勞動生產(chǎn)率和競爭力降低的重要原因。龐大的福利開支也是債務(wù)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希臘債務(wù)危機爆發(fā)以后,西部歐盟國家主動地、南部歐盟國家被動地削減社會福利、緊縮公共財政,試圖提高市場競爭力。然而,這種緊縮在歐盟內(nèi)部并沒有達(dá)成社會共識,在發(fā)展并不均衡的歐盟國家之間出現(xiàn)了諸多矛盾。
在越來越大的社會鴻溝面前,歐盟各成員國政府用于干預(yù)社會的能力和權(quán)力卻越來越小。而逐漸獲得了更多權(quán)力的歐盟由于沒有統(tǒng)一征稅的授權(quán),無法在歐盟全境有效地干預(yù)市場和社會,無法提供與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yīng)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在歐盟內(nèi)部,資本和社會之間固有的利益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繼續(xù)擴大。資本的趨利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結(jié)構(gòu)性變化,而富人逃稅則大大削減了成員國社會再分配的財力。歐洲民眾不斷采用各種方式抗拒社會福利水平的降低,使歐洲社會體制處于臨淵涉險的境地。因而,只能同時采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措施,既要鼓勵企業(yè)參與全球競爭,又要保護(hù)歐盟內(nèi)部市場;既要加大人力資源領(lǐng)域的社會投資,又要努力削減社會福利投入。
目前,歐洲民眾的不滿情緒不僅表現(xiàn)為反分配不公和反財富鴻溝,而且表現(xiàn)為反經(jīng)濟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甚至反對歐洲聯(lián)合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原則,特別是反對貨物、人員、服務(wù)、資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員自由流動。歐盟決策者明白,沒有社會的支持,歐盟將沒有前途,歐洲經(jīng)濟難以真正復(fù)蘇。但建設(shè)“社會支柱”不僅需要正確的政策,更需要合法的體制、可靠的財源以及民眾對社會政策的認(rèn)同,而這一切都需要歐洲進(jìn)行深入的制度性改革。
(摘自新華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