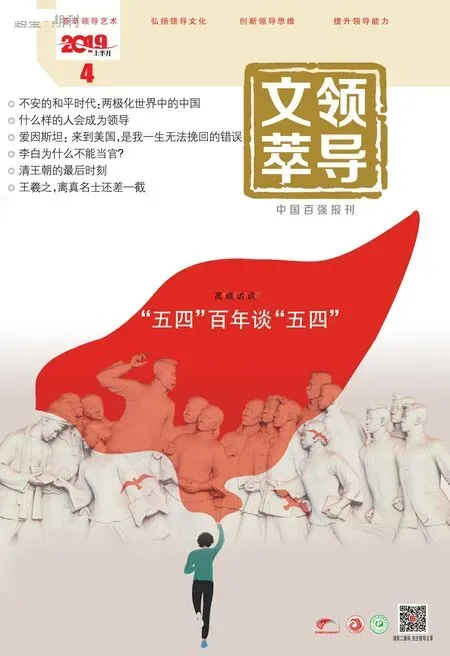懂得“不做”,是一種智慧
吳軍
前段時(shí)間著名作家王蒙到美國(guó)進(jìn)行文化交流,在洛杉磯和圣弗朗西斯科各做了一次報(bào)告。他講的內(nèi)容很多,我對(duì)他的一句話印象特別深。
講到中美文化的比較,王蒙講:“美國(guó)很了不起,但并非做的都是對(duì)的。美國(guó)人總是在想,I do it,I try it。這有進(jìn)取的一面,但有時(shí)候就不計(jì)后果了。中國(guó)過去的文化是,大家都在想I can,t do it,這有消極的一面,但也有智慧的一面。美國(guó)人是否應(yīng)該想想,做事情的時(shí)候要了解自己什么不能做、做不到。”
王蒙的這段話確實(shí)反映出兩種文化在思維上的差別。
我們過去總是說,中國(guó)人缺乏進(jìn)取心,但事實(shí)上,中國(guó)在過去的40年里發(fā)展得不錯(cuò)。現(xiàn)在,中國(guó)并不缺乏進(jìn)取心,變得什么都想做了。
美國(guó)則相反,在冷戰(zhàn)結(jié)束后的這四分之一世紀(jì)里,什么事情都在做,但正如王蒙所總結(jié)的,出現(xiàn)的問題很多。美國(guó)現(xiàn)在倒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可以不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特朗普,他在反思美國(guó)是否做了很多不必要做的事情。
懂得“不做”,是一種智慧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比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有時(shí)顯得更難。
之前和段永平等人聊過,巴菲特從來不告訴他們?cè)撟鍪裁矗偃谒麄冞@輩子不要做什么。我雖然沒有像他們那樣去和巴菲特吃飯,但對(duì)此深有同感。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xué)讀博士時(shí),我的老師,語音識(shí)別的泰斗賈里尼克給我的指導(dǎo),總的來講就是告訴我什么做法不管用,這來自于他幾十年的經(jīng)驗(yàn)。至于什么方法管用,他說他不知道,讓我們年輕人自己去找。
當(dāng)然,他會(huì)給我們創(chuàng)造條件,每星期請(qǐng)一位世界一流學(xué)者來做報(bào)告,暑假還要把世界上最好的科學(xué)家請(qǐng)來工作8周,讓我們有可能找到該怎么做的方法。
很多時(shí)候,我們自以為找到了一些好的做法,但賈里尼克會(huì)說:“哦,這個(gè)不用浪費(fèi)時(shí)間了,我們?cè)贗BM已經(jīng)證明它不管用。”這樣就給我們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試錯(cuò)時(shí)間,也避免了經(jīng)歷不必要的失敗。
你的失敗少,時(shí)間長(zhǎng)了,成功的可能性就大。相反,如果一個(gè)人總是失敗,總是講失敗是成功之母,那他有可能永遠(yuǎn)都走不出失敗的怪圈。
遠(yuǎn)的不說,就說美國(guó)總統(tǒng)奧巴馬。他競(jìng)選時(shí)的口號(hào)是“Yes,We Can”,意思是我們什么都行。這個(gè)態(tài)度倒是很積極,但這位40多歲的年輕人之前只有兩年從政經(jīng)驗(yàn),只知道加速,不懂得剎車的道理。
本來美國(guó)已經(jīng)病得不輕,該好好調(diào)理才是,但他偏偏要給它打雞血,結(jié)果從全民健保開始,做一件事失敗一次,永遠(yuǎn)走不出失敗的怪圈。8年下來,不僅讓美國(guó)喪失了全球超級(jí)大國(guó)的地位,而且把世界局勢(shì)搞得很緊張。
如今,特朗普當(dāng)選總統(tǒng),表示要修正奧巴馬激進(jìn)的政策,包括全民健保、TPP(跨太平洋伙伴關(guān)系協(xié)定)和對(duì)非法移民的政策等,也就是說要?jiǎng)x車了。
另外再補(bǔ)充一句,即便是希拉里當(dāng)選總統(tǒng),她也要修改全民健保法案,廢除TPP,也會(huì)做相應(yīng)的剎車。
剎車和引擎,一個(gè)也不能少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事情能做;知道了什么方法不管用,也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方法管用。因?yàn)樗鼈儾⒎菍?duì)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
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怎么做,是需要年輕人自己動(dòng)腦子的。一個(gè)好的導(dǎo)師知道不能約束學(xué)生的想法,因?yàn)檫@樣學(xué)生才能進(jìn)步。
卡內(nèi)基·梅隆大學(xué)的一個(gè)畢業(yè)生在畢業(yè)典禮上問主講嘉賓比爾·蓋茨,下一個(gè)像微軟這樣的機(jī)會(huì)在哪里。蓋茨說,這是我該問你的問題。像蓋茨這樣的智者,很清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他希望年輕人提出什么事情能做,這樣才能突破老一代的思維局限性。
一輛汽車也好,一輛火車也好,既要有引擎,也要有剎車。引擎的作用很好理解,剎車的作用常常被忽略。沒有剎車,不僅會(huì)出事,而且無法轉(zhuǎn)彎。
小到個(gè)體,大到組織,不可能永遠(yuǎn)沿著一個(gè)方向走,經(jīng)常要不斷地轉(zhuǎn)彎,改變方向,開過車的人都知道剎車在轉(zhuǎn)向時(shí)的作用。懂得不能做什么,會(huì)使得我們轉(zhuǎn)彎非常順當(dāng);否則,開車橫沖直撞,很難開到目的地。
讓年輕人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己找出該怎么做的方法,就好比機(jī)動(dòng)車的動(dòng)力;有經(jīng)驗(yàn)的人告訴他們不該犯的錯(cuò)誤,這樣機(jī)動(dòng)車就有了方向。有了這樣的配合,會(huì)事半功倍;反之,則會(huì)陷入泥潭。
拋開誤區(qū),才能做到駕車自如
在對(duì)引擎和剎車作用的理解上,人們常常有兩個(gè)誤區(qū)。
一個(gè)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忽視剎車的作用。就如同奧巴馬一樣。一輛沒有引擎的汽車,最壞的情況是不能開動(dòng),但一輛沒有剎車的汽車,開起來就如同闖入瓷器店的公牛,會(huì)把周圍的一切都給毀了。
前一陣子默克爾終于開始反思她在難民問題上的政策,她想回到美好的昨天,但為時(shí)已晚,是她不懂得剎車的道理,才毀掉了歐洲。這個(gè)誤區(qū),今天很多人已經(jīng)看到了。
但是,還存在第二個(gè)誤區(qū),常常被人們忽視,那就是把引擎和剎車搞反了。
在一個(gè)和諧的社會(huì)里,有動(dòng)力的人應(yīng)該成為引擎,有經(jīng)驗(yàn)的人應(yīng)該成為剎車。這個(gè)道理大部分人都懂,但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很多人卻不這么做。
中國(guó)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是把全社會(huì)每一個(gè)人求富的動(dòng)力釋放出來了,而不是像“文革”時(shí)期那樣,由國(guó)家告訴人們?cè)撟鍪裁础?/p>
但是,總是會(huì)有人癡迷于頂層設(shè)計(jì),本該起剎車作用的卻去扮演引擎的角色,而下面該起引擎作用的卻不得不被動(dòng)地去剎車。
奧巴馬領(lǐng)導(dǎo)下的美國(guó)恰恰違背了建國(guó)國(guó)父?jìng)儗?duì)引擎和剎車良好的定位,才使得美國(guó)有了今天的尷尬。
回到個(gè)人,我們需要不斷地探尋怎么做的方法,也要不斷地了解什么事情不能做。這樣,我們駕車就自如了。
(摘自《發(fā)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