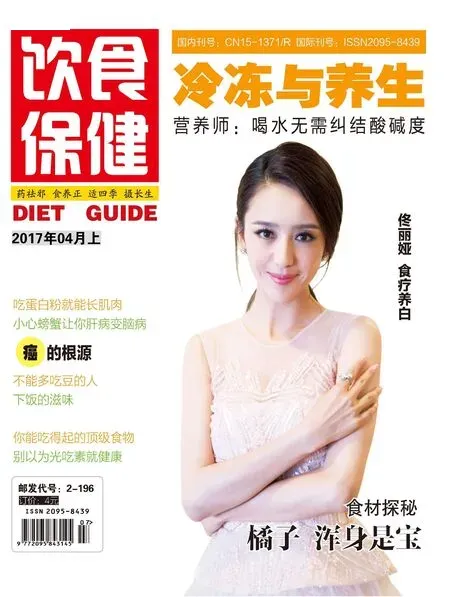《三生三世》青丘白淺的原型能吃人
文/夏秋
《三生三世》青丘白淺的原型能吃人
文/夏秋

大熱IP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收視率和網絡播放量都飆到了榜首的位置,自帶流量又賣力宣傳的大冪冪功不可沒。先拋開原著的抄襲爭議和叫座不叫好的評價,本文單純講一講女主角青丘白淺所屬的物種,其形象在中國的流變。
白淺是居住在青丘之國的九尾白狐,典出《山海經》,相信很多人已經知道了。《南山經》《東山經》《海外東經》和《大荒東經》都有關于九尾狐的記載,說它四足九尾,住在青丘。
《南山經》:“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之不蠱。”
《東山經》:“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蛭,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海外東經》:“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大荒東經》:“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山海經》這部奇書,初步形成于先秦,涵蓋了上古地理、歷史、神話、天文、歷法、氣象、動物、植物、礦產、醫藥、宗教、考古、人類學、海洋學等等諸多內容。東晉郭璞是最早給這部書做系統注解的人,他在《山海經注》中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做瑞于周,以標靈符。” 意思是說,總體上來講,九尾狐的出現是個吉兆,“太平則出而為瑞也”。那么從先秦到兩晉,九尾狐食人獸這種略兇惡的設定,是怎么變成吉兆的?
這得從大禹說起,《呂氏春秋》《吳越春秋》等古籍都記載了大禹娶妻的故事。這個故事說,大禹到三十歲,還是一只單身狗,有一天他再也不想看別人成雙成對虐狗了,想找個女子脫單。可天下之大,這個女子會在哪兒呢?
大禹一想,莫慌,上天必定會給我提示的。果不其然,他在涂山看到一只九尾白狐。正好這個時候涂山氏有女子在唱歌:“綏綏白狐,九尾厐厐。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咦,聽起來是個旺夫的姑娘,于是大禹就高高興興娶了涂山氏,后來生了兒子啟。從啟開始,世襲制代替禪讓制,大禹的后代們做為夏的首領,一直到桀被商湯打敗、夏朝滅亡為止。“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
這個故事顯示,看見了九尾白狐,不只能脫單,并且包生兒子,還是王者的征兆。
見此祥瑞,能脫單,多子多孫,還能稱王,愛我你怕了嗎?
《禮記》和屈賦《九章》記錄了狐貍的另外一個特殊習性,據說它將死之時,頭必對著出生的山丘方向,被引申為禮不忘本。成語“狐死首丘”,就是這么來的。有學生物的來證實或證偽嗎?
這種靈獸,既代表多子多福,又代表王者之征,還不忘本,那豈有不成為祥瑞之理。吃人那點小事,就漸漸被淡忘了。漢代石刻像及磚畫中,常有九尾狐與白兔、蟾蜍、青鳥并刻于西王母座旁。漢代西王母的形象是擁有不死藥的神仙,九尾狐在她座旁,算得上是位列仙班了。
此后一直到唐朝,九尾狐或者白狐是四海歸一、太平盛世的象征。
曹植《上九尾狐表》:“然后知九尾狐。斯誠圣王德政和氣所應也。”
南朝《宋書·符瑞志》:“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焉。”
南朝蕭統《昭明文選》:“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
唐《藝文類聚·河圖》:“皇帝生,先致白狐。”《藝文類聚·瑞應圖》: “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
當然,其它普普通通甚至妖里妖氣的狐貍也是有的,東漢魏晉就有狐貍善于幻化的說法。比如《搜神記》寫過老貍化身為人與董仲舒對談的故事,也有狐貍阿紫魅惑人的故事。給山海經做注的郭璞所寫的《玄中記》,其中對狐的描述,就已經非常套路化: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盅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唐朝以來,狐貍的形象有了比較大的轉變,從“總體祥瑞、部分妖魅”變成了“介于神與妖之間而偏向于妖”。一方面是民間百姓依然設廟參拜狐神,“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另一方面,狐神,哪怕是最厲害的九尾狐,也多是以妖神的面目出現。這和佛教的推廣不無關系,曾經西王母的愛寵,地位沒有漢朝那么高了。唐代筆記小說里,狐妖狐魅作怪的故事漸漸多了起來,宋初編纂的《太平廣記》中收錄了不少這類故事。
安史之亂以后,把君王身邊的所謂“紅顏禍水”比作狐妖的情況,就更加冠冕堂皇。比如白居易在《古冢狐》中就把妲己、褒姒比作狐妖,“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增溺人心。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
兩宋時期,漢族政權常常處于北方民族的軍事威脅中,而契丹、女真、黨項、蒙古等民族,又都可以算作“胡人”,胡與狐諧音,因此這時候狐貍連帶著被憎惡,其形象已經完全妖異化了。當年的祥瑞九尾狐,被打落云端,稱作“九尾野狐”“妖狐九尾”。在白居易《古冢狐》“褒妲狐媚善蠱惑”的基礎上,宋人進行了選擇性加工,九尾狐化身蘇妲己魅惑紂王這一傳說流傳開來。
元代話本《武王伐紂書》在這個基礎上,以書面的形式固化了“九尾金毛狐吸取妲己精元并借用其美麗皮囊”的情節。明代小說《封神演義》正是以《武王伐紂書》為藍本,進行了擴充和改編。托《封神演義》的福,九尾狐變成了人盡皆知的壞妖精。
對于從不關注言情IP的直男來說,提起狐貍精,十有八九是這種情況:“嚇,狐貍精最早不是聊齋里的么?”可見《聊齋志異》對于狐貍精的描寫有多深入人心。
蒲松齡跳脫出了“女為狐媚害即深”這種厭女癥思維定勢,狐貍這個物種不再局限于“亡國害人”的單一設定。他塑造的女性狐妖,很多集美麗與智慧于一身,是可親近和愛慕的對象。象嬰寧、小翠、蓮香、和辛十四娘這些狐女,或純真嬌憨,或知恩圖報,或有先見之明,這在女子須“嚴守禮教”“無才便是德”的時代,還是挺難得的。
無怪乎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聊齋:“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藹可親,忘為異類……”
但聊齋里狐貍精們總是毫無所求、上趕著向書生自薦枕席,這種情節放到現在來看,是直男們念念不忘,也是很多女性嗤之以鼻的。
現代關于狐貍精的影視劇,要不就是截取聊齋和封神榜的一小段炒冷飯,要不就是披著狐貍皮的瑪麗蘇。大清早亡了,熱門小說、影視劇對于狐貍精的刻畫,仍然還是停留在“勇斗小三”“宜室宜家”的階段,這樣的劇情網絡播放量還達到三十億,相當于全國人民在網上平均看了兩遍,這還不包括電視臺的收視數據。
某種意義上,我國人民的喜好,和古人保持著驚人的一致,文藝工作者的想象力,則呈現出遞減趨勢,這真挺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