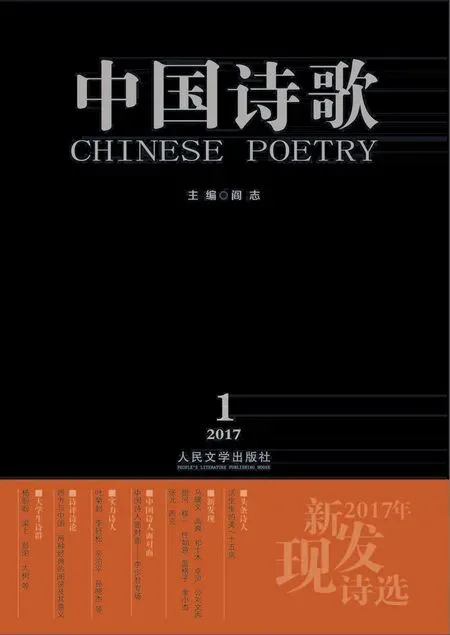混亂記憶〔組詩〕
金小杰
混亂記憶〔組詩〕
金小杰

1992年生于山東青島。就讀于山東某大學。菏澤市作協會員,菏澤市青年作協理事及簽約作家。作品散見于《中國詩歌》、《時代文學》、《山東文學》等。獲山東省作協“青春文學大賽”、“中國夢”主題征文三等獎,全國高校征文比賽、全國短篇小說大獎賽優秀獎等獎項。
有人痛哭,有人隱泣
床鋪不斷地騰空,又不斷地補滿
留下的,自封為王
逃掉的,可能一生都在流放
打卡,上班,把電子元件焊牢
十二小時倒班換班,站得雙腿充血腫脹
在這場戰爭中,誰都不是贏家
混亂記憶(組詩)
驚心動魄
十八歲外出務工,沒有學歷,沒有經驗
馱起一個比自己高兩頭的鋪蓋卷,擠上
嚴重超載的黑車。十八歲的江湖
很小,小到只剩下城郊的一個電子廠
水泥路,矮磚墻,風吹著風
吹得一車少年集體沉默
更加沉默的是宿舍的架子床
鐵架撞擊木板
木板疼,骨頭更疼
手中揮起的小錘把人生的第一場雄心壯志
敲得偃旗息鼓
深入生活
二十幾歲,在深信愛情的年紀卻篤信了生活
從云南到福建,老紀扛著全站儀
扛著拍下的三萬里云彩,一路逃竄
就業,賺錢,自己養活自己
畢業兩年,一腔熱血涼成半杯開水
知道人有很多活法,路不止一條
而深愛他的那個女孩
被留在山東,一等兩年
當初信誓旦旦許下的萬里江山
如今變成市郊還不完的房貸
太窮,窮到連自己都感到害怕
這不是我認識的老紀
老紀不寫詩,但很有情懷
失戀那天,他陪我暴飲暴食
拉著我在街頭疾走、逆行,只為趕一場電影
樹葉落下,折草莖為筷
我們分食同一罐糖水山楂
他說,果子酸,心更酸
但日子會越來越甜
莫名的樂觀,畢業后土崩瓦解成笑話
“當初太年輕”,這句話說得老氣橫秋
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錢
不知道什么時候適合衣錦還鄉
“好好混,等你戴著大金鏈子回山東。”
這是我同他最近的一次交談
火鍋城
鄉下人勤勞,起早。抵達之時
這座城市杯盤狼藉
值夜班的服務員從柜臺后爬起
短裙絲襪,失血般蒼白
染著黃毛的大廚熱心幫忙提行李
只提漂亮女孩的行李
宿舍在居民區,頂樓,沒有電梯
樓梯間有小姐摟著脖子和人說再見
也有單身職工出門上班,目光呆滯
仍舊是架子床。房間有門,有窗,沒有玻璃
二十個女服務員住八十平米,架子床擠成稻秧
交押金,簽合同,白紙黑字
簽下一張張甲方乙方,簽下一張張賣身契
夜晚,這座城市翻著白眼活過來
吞噬游客、金錢、冒泡的啤酒,以及
男歡女愛揮之不去的惡臭。當然,還有火鍋
酸菜魚、牛羊肉、牛油、豬肉,滿滿當當的水汽
“上班必須穿制服絲襪。”
年過四十的老板娘盯緊每個姑娘的大腿和胸部
鍋底沸騰,像極了這座城市
青椒、油菜、寬粉、香菇,每個人都尖叫著跳下水
“摸一下又不會死。”
老板娘坐在柜臺后點錢
點著姑娘們的尖叫,點著
每天夜里都會上演的這出戲
疼痛的高粱(組詩)
祖父曾是老酒匠
有高粱酒的地方就有英雄
叼著旱煙的祖父緊了緊褲腰
鋪下一張大紅的炕席
嗩吶響起,一響便是十里
祖母的花轎搖搖晃晃
搖晃起祖父釀的十八缸烈酒
搖晃起酒香馥郁的后半輩子
花轎落下,長起一片火紅的高粱
紅高粱,祖母的紅蓋頭
摻上地瓜炒得半生的高粱米
是黑酒壇里一喝便倒的烈性
是一群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青年漢子
釀酒的祖父,大半輩子抱著酒壇
守著自家的酒坊和婆娘
挑著酒擔走不出方圓百里
走得還不如缸里的酒遠
喝酒的祖父,一輩子也沒有成為英雄
躺進薄棺材的老酒匠
和烈酒、高粱糾纏的這輩子
除了手上的老繭,什么也握不住
扎笤帚的父親
父親瘦成了一棵高粱
麥收后的七月,父親要去看看高粱
看看站在田間地頭曬得漆黑的自己
父親是村里惟一的手藝人
是惟一一棵活到今天的高粱
母親的皺紋抻成笤帚把兒上的細繩
勒疼父親的脊梁
勒疼村頭老樹密密匝匝的年輪
紅高粱,十二個骨節
長成父親手上十二個月的老繭
父親最小的兒子遠走他鄉
分不清地里的麥子和野草
顛倒日夜,混淆了太陽和月亮
父親擎著一棵孤獨的高粱
一棵掛滿淚水斷了根的老高粱
身前空空,身后空空
找不到另一雙布滿老繭的手掌
高粱熟在九月的村莊
九月的村莊沒有高粱
扎笤帚的高粱、編席子的高粱、織斗笠的高粱
統統衰老成無人認領的遺產
父親瘦成了一棵高粱
蒼老的九月,父親要帶我去看看高粱
看看那棵祖父傳下來我扛不動的高粱
一棵患病的高粱
我生在北方
陽光下的村莊高粱般生長
盤根錯節的疼痛在地下延伸
結出的果實火一般滾燙
我就是那棵深夜喊疼的高粱
吃高粱米的祖父做了一輩子酒匠
釀出的烈酒灌醉了方圓百里的土地
灌醉了祖孫三代喝酒吃肉一呼百應的英雄念想
釀酒的祖父留下一只黑酒壇
父親光著脊梁
挖出埋在后院的十八口酒缸
又和烈酒、高粱斗爭了大半輩子
最終還是失敗收場
扎笤帚的父親抱緊高粱穗子
長成了北方二十四節氣的村莊
我就是那個深夜出逃的小兒子
兩手空空,喪失了土地、雨水、陽光
接過父親手中赤裸的高粱米
尋不到三畝薄地將它下葬
十二個月的村莊
不見了長滿車前子、狗尾草的麥田
不見了蒲葦茂盛浣洗衣裳的大河
該怎樣安放
那流落在外的半只腳掌
那棵最為年輕的瘦高粱
扛不動祖父的烈酒、父親的笤帚
扛不動喪失土地喊不出疼的村莊
在東明
在東明,與莊子小酌
酒才喝了兩口,這個稀里糊涂的老頭就要化蝶
我一次次按住他,按住他內心的大雨
南華山上,光陰皎潔
從野外割回的茅草,質地柔軟
經緯交織,打成一雙雙溫暖的草鞋
日子清貧簡單,而人心坦蕩直接
登仙橋上,酒至半酣的莊子撒米、勸雨
最后一滴酒水落肚,一場大雨傾盆而下:
人心不可試,何況發妻
這個早已酩酊的老頭又要化蝶
他說,他要去找另一只蝴蝶
懷念葡萄
這一生,可以不去大澤山
但不能不嘗大澤山的葡萄
閑的時候便會莫名想家
想念搪瓷小碗里盛的小粒果實
月光好的時候,母親跪在井臺邊捶洗衣裳
父親蹲在門外有一口沒一口地抽著旱煙
葡萄架下,一只貍花貓剛剛睡醒
跌跌撞撞跑來的,是我的童年
我不擅長抽刀斷水,現如今
一張車票,一個歸期,一千多里風塵
我始終拔不出深陷異鄉的半只腳掌
中秋,一個人去車站等人
不清楚車次,不知道姓名
但終究會有人從遠方來,帶著故鄉
伯樂相馬
翻山越嶺之后
良駒難尋的失望結得比生鐵還硬
這個相馬的男人,沒有帶酒
只有太行山上的風,刮得人臉生疼
一同痛的,還有一匹瘦馬
山腳下,破敗的鹽車是馬匹終其一生的命
伯樂遇馬,在這里像是一場意外
只一眼,就讓這個威武的漢子哽咽難言
萬金難求的騏驥空有一躍千里的志向
卻始終掙不脫趕馬人手中那根破舊的韁繩
太行山上,風在嗚咽,馬在嗚咽,人也在嗚咽
這翻山越嶺相遇恨晚的疼痛和委屈
像是一場大雨,滂沱
對聯
研磨,順筆,鋪下大紅的紙張
不知道該寫些什么
太白撈月的鞋子還落在岸邊
東坡喝剩的半壺黃酒還留在桌上
我不會喝酒,也不會唱歌
李白和蘇軾的縱酒放歌,我都學不來
我的硯臺里沒有崇山峻嶺大河大江
更不會有日月星辰滄海桑田
我的心很小,愿望也很小,小到
一張紙上寫著風調,一張紙上寫著雨順
愛情
內心荒蕪的人在大談愛情
他們左擁右抱
強調著肉體不會說謊
二零一六年正月,我深夜不眠
有這樣一群人
在應該長心的地方
長了一顆腎
隱居
開始隱居
地址:手機,聯系人
開始畏光
開始不見天日
隱去身高、體重、年齡
屏幕上開出桃花十里
不必種豆南山
不必紡紗織布
更不必推杯換盞禮尚往來
自此定居網絡不問柴米
一座城
靜如空山
十指在鍵盤上輕輕嘆息
在長樂小學
這片土地盛產大塊的石頭
像當地的男人,方方正正
下車,問路,橫穿整個村莊
目的地是村頭一所小學,紅磚、矮墻
學校正在放假,沒有孩子
從村南到村北,路瘦成一根魚脊
我站在破舊的校門口,打量
下半輩子的江山
沒有自習室、閱覽室、圖書室
野花開遍整個操場
一個女孩怯怯地喊著“老師”
像一把鑰匙,所有的風都調轉了方向
陽光很好,風很輕,草穗正在結籽
一根粉筆,正躺在我的講桌上
致Z
我躲進山區小學,你逃往四川成都
都一樣的膽小,在盛大的人流中反復拷問自己
寫詩?還是討生活?聲勢浩大的反問
是一場大雨,把彼此淋到透濕
今夜,隔著幾千里的山山水水,你又一次告訴我
想回大巴山,種地、養豬,再不成占山為王
突然扯開嗓子唱當地的民歌
像在喊山,歇斯底里
卻怎么也驚不飛山間夜宿的林鳥
也只有我知道
你的對面,根本沒有山脈起伏
只有一堵墻和一部正在通話的手機
最后的茉莉
1
是怎樣的悲傷令百草落淚
我拂過淚水驟停的花蕾,指尖微涼
三年未見的瘦哥哥呵
我該怎樣向你形容,此刻手掌上
這若有若無的花香
2
你怎么還不明白
那年你站在花叢微笑的模樣
像輕輕吻過湖面的一片云彩
投在,我的心上
3
你不會來
但風會來,雨也會來
窗外的雨落得再緊一點吧
把滿園的花枝打折
你,可能會來
4
茉莉,這小朵小朵害羞的云彩
像小段小段的空白
你出門的這段日子
它們又填補了我內心大片大片的空白
5
我再也等不來你了
最后的這朵茉莉不會打開
一張咬緊牙關的小嘴
無論風,還是雨,都撬不開
撬不開的,還有那句:
我愛你
寫在二十五歲
身邊的女孩,只談成家,不談立業
不聲不響地結婚生子
不聲不響地歸于塵土,一生
只埋下半塊墓碑。沒有名字,只剩姓氏
二十五歲這年,她們每日梳妝打扮
等一場風花雪月,等一個遠道而來的
男孩。或者在等一場聲勢浩大的葬禮
借機埋下昨天和今天
還有分毫不差的明天
二十五歲的女孩們,歡天喜地蓋上蓋頭
心甘情愿地,釘緊棺蓋
原諒
——給T
原諒你的不辭而別,原諒你
承諾之后的食言
我也原諒這夜色,太過深沉
太過肝腸寸斷
如果無法原諒
就無法遇見
比如大風刮過的天空
比如這場大雨過后星空的璀璨
我原諒你,也是在原諒我自己
拋開別離后的刻薄和偏見
你尋你的河流
我找我的雪山
長發
這一頭長發像是一場美麗的牽絆
它們生長、茂盛,長成小片的森林
勾住那些浮在半空裝滿油鹽的瓶瓶罐罐
勾住那些冒冒失失闖進森林腹地的男人
同時也勾住我,勾住我朝向死亡飛奔而去的腳步
除了這些密不透風的枝丫,我什么也看不見
想要剃度出家甚至連根拔起
但木魚已經隔得遠了,青燈也是
讀經的時候,會有孩子的哭聲傳來
我陷入生與死之間,這個漫長的過程
等到老了,滿頭的青絲會迎來第一場大雪
一生,轟然
奔向死亡
時間就站在身后
它“滴答”的腳步聲,像
一顆定時炸彈
綁在我的心上
被全世界拋棄
所有人都在開著玩笑,只有我一個人當了真
風刮過干干凈凈的天空,只留下一句:對不起
如果道歉能夠挽回錯誤,這世間
怎么還會有那么多的支離破碎
今夜,被全世界拋棄。所有的嘲笑都面向我
這個深情不減的女子,千瘡百孔還未放過自己
讓后半生的雨下個痛快吧,我不用你
去施舍,去同情,去可憐,去欺人,然后自欺
我親手扼住這顆奄奄一息的心,不想讓它復活,
只想讓它窒息
八月的風冷成刀子,一下下,剔除我那知冷知熱的血肉
從今以后,我感受不到冷暖,亦不知曉苦痛
秋天的柿子
我愛這泥土高濺的塵世
陽光強烈,水波浩蕩
我來到這最初,也是
最后的地方
埋下自己
如同埋下一顆秋天的柿子
這十月的風和陽光
又同我有什么關系
只想擇一窮鄉僻壤
在陌生的人海中奉子成婚
而這些枝頭高懸的甜蜜
曾是我成熟的乳房
赴莊子之約
沐浴,焚香,穿一襲寬大的袍子
日光還未回暖,南華山上百草無言
嗜睡的老頭至今還在追著蝴蝶
翻山越嶺,從未放過自己
今日赴約,沒有帶酒
南華山上的風烈成小刀
一下下,剝落我的衣衫,像風中
飛快翻動的古籍
一同翻開的,還有《莊子》
從“北冥有魚”到“外篇·馬蹄”
腳上一雙破舊的草鞋沾滿霞光、霧靄
竟然走得比命還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