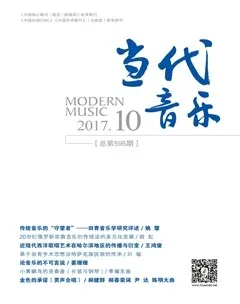傳統音樂的“守望者”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2233(2017)10-0005-04
在音樂學界,田青是不可復制的一位學者,不僅在音樂史、宗教音樂、傳統音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音樂評論等多領域頗有建樹,而且他所做之事,總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隨著自媒體時代的來臨,原來被封存在學術期刊儲備庫里、少有人問津的學術論文,通過“田青思想館”微信公眾平臺的推送與傳播,田青的一些精彩論文單篇閱讀量突破9000大關。其中,除了專業領域內的同行與學者外,更多的讀者則是來自專業領域之外、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積極關注中國傳統文化興衰命運的普通民眾。在微信平臺的讀者評論中,“傳統文化堅定的捍衛者”“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發揚光大的提倡者、推動者”等字眼會映入眼簾。那么,從專業領域的角度,又該如何看待田青的音樂學學術研究?從1979年第一篇公開發表的學術文章開始,田青30年來的研究成果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一、“中國佛教音樂”的整體性研究
如果說宗教類“非遺”的整體性保護理念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文化多樣性在中國“非遺”保護過程中本土化實踐理論探索的表現之一的話,那么當我們將時光機器退回到20世紀80年代,會驚奇地發現,無獨有偶,田青早年的宗教音樂研究也針對當時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地域性研究特點,在對全國東西南北、大寺小廟的實地考察基礎上率先提出了“中國佛教音樂”的整體研究觀。田青1985年引起學術界震動的碩士論文, 則是以超越地域性、區域性的“民間音樂”考察方法, 把中國佛教音樂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現象而進行的縱向考察與研究。
以此為開端,田青此后的宗教音樂研究則應用音樂史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史料的梳理與分析,在楊蔭瀏、査阜西、潘懷素等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撰寫了系列論文, 較為系統地回答了一系列中國宗教音樂的整體性問題:論證佛教音樂自天竺經西域傳入中國后,逐漸與中國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終形成中國化的佛教音樂;肯定佛教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遺產;厘清中國佛教音樂的分類 佛教音樂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唱給“佛”“菩薩”“餓鬼”等非現實對象聽的,可稱為“法事音樂”,包括佛教儀典(如佛誕、傳戒儀等) 、朝暮課誦、道場懺法(水陸法會、瑜伽施食焰口等) 中所用的音樂; 一類是唱給現實對象聽的, 可稱為“民間佛曲” , 起源與化俗法師的“唱導”, 從唐代俗講到今世流傳民間各地的“勸善”“佛歌”“經韻”等, 均屬此類。前一類的音樂淵源古遠, 代代相傳, 具有某種神圣的意義, 且不分南北, 為全國所有佛教徒所習唱。而后一類音樂則與各地民間音樂融為一體, 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 具有廣泛的群眾性。[1]、產生與發展的四個階段及其每個階段所呈現的特點 佛曲隨佛教傳人中國后,中國佛教音樂史大致經歷了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自東晉至齊梁的華化及多樣化、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四個階段。[2];系統梳理與總結了中國宗教音樂20世紀40-90年代五十年的前沿研究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發展脈絡;從不同角度全面論證了佛教、禪宗與中國音樂的千絲萬縷密切聯系,禪對中國音樂,乃至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
如果說楊蔭瀏結束了中國宗教音樂研究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記譜” 階段, 開始進入了整理、研究階段的話[3],那么20世紀80年代,田青則在對全國數百所寺廟的充分調查基礎之上,開啟了中國宗教音樂文化整體研究的新階段,打通了由時間與空間構建起來的中國宗教音樂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對話通道,而且在重新再現、睿智解讀中國宗教音樂歷史的同時,不忘回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活態的中國宗教音樂的寺院傳承與民間傳統,探尋隱秘在其中的文化密碼。
二、突破“禁區”
在我看來,以敢為天下先的膽識與勇氣突破固有思維定勢,不走尋常路地重新認識特定歷史時期中的人與物是田青學術研究的特點之一,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其一,率先突破宗教音樂研究禁區。20世紀80年代初, 有人認為“十年浩劫”已蕩盡了宗教音樂和產生、流通宗教音樂的土壤、場合, 并懷疑在中國大陸不允許對宗教音樂的研究或不具備研究宗教音樂的條件[4]。在剛剛迎來的“科學的春天”,田青就率先在《中國音樂與宗教》一文中指出:“這是一個過去被理論界長期忽視的問題。雖然建國后某些理論家如楊蔭瀏先生、潘懷素先生接觸了宗教音樂的問題, 某些音樂工作者也收集了一些宗教音樂, 但基本上僅僅停留在采風階段, 沒有深入研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左傾’思想的禁錮, 這是客觀原因;一是缺少宗教方面的知識, 這是主觀原因。”[5]
他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80年代宗教音樂研究領域的空白以及前人對宗教文化與音樂在認識上的誤解與偏差,并在此基礎上,田青對楊蔭瀏“如何對待我國的宗教音樂”的問題做出了明確回應。對于為什么要研究宗教音樂, 他總結了四方面的原因:宗教是意識形態之一, 是人類整體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宗教的認識, 過去頗有偏差;中國傳統音樂, 從總體上看, 是由民間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文人音樂四大部分構成,缺少對宗教音樂的研究, 便無法得出對中國傳統音樂的總體認識;現存的宗教音樂, 是一個急待開發搶救的寶藏。[6]
對于宗教是人類整體文化中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到:“一部文明史,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部宗教史。凡有一點歐洲藝術修養的人都知道, 二十世紀之前, 無論是歐洲音樂史還是歐洲美術史, 基本上是宗教音樂史或宗教美術史。中國文化受宗教( 主要是佛教、道教) 的影響也很大。王荊公日:‘成周三代之際, 圣人多生儒中, 兩漢以下, 圣人多生佛中’, 尤其是禪宗興起之后, 中國文人, 鮮有不談禪者。[7]”而對于宗教的偏差認識,田青當即認為:“對馬克思‘宗教鴉片’說, 是片面理解的例子。實際上, 宗教的產生, 一方面是人類在自然面前感到‘惱人的軟弱無力’的結果, 一方面, 也是人類想象力的空前發明, 是人類正確認識到自然規律與人類生活有著某種必然關聯之后希圖駕馭自然的一種勇敢而幼稚的愿望(如‘呼風喚雨’‘驅邪鑲災’之類)。宗教產生之初, (當然是自然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生產力的一部分,是一種特殊的生產手段。[8]”歷經三十載,這些觀點依然是當下學術界需要面對與認真思考的理論問題。在當下依然沒有完全開放的研究禁區,田青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果敢提出更需要直面問題的敏銳判斷與執著勇氣,他的突破開啟了改革開放初期宗教音樂研究的新認知。
其二,給予特定人與物以正面評價。在青主主張“向西方乞靈”之時,在崇洋媚外學習西方的社會思潮下,田青愿意做個“保守派”,守望中國的文化傳統;而在“文革”后的1983年,田青又是敢于以《浸在音樂中的靈魂——兼評青主的美學觀》為題第一個站出來肯定青主之人。他指出:“導師們沒有錯,青主也沒有錯,錯的是那個時代……”[9]
田青的《梁武帝與音樂》一文,在那個只能謳歌“工農兵”,把所有“統治者”都當成批判對象的特定歷史時期,田青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肯定梁武帝對中國佛教音樂的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指出他不僅創造了中國佛教音樂的第一個高潮,而且對后世中國佛教音樂的發展功不可沒。在1985年,梳理一個帝王的文化行為、為一位封建統治者尋找客觀評價的學理依據,是需要一定勇氣的,而文章開篇所引述的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論斷,則更像是為學術梳理找來的一塊名正言順的“擋箭牌”。
1992年,田青又一次打破尋常思維,選擇被視為“誨淫之作”的奇書《金瓶梅》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書中所保存的有關明代佛教音樂的大量現實主義資料, 窺見明代佛教音樂的一般狀況,肯定《金瓶梅》對佛教音樂研究中現存活態音樂與古代典籍樂譜之間在時空轉換中無法精準對接研究困境中重要的補足作用,認為《金瓶梅》對中國佛教音樂的研究具有極大幫助。[10]
青年的田青明白,一種學術觀點的確立往往以宏觀的社會背景為基礎,其好壞對錯皆需透過特定時代、特定歷史背景之鏡來窺探其究竟,而在不同時代中,那些跳出時代普遍認同之外、身上傳承著中國脊梁精神的、對后世文化有重要貢獻的人,無論時代用怎樣的標尺來丈量,田青則果斷地堅持自己的判斷,說別人不敢說、不愿說的話,為那些被時代遺忘或有意遺忘的人尋找話語空間。
三、以佛教音樂的鑰匙打開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方便之門
四十多年前,為了尋找埋沒在音樂史料中的民間活態傳承,田青背著一個“破錄音機、一壺水和一個裝著書和干糧的綠書包,睡在火車的座位下面,獨自參五臺、謁峨嵋、拜九華、覲普陀、涉敦煌,造訪前藏、后藏、安多、康巴數百所漢、藏寺廟”,深入窮鄉僻壤、深山老林里的荒郊野廟尋找宗教音樂的根脈。20世紀80年代,田青受邀擔任“中國音像大百科·佛教音樂系列”的主編,對漢傳、藏傳、南傳三大語系的中國佛教音樂進行了“原汁原味”的忠實記錄從1987年至今,“中國音像大百科”版的佛樂系列磁帶已出版:《津沽梵音》(2盒)、《五臺山佛樂》(5盒)、《潮州佛樂》(4盒)、《常州天寧寺唱誦》(3盒)、《九華山水陸》(4盒)、《云南佛樂》(3盒)等。,保存了中國傳統佛教音樂的精華,而且時至今日,隨著中國寺院佛教音樂的逐漸趨同化,這些20世紀80年代田青用錄音機記錄下的、蘊含各地地方特色的佛教音樂卻為中國留存了一筆再也無法復現的珍貴遺產。
以田野為積淀,田青不僅開啟了他的佛教音樂研究之旅,而且為了把這部分久不為人知的文化珍寶呈現給世界,他借遠赴世界名校講解佛教音樂的機會將傳統宗教音樂搬上舞臺 1989年春,田青率五臺山佛樂團參加香港第一屆中國佛教音樂國際研討會,這是中國佛教音樂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上亮相。。從1989年開始,他帶領五臺山佛樂團、天津佛樂團、北京佛樂團、拉卜楞寺佛樂團等先后出訪了十幾個國家和地區,以佛教音樂的名片為世界理解中國、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對話與交流提供了重要契機。
從1998年開始,田青又開始策劃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活動。2003年,在田青的促成下“中國佛樂、道樂展演”順利舉行,臺灣佛光山梵唄贊頌團與大陸的佛、道樂團一起在北京中山堂、上海大劇院同臺演出。2004年3月,在陳水扁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連任的關鍵時刻,田青作為藝術總監,組織策劃了包括漢傳、藏傳、南傳佛教三個語系、八大叢林兩岸佛教僧眾在臺北、高雄的演出,并親自擔任音樂會主持人,向觀眾宣揚兩岸“法乳一脈”、同根同源。2004年,此后由兩岸佛教界140名僧人組成的“中華佛教音樂展演團”,分別赴澳門、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地進行了盛況空前的演出,受到當地民眾的一致好評。田青正是在佛教音樂田野考察與學術研究的基礎上,用這一系列實踐活動打開了兩岸、中國與世界的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的方便之門。
四、反思中國民族音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發表于1986年的《中國音樂的線性思維》可以說開啟了田青學術研究的另一條關注現實之路,文中觀點也成為了田青后來撬動反思中國民族音樂命運之盤的一個有力杠桿。
《中國音樂的線性思維》從回顧西方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各自走過的不同道路入手,認為音樂是一種思維,由于地理環境、社會背景、經濟發展的差異,每一個民族都歷史地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思維性格和方式,強調了儒釋道三者對中國音樂、繪畫、書法、建筑乃至舞蹈線性藝術特征的塑造作用,并提出審美無法用“先進”與“落后”來判斷。[11]
在分析總結東西方音樂的過去中,田青首次提出,音樂審美與“先進”“落后”的標準無關,而這音樂審美與“科學”標準的關系論斷也奠定了田青后來對中國民族音樂現狀與未來系列思考的根基。在文章的最后,田青提出對中國音樂前途的思考:在一個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要振興我國的音樂事業,似乎也不應該只走一條路。我們一方面應該“拿過”西洋已發展到頂峰的“復音音樂體制”來創作我們自己的復音音樂;一方面,也不必以為我國傳統的線性思維是“落后”的。復音有復音的美,單旋律有單旋律的美。[12]
20世紀90年代,針對當時音樂界對民族樂隊與樂器改革中存在的問題,田青又將審美無“先進”與“落后”觀點應用到對民族樂器、樂隊改革的“彭修文模式”的批判與思考中。作為20世紀中葉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民族音樂的樂隊組合形式和創作模式,“彭修文模式”致力于將歐洲十八、十九世紀“古典音樂”和聲學、配器法、曲式學運用到民族器樂的創作中,并以西方工業社會的樂器制作標準和西方管弦樂隊編制為楷模完成對中國民族樂隊的改制。在此改革潮流中,田青清楚地看到:
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改革”,是以從“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屈辱史為背景的。在學習西方、振興中華的歷史重壓下,這些“改革者”們的愛國心、凌云志,以及他們出眾的才華和想象力,不得不用在了對西方音樂文化的模仿上。他們虔誠地相信只要把我們的民族樂器和民族樂隊“改革”成西方樂器和樂隊的樣子,我們民族的音樂文化就能擺脫“落后”的局面。他們不屑于深挖自己的傳統,在某種程度上,還有意無意地割裂了傳統。(如不去挖掘仍在中國民間流傳的類似“五調朝元”的固有轉調方式,不去向那些能用指法和“口風”在一支竹笛上轉五個調的老藝人學習而寧可犧牲民族韻味去追求“十二平均律”的“音準”)其思想的深處,其實還是一種隱蔽著的民族自卑感——認為我們的樂器和樂隊不如西方的樂器、樂隊“科學”;我們的混合律制,不如西方的“十二平均律”“科學”。其實,藝術不是科學,在藝術領域,也本沒有“先進”與“落后”的區別。[13]
以此為積淀,曾在20世紀末引來萬眾矚目的中央電視臺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又給予了田青將審美無“先進”與“落后”觀點引向深入的機緣,這一次他將目光投向中國民族聲樂的教育與現實中。通過電視銀屏,田青對民族聲樂“科學”唱法“千人一聲”“罐頭歌手”的批判一夜之間家喻戶曉,他也因此得罪了很大一批民族聲樂的教育家,但幾十年過去了,田青并沒有因此而改變過自己旗幟鮮明的主張,依然呼吁民族聲樂教育應該反省,藝術審美不應以崇尚標準化的科學、追求西方的“先進”而抹殺藝術的本質,呼吁“拒絕平庸,追求特色”[14]。
對于民族唱法“千人一面”的原因,田青認為,在許多中國人的潛意識里,不僅西方文明是“先進”與“現代化”的代名詞,而且“科學”也是真理的風向標,為了追隨先進與科學的步伐,中國付出幾代人的努力真心實意地效仿西方、崇尚科學,緊鑼密鼓地奔向心向往之的藝術現代化、標準化與規范化,其中就包括民族樂隊、樂器的改革和以西洋美聲唱法的美學觀和教學方法為基礎的學院派的“民族唱法”[15]。而造成上述現象的根本原因,田青則認為是時代的要求,隨著改革開放中國人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國民眾一方面進一步強化了對西方文化的認同意識,另一方面則開始有了一種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大國意識”的萌生,渴望得到國際的承認和尊重,而民族美聲唱法正是這一時代要求的產物。[16]
事實上,田青對過去與現在的歸納、總結與批判,為的是在明天能夠看到中國民族音樂一個更加美好、值得期許的未來,因為割裂了昨天和今天,也就不會有明天。
結 論
在人生的棋局中,田青以不卑不亢的精神品格面對生活給予他的一切,能夠在逆境困境、時代變遷、幻境紛擾的無常世界中不迷失自己,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在世事變化中堅守自己的信念,這既是田青品格與學術輪廓的勾勒與描摹,是田青對中國佛教音樂和民族音樂當下與未來命運的獨立判斷所呈現給我們的與眾不同,同時這不卑不亢也成為他面對現代化、現代轉型的社會和西方強勢文化對本土文化造成沖擊時所堅守的一種文化態度與勇猛決心。
這份堅守與決心使田青成為了當下音樂學界對中國“士”精神少有的繼承者:他的率先突破宗教音樂研究禁區、敢于給予特定人與物以正面評價是傳統文人氣節與風骨的附身;他的“中國佛教音樂”整體性研究的學術視野是中國傳統文人通才智慧的生動注腳;他對中國民族音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反思,以佛教音樂推動兩岸、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與對話是以天下為己任精神傳統的鮮活承繼。
近年來,田青因拒絕發展、積極提倡搶救與保護民族民間音樂而成為了民眾心目中的 “保守派”,但真正懂田青的人,應該知道他其實并不是個循規蹈矩、保守守舊之人。他之所以批評民族音樂的同質化,是因為更希望中國民族音樂能夠在全球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實現“和而不同”的多樣性發展、當代西方話語結構依然可以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共生發展,不在現代社會轉型中迷失自己。正如他所言:“我希望我們的音樂家們,能夠穿越近代中華民族的屈辱史,穿越‘五四’反傳統的傳統,找回淹沒在西方強勢文化語境中的屬于我們自己的話語系統,找回那些當我們的父兄在和我們一樣熱血沸騰的年紀里被他們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的孩子。新古典主義所追求的,是中華傳統文化在新世界中的重現、再生。我認為,無論是‘文化全球化’的展望還是‘后殖民主義理論’的沉浮,中國民族音樂只能唱著自己的調子走向日益縮小的“地球村’”。在現代化、同質化與西化的沖擊中不丟失自我是田青學術良知的底線,而當現實一次次沖破他的底線時,他首先要做的、能做的,則是義無反顧、斬釘截鐵地做一個中國佛教音樂、民族民間音樂的“守望者”。
[參 考 文 獻]
[1] 田 青.淺論佛教與中國音樂[J].音樂研究,1987(04):32—34.
[2] 田 青.中國佛教音樂的產生與發展[J].法音,1989(03).
[3] 同[1]
[4] 田 青.淺論佛教與中國音樂[J].音樂研究,1987(04).
[5][6][7][8] 田 青.中國音樂與宗教[J].中國音樂學,1986(03).
[9] 田 青.浸在音樂中的靈魂——兼評青主的美學觀[J].人民音樂,1983(10).
[10] 田 青.從〈金瓶梅〉看明代佛教音樂[J].中國音樂學,1992(02):76.
[11][12] 田 青.中國音樂的線性思維[J].中國音樂學,1986(04).
[13] 田 青.再談民族音樂的“第三種模式”[J].中國音樂,1997(03):6—7.
[14] 田 青.中國民族音樂的現狀和未來——田青研究員講座實錄[J].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4(01).
[15][16] 田 青.原生態——喚醒文化自覺與維護文化多樣性的契機[J].中國藝術報,2007.
- 當代音樂(下旬刊)的其它文章
- 書訊
- 薪火相傳傳道授業
- 金色的承諾(男聲合唱)
- 楊花吐蕊
- 長相思
- 小黃鸝鳥的變奏曲(長笛與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