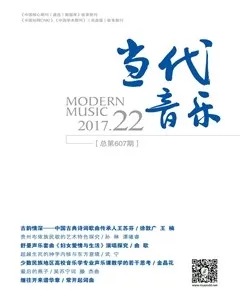超越生死的神學內核與東方意境
[摘要]
《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作為莫扎特不朽的杰作,不僅將單簧管藝術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也向世人展現了他音樂的至高境界。這其中滲透著莫扎特對于生命的感懷和超驗般的神學思想:他對于上帝始終保持一種“幸福感”的敬仰和信念,對于死亡有著超然脫俗的感悟和體認。同時慢板樂章也蘊含著東方美學的意境:“中和”“含蓄”“樸質”。而這高古超拔情狀中難得的寧靜,深沉傷感中迷人的憂郁,便造就了人類文化的“千年絕調”。
[關鍵詞]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慢板;神學;生死;意境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2233(2017)22-0024-03[HK]
《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創作于莫扎特辭世前兩個月
Concerto in A for Clarinet,K.622創作于1791年10月,莫扎特正是在這一年的12月5日去世。,但卻是歷史上最重要和最偉大的單簧管協奏曲,它是莫扎特單簧管協奏曲中的孤品,更是神品。
一、創作緣起
1發端——單簧管音色的偏愛
在西方音樂史中,為單簧管寫作協奏曲的作曲家寥若晨星,而莫扎特卻能為其專門創作《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足見他對這一樂器的喜愛程度。
其實,童年時的莫扎特就對單簧管的獨特音色鐘愛有加。在7歲時的歐洲巡演中,莫扎特就在曼海姆樂團的演奏中領略到單簧管的魅力,并傾心于它那圓潤柔和并富于幻想性的美質。
2歷經——單簧管創作的實踐
莫扎特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將單簧管視為重要的樂器并開始挖掘其藝術塑造的各種可能性,使得這件18世紀初才誕生的新生樂器,由最初的稚嫩提升至成熟的綻放。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唐璜》《魔笛》和《狄托的仁慈》中,莫扎特用單簧管深情如歌的優美旋律表現不同人物的特色;室內樂《bE大調五重奏》
鋼琴、雙簧管、bB調單簧管、大管、圓號。和《A大調五重奏》
A調單簧管、兩只小提琴、一只中提琴、一只大提琴。中,莫扎特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該樂器的音色性能;交響曲《bE大調交響曲》(作品第39)和《g小調交響曲》(作品第40)中,莫扎特卓有成效地發揮了單簧管的技術與表現力,為實現作曲家的藝術構思增光添彩。
3終成——單簧管演奏的保障
與單簧管演奏大師安東·斯塔德勒(Anton·Stadler)的友誼,也是促成《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這部經典之作的重要原因。斯塔德勒
斯塔德勒發明的帶有一個可以延伸至較低音區的單簧管(巴塞管),為莫扎特的音樂創作提供了樂器上的支持。是當時舉世無雙的單簧管高手,有著卓越的演奏技巧,他們之間長期的合作與交流,使莫扎特對單簧管已很出色的掌握更進一步,并最終激越而成這首“近乎完美”的上乘佳作,作品因而也被稱為《斯塔德勒協奏曲》。莫扎特起初是為斯塔德勒量身譜寫,所以便采用了他偏愛的A調巴塞管(Basset horn) ,它比一般單簧管擁有較廣的音域和較大的表現幅度,音色圓潤柔美,帶有一絲憂傷和黯淡,因此也與此曲的意境更為貼切。
二、文本分析
慢板樂章的曲式結構為三部曲式,分為ABA三段,舒緩的行板,明朗的D大調,律動的3/4拍。
A段共有四個樂句,是雙重成對結構(aa1bb1)。開始的樂句a,主要由A大調Ⅰ級主和弦的上行琶音分解的材料Ⅰ,以及三音連續下行級進的材料Ⅱ構成(見例1)。單簧管的音質極美,氣若游絲,開闊向上的感覺為根基,有以寬廣的胸懷擁抱世界、超脫于現實之上的感覺。隨后,附點四分音符加三個八分音符的節奏配以旋律的迂回行進構成了材料Ⅲ,收尾是莫扎特慣用的強化二度音的下行,夾雜著小倚音和附點八分音符的節奏型,形成材料Ⅳ。a句中蘊含的材料已經形成樂章發展的核心細胞,它們在之后的音樂進行中得以變化發展。句中溫暖人心的旋律在單簧管獨奏呈示之后,交由樂隊全奏重復,也就是a1句,這其中長笛、圓號、單簧管和小提琴共同參與到旋律的抒發中。b句先由單簧管奏出,采用了五個音的連續下行,是下行級進的材料Ⅱ與材料Ⅲ節奏模式的結合(見例2),由上中音進行到下中音,小調的偏離感濃郁,有淡淡凄楚哀傷之感,而且樂隊的插句更加強調了這一音樂下行的姿態。其后首次出現了十六分音符的音型,也依然是之前倚音加附點節奏、二度下行的收尾音,即材料Ⅳ。樂隊全奏的b1句中加入了大提琴和低音提琴與主旋律線條的反向行進和痛苦的半音化織體,從而使得音樂的戲劇性張力增強,陰沉的氣息襲面而來。兩個樂句對比可知,莫扎特采用了先揚后抑的方式,前一句旋律總體的走向往上,后一句則向下,并且總體的情緒基調也是平和中略露淡淡的憂傷,其中微妙的情緒對比,又是那么自然流暢,令人著實贊嘆。
中段,大致可看為A樂段的變奏式展開,情緒轉為烏云間隙中明朗的閃現。主奏與樂隊的關系,由A段的呼應式轉為獨白式,以突出單簧管獨立表情的抒發展現,樂隊的協奏若隱若現,僅僅給予和聲背景的支持和烘托。上行的主和弦變為迂回跳進式,十六分音符的節奏型擴張為下行的屬七和弦琶音組,三個音的連續級進下行和附點八分音符的音型(材料Ⅳ)仍舊可見。不過這里的琶音下行至低音區后立即折返到相隔1至2個八度的高音,跨度極大,盡顯單簧管高低音區音色的強烈對比,使純凈明亮的高音與低沉憂郁的低音對置,既能增加戲劇對比,又能展示演奏家高超的技藝。這一精彩的段落中,充滿了單簧管炫技式的華彩,莫扎特用圓熟的手法為單簧管布置了一個寬闊的舞臺,將這一樂器的特色發揮到極致。
再現段省略了a句的樂隊呈示,b句的樂隊全奏中,陰沉的半音化織體全面滲透,使人聯想到莫扎特當時凄涼的境況,淡淡的哀傷油然而生,且最后增加了一段內省獨白式的單簧管主奏,有種意味深長的眷戀和告別的情狀。
三、意蘊解讀
由于這首協奏曲創作于莫扎特離世前,當時他境況不佳,身染重疾,債臺高筑,生活環境相當窘迫,但我們從音樂中絲毫聽不出莫扎特的抱怨,反而是一種安寧柔和,恬靜澄澈。《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就各個層面而言都是杰出的上乘之作,這個迷人的作品會讓聽眾心境分外安寧,仔細聆聽,更會發現莫扎特單純的赤子之心。
1神學內核
由于莫扎特童年便從父親那里繼承的神學方面的教導,使他對上帝始終保持著堅定的忠貞和虔誠的信仰,這樣的一種心境也反映到他的音樂作品中。在他寫給父親的信中,他曾說到對于上帝和創造者由衷的“幸福感”和感激之情,并且祝愿周圍的人都能享有這種“幸福感”。即便在莫扎特與死神共舞的最后歲月里,這一理所當然的信念也從未動搖過。
聆聽這首單簧管協奏曲的慢板樂章,其中的感受是極其美妙的, 具有不可超越的美、力量和內省性。它能撫慰你的心靈,平和你的心境,使你的身心被從天而降的“幸福感”包裹。這里的音樂沒有宣講和說教,也沒有自我表現,而是用生命天然、謙恭地歌唱。縈繞在我們耳際的無字樂音擁有超越一切“美”所表征的品格,是一種無法言說的超驗的體認。其本質造成了一切對立的契合(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也因此而彰顯著基督教生命信條的神學內核。[BW(S(S,,)]
2生死觀念
作為莫扎特的蓋棺之作,這首協奏曲有著特殊的創作情境,因而也有著特殊的藝術價值。這是一個音樂家在生[JP2]命的彌留之際,其全部藝術理念和生命價值的升華與超越,散發出攝人心魄的藝術魅力。協奏曲慢板樂章從容平靜,我們可以明顯體會到莫扎特此時的心境,雖然經歷各種不幸和磨難,而且已經預感到死亡的降臨,但他沒有恐懼,也沒有過分的悲傷,而是坦然面對死亡,把死神視為自己的朋友,以極盡包容萬物的廣闊胸懷,從容不迫的微笑告別人世,這是莫扎特對于死亡的超越,是人性的過濾和升華。[JP]
莫扎特在訣別前給他父親的信中寫道:“既然死——仔細看來——是我們生命的真正終極目的,幾年以來,我便與人的這位真正最好的朋友相識了,所以,它的形象對我而言不再僅僅是某種令人驚恐的東西,而是頗為令人感到安寧和寬慰的東西!我感激我的上帝,他使我有幸為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創造機會認識死,將它看成是達到我們真正幸福之境的鎖鑰。”正是因為有了如此超然的生死觀, 他才可以在生命的彌留之際創作出這樣一部曠世杰作,而其中的慢板樂章也被譽為天鵝絕唱。其中雖然也有些許陰云籠罩,但莫扎特與身俱來的隱忍,洞察生命本質的睿智,使他最終正視生死,而這與中國道家的生死觀極為相似。
生,順應自然;死,亦順應自然。珍惜生命是道法自然的產物,而欣然地面對死亡也是道法自然的應有之義。莫扎特顯然對此有著相同的領悟,死亡對他來說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倘若從這一點出發,似乎才能更好地理解《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的感情基調,從而以樂天知命的角度參透音樂特征表象的深層緣由。
3東方意境
意境雖是東方美學特有的范疇,但由于音樂的相通性,我們完全可以用來理解莫扎特的作品。
莫扎特的音樂中總讓人體會到一種均衡感,富含音樂辯證法的有序世界在他的筆下完美展現。協奏曲中的獨奏樂器和樂隊之間是平等和諧的關系,在對話、對比和競奏中,達到前所未有的融合。這與中國音樂美學中的“中和”“中庸”思想如出一轍。
中國古代音樂的審美準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此慢板樂章中也有很好的體現。音樂所反映的哀傷從未過分,快樂而很有節制,莫扎特的情感表現總保持著一種理性的人道的控制。
中國古代音樂“意境”理論中強調的“靜”“虛”“合”,在此協奏曲的慢板樂章中也有很好的體現。音樂節奏舒緩,曲調寧靜,情景幽遠,單簧管的音色富有詩意,宛如唐詩里的鐘聲:“孤村樹色昏殘雨,遠寺鐘聲帶夕陽。”兩者皆清幽曠遠,皆非儒家入世的躁動,而是超塵拔俗的澄明。走向21世紀的人類,特別需要這澄明的充實,解除或緩和精神的焦躁、灼熱,使精神有所寄托。
中國道家代表作《淮南子》中曾有過“大樂必易”的說法,意思是說,越是偉大的音樂,其本身越是簡單,此處慢板樂章的音樂便是如此。莫扎特所采用的作曲手法并不復雜煩瑣,但一切都恰如其分,含蓄內斂,干凈清晰,“簡單”的音符卻生成了意味深長的深刻品質,達到了超越普通的美學境界。而這一切又源自莫扎特心靈深處的情感體驗,是他在生命彌留之際所達到的至高境界,已然觸及到人生中帶有永恒和普遍意義的“形而上”意味。
結語
《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作為莫扎特不朽的杰作,不僅將單簧管藝術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也向世人展現了他音樂的至高境界。這其中滲透著莫扎特對于生命的感懷和超驗般的神學思想:他對于上帝始終保持一種“幸福感”的敬仰和信念,對于死亡有著超然脫俗的感悟和體認。同時慢板樂章也蘊含著東方美學的意境:“中和”“含蓄”“樸質”。而這高古超拔情狀中難得的寧靜,深沉傷感中迷人的憂郁,便造就了人類文化的“千年絕調”。
[參 考 文 獻]
[1]孔繁濤.高貴的優雅 含蓄的傷感——評析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J].音樂創作,2014(03).
[2] 董德君.單簧管在外國作曲家交響樂與重奏作品中的應用[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04(03).
[3] 趙鑫珊.莫扎特之魂[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6.
[4] 于潤洋.試從中國的“意境”理論看西方音樂[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3(03).
[5] 李雅坤.以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為例,談莫扎特音樂與中國文化的共鳴——初探西方古典音樂在中國當代社會普及的方向[D].上海音樂學院,2012.
[6] 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 沈雨.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的音樂觀和哲學觀[J].大舞臺,2014(07).
(責任編輯:崔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