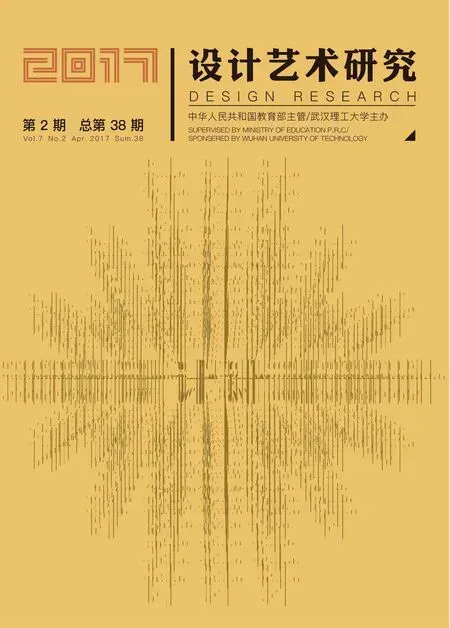繩床形制考論*
劉顯波LIU Xianbo 熊雋 XIONG Juan
湖北工業大學,武漢 430068(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430068, Wuhan)
設計歷史(Design History)
繩床形制考論*
劉顯波LIU Xianbo 熊雋 XIONG Juan
湖北工業大學,武漢 430068(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430068, Wuhan)
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是新型坐具大量傳來,中原地區逐漸加以接受的轉折時期,因此許多坐具的形制和稱謂都處在產生、分化、轉換的過程當中。繩床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文獻中僅載其名,未見有文獻專門描述其具體形制、種類,這造成宋代以后學界產生不少爭議。繩床作為中國早期高型坐具的代表,對傳統坐具的設計體系產生過重大影響,有深入探究的必要。本文以歷史文獻及相關圖像資料為依據,考論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繩床的形制及其演變發展。
繩床;早期高型坐具;坐具形制;高坐家具
繩床是一種坐面以繩編成、較寬大,可容盤膝而坐的高型坐具,約在魏晉時期隨著印度佛教的傳入而由中亞傳入我國,起初主要在僧侶階層中流行,到唐代早期,繩床逐漸在世俗生活中得到應用。唐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記載了印度僧侶使用繩床的情況:“西方僧眾將食之時,必須人人凈洗手足,各各別踞小床。高可七寸,方才一尺,藤繩織內,腳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掂隨事。”[1]可見,與胡床相比較,繩床的傳入和流行,帶有更濃厚的宗教色彩。和腿部交叉的可折疊坐具“胡床” (今俗名“馬扎”)一樣,繩床的創生地并非印度,而是來源于古代西亞、北非地區。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兩河流域已經出現了椅子。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也已經出現了象征社會等級的凳子和高靠背椅,目前保存的公元前15世紀的一件埃及矮凳實物,其坐面就是用繩編織而成(見圖1)。這種編織坐面的坐具大約很早就傳入印度,并且成為印度僧人日常修行時常用的坐具。

圖1 古埃及繩編矮凳
宋代以后,各類椅凳在世俗社會中日益盛行,逐漸取代了床、席在家具體系中的中心地位,隨著形制的繁衍,早期高型坐具“繩床”的名稱與形制的關系已發生了混淆。宋人程大昌《演繁露》載:“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唐穆宗于紫宸殿御大繩床見群臣,則又名繩床矣”。[2]程大昌認為繩床就是下部有交叉轉關結構的胡床。然而繩床之名,在唐穆宗以前的文獻記載中已多見,程大昌之說明顯混淆了繩床和胡床的概念。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為繩床的坐面與胡床一樣是繩編軟面;二是因為它們皆為外來家具樣式,在高型坐具流行的早期,世俗俚語中的“胡床”可能曾被用來指稱一切外來坐具,在長久的習用傳播中,各種名稱間的界線就容易混同。元代胡三省在《通鑒注》中亦曾講述繩床的樣式:“繩床,以板為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后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3]近現代學者多據此認為,繩床就是一種帶有扶手和靠背,坐面以繩編制、可供人盤腿其上的大椅子。實際上,根據古代文獻的記載,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流行的繩床并非僅有椅子式一種。
一、歷史文獻中記載的繩床
我國本土關于繩床的記錄最早出現在南朝梁《出三藏記集》、《高僧傳》等宗教文獻:
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后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后,即扶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余人,并聞香氣芬烈殊常。[4]
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丸瀾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愿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5]
《晉書》、《北齊書》也有數處出現關于繩床的記錄:
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咒愿數百言。[6]
三年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7]
查考這些文獻,其中無一不與一個姿態有關,即“坐”。我國古代文獻對姿態的描述用語非常講究,魏晉南北朝以來,曲肢坐的姿態主要包括跽坐、箕坐與佛教傳入后始流行的盤膝結跏趺坐。無論是席地還是坐于床榻,如果邊旁有物可供倚靠,必寫明“倚某物”,如西晉張華著有《倚幾銘》;《南史》卷十二載:“后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8]。描述隨新型坐具一同出現的垂足坐姿,如坐胡床、筌蹄則皆言“踞(據)胡床”、“踞(據)筌蹄”。繩床坐面寬大,人體常作盤腿坐姿,因而為“坐繩床”。與此相應的是,早期佛教文獻對繩床的記載也沒有專門提示它是否帶有靠背和扶手。《十誦律》記載,最初的繩床是一種無腳的坐臥兩用家具,后因有比丘在坐禪時入睡被蛇咬而亡,佛陀開始允許比丘在床下安裝床腳。①《四分律》中記載的繩床有五種:旋腳繩床、直腳繩床、曲腳繩床、入梐繩床、無腳繩床”[9],并嚴格規定了有腿繩床的高度范圍,超過則為犯律。《四分律》中記載五種繩床的樣式區別主要在于床腳的不同,沒有特別指出它是否帶有靠背扶手,但可以確定的是:其坐面由繩編成,主要功能是專門供單人盤坐。即使是帶有靠背和扶手的椅子式繩床,也是不能倚靠的,僧人在禪修使用時,要求“結跏正坐,項脊端直;不動不搖,不萎不倚;以坐自誓,助不拄床”,[10]即便帶有靠背和扶手,繩床的作用也僅僅是為坐禪的僧人圍合出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
《高僧傳》中還有這樣一則記載: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密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赍繩床自隨,于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床。[11]
這種僧人在乞食中隨身自赍的繩床主要用來修行打坐,不但不太可能帶有扶手和靠背,而且僅能供人盤坐容身,床腳也不可能太高。帶有靠背扶手的繩床,佛經中又有一專門的別名“倚床”。《大般涅槃經·壽命品》中有“敷師子座,其座四足純紺琉璃,于其座后各各皆有七寶倚床,一一座前復有金機”之語,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五釋其中“倚床”一詞云:“依綺反,《說文》云:依也。經文多作猗字,非也。如此國繩床,后有倚背是也。”[12]所謂“倚床”,就是帶有靠背的椅子式繩床,其名稱所指范圍,顯然比“繩床”要窄。
唐貞元年間(785年—805年)的《濟瀆廟北海壇祭器雜物銘》記載有“濟瀆廟北海壇二所器新置祭器及沉幣雙舫雜器等一千二百九十二事……繩床十,內四倚子”[13]。“倚子”是“椅子”的早期寫法,這里帶有靠背的繩床需要在十張繩床中特別標明,顯示出“倚子”屬繩床之一種。另《景德傳燈錄》中記載的五代僧人羅山義因禪師的一則公案云:
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像俱寂?”師曰:“有甚么?”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床、倚子。”[14]
為比喻“萬象齊生”,義因法語中的“繩床”與“倚子”顯然是相關而非等同的概念。從以上這些文獻證據可以看出,直至唐代,人們觀念中的繩床仍然至少分為后有倚背和后無倚背的兩種。
入唐以后,帶有靠背扶手的繩床逐漸在世俗生活中開拓其影響,與之相隨的是,繩床的靠背和扶手不再只起圍合出僧侶靜修空間的作用,而開始真正發揮可供身體倚靠的功能。文獻中與繩床有關的倚坐之姿,最早出現在唐代詩文中:
木槿花開畏日長,時搖輕扇倚繩床。(錢起《避著納涼》)
不出囂塵見遠公,道成何必青蓮宮。朝持藥缽千家近,暮倚繩床一室空。(韓翊《題玉山觀禪師蘭若》)
辭章諷詠成千首,心行歸依向一乘。坐倚繩床閑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白居易《愛詠詩》)[15]
這些可以“倚”的繩床,顯然屬于椅子式樣,但由于名稱上直稱為“繩床”,而不稱之為“倚床”,單從字面上也就很難分辨“繩床”是否帶有靠背扶手。《太平廣記》卷九五記載唐初高僧洪昉禪師事:
陜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為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今為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阇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16]
這段文獻中記載的繩床體制相當大,需要四人騎馬、各持一足,洪昉禪師盤坐在繩床上隨之而去。按情理分析,此處的繩床應是大椅子式樣,騎在馬上的人分持繩床之一足,繩床帶有靠背扶手,坐在其上的高僧才較為安全而不易墜地。②由此來看,唐初文獻中的繩床,已經很難根據字面來分辨其具體形制,也就無怪乎后世學者對繩床的名物關系爭論不休了。
二、南北朝流行的繩床形制
結合以上對文獻資料的分析可知,南北朝至唐代流行的繩床式樣確乎不止一種,參之以相關圖像資料,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繩床形象有三式。
其一多作平面四腿的獨坐榻式樣;其二則在坐面以上還帶有三面或四面圍欄,坐面一般較寬大,可供僧侶、信眾盤腿禪修。如敦煌莫高窟第303窟隋代壁畫《法華經變》中(見圖2),繪有四個坐繩床的僧人形象,其中兩張繩床為平面,坐面邊緣與面心異色,可能即為對編繩的描寫;另兩張則帶有三面圍欄,圍欄的立柱向上出頭。東魏興和四年(542年) 《菀貴妻尉氏造像記》中刻有一名僧人盤坐在左、右、后側帶有高度齊平的三面圍欄的繩床(見圖3),四根立柱都向上出頭。

圖2 敦煌莫高窟第303窟隋代《法華經變》中的繩床

圖3 東魏《菀貴妻尉氏造像記》中的繩床
再如陜西靖邊縣八大梁M1號北朝墓(北魏至西魏)出土壁畫中(見圖4),繪有一人坐在四面有圍欄的繩床上,圍欄左右兩面向后抬起,造成后側橫棖略高于前方,在后側圍欄處似還另插有一個編織而成的靠背。繩床的第三種形象是帶有扶手和靠背的椅子,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539年完成)西魏壁畫《禪修圖》中(見圖5),出現了帶有扶手和靠背的繩床。值得注意的是,這張繩床不僅明顯帶有靠背立柱和出頭的直搭腦,是完整的椅子形象,而且兩側的扶手中間嵌有壁板,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原傳統屏風樣式或是車廂造型的影響。作為一種兼有盤坐和憑靠功能的復合式家具,椅子式繩床對唐代及其以后中國坐具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圖4 陜西靖邊縣八大梁M1號北朝墓壁畫中的繩床

圖5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禪修圖》中的繩床
三、唐代流行的繩床形制
入唐以后,四面帶有圍欄的繩床逐漸不再流行,或許與這種樣式不便于日常使用有關。椅子式繩床則更受文人雅士的喜愛,在文獻中的記錄也就自然增多了起來,以至于宋代以后,人們普遍觀念中的“繩床”概念僅指椅子式繩床。明清家具中,有一類為文人喜愛的打坐用家具,坐面寬大可供盤坐,常為藤編軟屜,其中沒有靠背扶手的,稱之為“禪凳”,帶有靠背扶手的為“禪椅”,應當就是由兩種不同形式的繩床演變而來。從禪凳的存在也可推知,唐代流行的繩床依然有無靠背、類似獨坐小榻的形制存在,并對后世家具發展產生著持續的影響。
1.獨坐榻式繩床
獨坐榻式繩床在遺存的唐代圖像資料中較少,莫高窟第23窟北壁盛唐壁畫《法華經變》中,繪有一盤腿坐于方形四腿小矮榻的僧人形象(見圖6),矮榻榻面上敷有坐褥,由于它的樣式和供獨坐的唐代直腳床非常相似,僅通過壁畫圖像資料很難分辨坐面材質。

圖6 莫高窟第23窟北壁盛唐壁畫《法華經變》中的小榻
唐順宗元和元年(806年),日本學問僧空海返回日本的同時,帶回了其師長安青龍寺惠果大師饋贈的一批高僧畫像。這些畫像是畫家李真等人于唐德宗貞元年間(785年-805年)繪制的,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包括金剛智、善無畏、不空、一行、惠果五位大師的“真言五祖像”。空海回國后,又于821年請畫師補繪印度龍猛、龍智大師像,加上他本人的畫像,合為“真言八祖像”,目前仍珍藏在京都東寺(教王護國寺)。除不空金剛像保存完好外,其它的畫像雖存留下來,但畫面剝蝕難辨。所幸的是日本存在多個版本的畫像摹本,尤其以十三世紀鐮倉時代的摹本最佳。八位祖師中,除不空金剛坐于一方雙列壺門、帶有托泥的壺門榻,善無畏大師坐于一單列壺門、不帶托泥的壺門榻,惠果大師坐于一張椅子式繩床上以外,其它畫像中的高僧皆坐于獨坐方榻上(見圖7~圖9,左為鐮倉本,右為原本)[17],這些獨坐方榻,極有可能就是無靠背的繩床。尤其是金剛智畫像中的方榻坐面,似描繪有編繩痕跡,金剛智、龍猛所坐方榻的四腿皆以車木旋工旋成,疑即《四分律》所謂“旋腳繩床”。

圖7 《真言八祖之金剛智像》

圖8 《真言八祖之龍猛像》

圖9 《真言八祖之一行像》
2.椅子式繩床
唐代的椅子式繩床帶有靠背和扶手,與今天我們所說的椅子的區別僅在于坐面寬大且用繩織成,可供僧俗盤腿而坐。它的基本樣式,在敦煌壁畫、傳世繪畫及實物資料中有數見,以下就以具有代表性的數例對其常見的構造加以討論。
(1)靠背、扶手立柱出頭樣式
莫高窟第334窟初唐《維摩詰經變》中的繩床(見圖10)是迄今可見的唐代繩床樣式最早的一例,圖中繪舍利弗坐在一椅子式繩床上,除了坐面很矮以外,繩床的整個結構以方形直材相交形成框架結構,靠背立柱和扶手立柱皆向上出頭,其造型與東魏興和四年(542年)《菀貴妻尉氏造像記》石刻繩床形象(見圖3)具有明顯的承繼關系。此外,它的靠背中部裝有與扶手同高的橫棖,腿部上細下粗、向內傾斜,帶有明顯的側腳收分特征,這一點與285窟西魏壁畫《禪修圖》中的繩床極為相似。側腳收分似乎很早就出現在中國的框架式家具上,這個特征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家具文化現象。在敦煌壁畫中,立柱出頭的樣式并不一定總是一致的,如莫高窟第202窟南壁中唐壁畫《彌勒經變》(見圖11)、第61窟五代《維摩詰經變·法供養品》中所繪的繩床,搭腦橫棖向兩側伸出,而前腿立柱則向上出頭,顯示出這種式樣的變化性。

圖10 莫高窟第334窟西壁龕內初唐《維摩詰經變》局部

圖11 莫高窟第202窟南壁中唐《彌勒經變》中的繩床
立柱出頭的式樣,在陜西靖邊縣八大梁M1號北朝墓壁畫(見圖4)、莫高窟第303窟隋代《法華經變》 (見圖5)中的圍欄式繩床上都可以見到。立柱出頭在唐代椅子式繩床造型中的出現,是繩床早期流行樣式的一種遺風。在莫高窟第427窟中心柱北向面座沿隋代壁畫《須達拏太子本生》中繪制的一張僧人盤坐的繩床上(見圖12),扶手立柱的上端不僅出頭,而且修造成類似建筑欄桿望柱的蓮花花苞形態,這意味著這類繩床樣式逐漸出現了比較講究的做法。日本正倉院南倉藏有一張赤漆欟木胡床(日本文獻將繩床稱為胡床),是日本奈良時期寺院遺物,坐面尺幅78.5×68厘米,坐高42厘米,通高91厘米。

圖12 莫高窟第427窟隋代壁畫《須達拏太子本生》繩床線描
據記錄,部分材料為修補后配(見圖13)。該繩床坐面以藤編就,尺幅寬大可供人盤坐。它是以方形直材構造框架,靠背搭腦細而平直、末端出頭,靠背框架內裝有兩根橫棖,靠背下端橫棖及扶手橫棖以下,皆裝有三根短立柱來加固結構。扶手前端立柱向上出頭,頂端模仿建筑欄桿望柱樣式制成球形。四腿及坐面以上的立柱修造成上細下粗、略帶側腳的體式,使整體造型在穩固之外增添了挺拔開張的美感。從這張繩床構件末端和轉折部位包有鎏金銅具加固的情況來看,它應為一張制作精工、使用等級很高的繩床。

圖13 日本正倉院藏赤漆欟木胡床
日本正倉院所藏的繩床實物與莫高窟第427窟所繪隋代繩床相比較,搭腦皆為直型,扶手立柱出頭且加以精細的修飾,在造型上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在坐面以下,兩只繩床都使用橫棖加固,莫高窟第427窟繩床帶有接地的四根管腳棖,而正倉院赤漆欟木胡床腿間的四根橫棖則安裝在腿足上部三分之一的位置。腿部裝有橫棖結構,是隋唐以來繩床造型的新發展,它體現出隨著高型坐具的發展,繩床的高度也在逐漸升高,由于實用、穩固的需要,橫杖構件的設計由此誕生。
(2)靠背搭腦、扶手出頭樣式
這類造型的繩床在敦煌壁畫中最為常見,可能也是唐代繩床最流行的樣式。
莫高窟186窟窟頂東披中唐《彌勒經變》中繪制的一具繩床(見圖14),結體相當寬大,即使有一名僧人盤腿坐于其上,仍然可看出坐面用較淺的黃褐色料繪制,是敦煌壁畫中對編繩情況少有的清晰描繪。繩床以方材結體,靠背立柱間裝有一根與扶手同高的橫棖,靠背頂部安裝的搭腦為中部拱起、兩端略有上翹的弓形。搭腦末端及扶手末端皆出頭,腿間近地部位安裝管腳棖。腿部立柱上細下粗并向內傾斜,略帶側腳收分。莫高窟第23窟北壁盛唐壁畫《法華經變》、榆林窟第33窟南壁五代壁畫《經變式牛頭山圖》、莫高窟第98窟甬道頂五代壁畫《曇延法師圣容》、五代61西壁《五臺山圖》、東壁《維摩詰經變》等圖像資料中都有這一類型的繩床描繪。

圖14 莫高窟186窟窟頂東披中唐《彌勒經變》中的繩床
晚唐第9窟《維摩詰經變》壁畫中《舍利弗宴坐》 (見圖15)、《維摩詰與富樓那》都出現了繩床的圖像,除與前幾例有相似之處,如方材結體、搭腦和扶手末端皆出頭、靠背搭腦中部隆起、腿間加裝管腳棖、腿部線條上細下粗等特征外,扶手橫棖下還篏裝了板片,可見如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畫《禪修圖》 (見圖5)中的繩床扶手造法,到唐代還依然得到應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高窟晚唐第9窟《舍利弗宴坐》 (見圖15)、第98窟五代壁畫《曇延法師圣容》、榆林窟第33窟五代《經變式牛頭山圖》等壁畫中出現的繩床,在后腿及扶手立柱的頂端,用與主材相異的色彩各繪出了一個承托構件“櫨斗”。 《釋名》載:“盧(櫨)在柱端,都盧負屋之重也。”[18]“櫨斗”又稱“坐斗”,位于古代建筑中斗栱的最下層,它是斗栱體系中重量集中處所用的最大的斗,有時也可以單獨使用。在中國家具制作史上,唐代以前框架式家具的生產經驗并不豐富。入唐以后,受到新型坐具樣式流行的影響,框架式家具的生產需求日漸增加,這應是促使唐代家具制作匠師直接由傳統建筑構造經驗中借鑒、移植櫨斗結構的主要原因。

圖15 莫高窟第9窟晚唐北壁《舍利弗宴坐》中的繩床 (劉顯波繪)
(3)單側扶手樣式
前述皆為繩床的常式,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第148窟南壁盛唐壁畫《彌勒上生下生經變》中繪制的一張繩床(見圖16),僅有一側帶有扶手,腿間帶有管腳棖、腿部有側腳收分等,與常見的式樣差別不大。相似的例子還可見于莫高窟第138窟南壁晚唐壁畫《誦經圖》中(見圖17),可見這種繩床在當時并非罕見,有可能是為滿足使用者的特殊生活習慣或需求而造。

圖16 莫高窟第148窟南壁盛唐《彌勒上生下生經變》中的繩床

圖17 莫高窟第138窟南壁晚唐《誦經圖》中的繩床 (劉顯波繪)
觀察以上數例唐代椅子式繩床,我們可以發現它們有著一些共通的特征:其一是多用方材制作,少量使用圓材;其二是四腿多帶側腳收分;其三是靠背中部和四腿之間多安裝橫棖,前者便于倚靠、后者加固結構。在整體構造上的相同經驗之外,繩床的細節處理各有變化,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扶手和靠背的出頭方式,有橫棖出頭和立柱出頭兩種;其二是靠背搭腦出頭式樣中,搭腦有直線形和中部拱起、兩端上翹的弓形兩種;其三是腳棖的安裝部位或高或低,制作者可能根據整體結構的需求和視覺上的協調性而自由設置;其四是部分繩床上應用了櫨斗結構,這種結構方式與側腳收分一樣,都是從南北朝至唐代建筑結構中習得的構造手法,體現出此時框架式家具制作方法的發展性。以框架結構制作家具,在魏晉以前的中國傳統家具中并非主流,椅子式繩床的構造經驗,對以后框架式家具的衍進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作為一種外來坐具式樣,在傳入中國后經過工匠的發揮,產生出種種變體,為后世高型坐具的發展,積累了可貴的設計、制作經驗。
注釋
①(后秦)弗若多羅,鳩摩羅什等譯:《十誦律·卷第三十九》,“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集比丘僧已,語諸比丘:‘從今繩床腳下,施支令八指’”.②當代研究者楊森認為,這里的繩床指的可能是胡床,“持繩床一足”指四人各持一胡床,顯然不確。參見楊森《敦煌壁畫家具圖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頁.
[1](唐)義凈.王邦維注解.《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卷第一?食坐小床》[M].北京:中華書局,1995:31.
[2](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四》.
[3](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四二?長慶二年》[M].北京:中華書局,1956:7822.
[4](南朝梁)釋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十四?佛馱跋陀傳》.
[5](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上》[M]. 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2:246-247.
[6](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九十五?佛圖澄傳》[M] .北京:中華書局,1974:2486.
[7](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三二?陸法和傳》 [M] . 北京:中華書局,1972:431.
[8](唐)李延壽.《南史?卷十二?張貴妃傳》[M] . 北京:中華書局,1975:348.
[9](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第十二》.
[10](隋)智顗.《摩訶止觀?卷二上》.
[11](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譯經上》[M]. 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2:371
[12]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31.
[13](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M].北京:中國書店,1985:11.
[14](宋)道元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卷九》[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1793-1794.
[15](清)彭定求、沈三曾等.《全唐詩》卷三百二十九,卷二百四十三,卷四百四十六。
[16](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九五?洪昉禪師》[M].中華書局,1961:631.
[17]莊伯和.《佛像之美》[M].臺灣雄獅圖書公司,1980:155-158.
[18](漢)劉熙.《釋名?卷第五》(《叢書集成初編》本) [M].商務印書館,1939:87.
(責任編輯 喻仲文)
A Research On Rope Bed Shapes
From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is a period of change when large number of new seats came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and were gradually accepted by the people of the area. Therefore, so many of the shapes and titles of the seats are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change, and diverging from their original forms. The records of the Rope B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d before only covered its name, but no specif c description on its structure and categories, which created many controversies in this f eld after the Song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Rope Bed since it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China's early high-footed seats which has a signif can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design systems of seat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related image data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hapes and evolution of the Rope Bed from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rope bed;early high-footed seats;seat shape;high-seat furniture
J525.3
A
10.3963/j.issn.2095-0705.2017.02.006(0032-09)
2017-03-27
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2015105)。
劉顯波,湖北工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教授,明清家具收藏家,碩士研究生導師;熊雋,湖北工業大學木雁堂博物館執行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