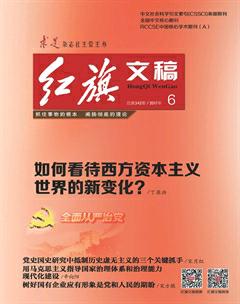新加坡為何陷入“中年危機”
趙宇新
新加坡建國后經(jīng)過幾十年的努力,建立起一個較為繁榮有序的現(xiàn)代國家,其改革成果一度被推崇為“新加坡模式”或“新加坡經(jīng)驗”。新加坡在社會治理和社會風險防控方面一直在世界范圍內(nèi)享有盛譽,為一些國家所效仿。但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的深化和國際格局的變化,新加坡經(jīng)濟增長放緩,由此引發(fā)一系列社會問題,給社會風險防控埋下隱患。中國在學習新加坡經(jīng)驗的同時,還須時刻保持理性檢視的警覺態(tài)度。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交融的移民國家,多元性主要來自種族、宗教、移民和經(jīng)濟全球化。這些天然分歧和緊張關系,構成了擾亂新加坡公共秩序、威脅其社會安全的風險隱患。新加坡自建國之日起,便把社會風險防控視為國家的戰(zhàn)略任務,并在長達50年的實踐中積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經(jīng)驗和做法。比如,新加坡注重涵養(yǎng)其共同的價值觀、注重樹立利益共享理念、注重良好警民關系的構建、制定國家反恐策略,等等,對其他國家的社會治理具有一定啟示意義和借鑒價值。
可以說,新加坡的社會風險防控體系曾有效保障了其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平穩(wěn)走過了50年。但是,近年以來,新加坡的經(jīng)濟社會治理理念逐漸暴露出種種弊端,特別是其理念在執(zhí)行或落實的層面出現(xiàn)了斷裂和諸多的問題。總體來看,其經(jīng)濟發(fā)展成果并沒有惠及每個人,政府也沒能兌現(xiàn)承諾,民眾紛紛抱怨生活中遭遇的種種困難,新加坡陷入其前總理吳作棟所描述的“中年危機”。新加坡群眾民主與權利意識擴張,網(wǎng)絡媒體不斷挑戰(zhàn)法治權威,騷亂事件頻頻發(fā)生,社會矛盾激增,整個社會彌漫著不安之感。新任政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挑戰(zhàn)一:經(jīng)濟增長放緩,成為社會風險萬源之首。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通過幾十年的努力,一度將新加坡成功打造成“亞洲四小龍”之首。2015年,新加坡遭遇前所未有的經(jīng)濟困境,當年經(jīng)濟增長率僅為2.0%,為6年以來最低。2016年未有好轉(zhuǎn),GDP增速仍為2.0%,其中三季度GDP甚至暴跌4.1%,是自2012年三季度以來表現(xiàn)最差的一次。經(jīng)濟衰退直接導致社會就業(yè)減少、政府財政能力和轉(zhuǎn)移支付水平降低、社會保障能力下降、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這致使族群和階層間沖突加劇、矛盾激化、社會分裂,民眾急躁易沖動,新加坡綜合性社會危機正在形成并初顯征兆。
新加坡經(jīng)濟來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依靠馬六甲海峽這一全球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二是在中國大陸投資建設工業(yè)園區(qū)獲得巨大收益,中國自2013年開始已經(jīng)成為新加坡的最大貿(mào)易國。不論新加坡是否承認,中國已然成為新加坡經(jīng)濟上的戰(zhàn)略伙伴。但近年來,新加坡似乎處處為難中國,視中國為亞太地區(qū)的頭號敵手。隨著國際經(jīng)濟形勢走低、貿(mào)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退出TPP,新加坡處境會更加艱難。
挑戰(zhàn)二:族群沖突頻發(fā),社會不公嚴重,國家認同度明顯降低。2012年,近百名中國籍巴士司機因不滿薪資和不公平待遇舉行罷工,打破了新加坡26年沒有罷工事件的記錄。2013年,400余名印度籍勞工與警方發(fā)生沖突并引發(fā)大規(guī)模騷亂,成為新加坡建國以來首個街頭騷亂事件。2014年,約6000人在芳林公園舉行集會,抗議中央公積金養(yǎng)老制度,批評政府運作不透明。這一系列罷工、騷亂和集會事件,反映了新加坡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種族矛盾已處于一觸即發(fā)的危機之中。其深層次原因是新加坡貧富兩極分化,特別是外來勞工遭遇不公平待遇,包括惡劣的工作生活環(huán)境、蔑視的態(tài)度、拖欠克扣工資等,有時甚至被迫與雇主簽訂“霸王條款”,為了保證續(xù)簽不被遣返,外來勞工只能忍氣吞聲。截至2013年6月,新加坡大約有130萬外籍勞工,約占總?cè)丝?4%;其《2015年人口簡報》數(shù)據(jù)顯示,新加坡外籍人口163萬人,約占總?cè)丝?0%。新加坡出生率低,發(fā)展經(jīng)濟需要依賴外來人口以保持競爭力。但新加坡政府沒能讓中下層民眾平等地從經(jīng)濟發(fā)展中獲得收益,縮小族群經(jīng)濟差距成為空談,“人人都有成功的機會”的治理方針變成口號。李光耀在其2011年出版的《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一書中也承認,在新加坡內(nèi)部,絕大多數(shù)人的國家意識淡薄,缺乏團結一致的凝聚力,國家認同度有所下降。如果數(shù)量龐大的外籍人口和外來勞工的社會問題得不到有效改善,新加坡也將面臨巨大的社會風險隱患。
挑戰(zhàn)三:經(jīng)濟轉(zhuǎn)型,移民政策收緊,身份差異和社會排斥凸顯。一方面,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并保證經(jīng)濟可持續(xù)發(fā)展,新加坡政府于2009年開始推動經(jīng)濟轉(zhuǎn)型,核心內(nèi)容是提升各行業(yè)的職業(yè)技能,增強企業(yè)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吸引各地頂尖人才服務新加坡經(jīng)濟建設。另一方面,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新加坡本地人抱怨外來人口推高房價、搶走飯碗、壓低工資、造成公共交通擁擠不堪,移民被視為“萬惡之源”。2012年,新加坡為配合經(jīng)濟轉(zhuǎn)型、順應民意,做出收緊移民和外勞、推行差異化政策的決定。本地人比永久居民擁有絕對優(yōu)先權,減少對永久居民的醫(yī)療補助金,提高低技能外勞配額和勞工稅,優(yōu)先聘用本地居民,限制外來人口就業(yè)數(shù)量等。這些政策激化了族群矛盾,降低了移民歸屬感,加速了社會排斥。2015年以來,新加坡政府為了應對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又適度放寬移民政策,但這并不足以解決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大量族群矛盾和社會問題。
挑戰(zhàn)四:生活成本提高,政府托底民生準備不足,民眾負面社會心態(tài)不斷滋生。與經(jīng)濟增長放緩相比,更令新加坡民眾感到失望的是在生活成本提高和貧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政府仍堅持自由市場和低福利政策,拒絕設定貧困線和最低工資,認為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是推動經(jīng)濟更加繁榮。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政府支付醫(yī)療費用不足三分之一,而經(jīng)合組織中發(fā)達國家的平均負擔水平為60%至70%;收入低于平均數(shù)一半的國民占總?cè)丝诒壤呀?jīng)從2002年的16%攀升到2011年的26%;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14年,新加坡基尼系數(shù)為0.464,高于國際上其他發(fā)達經(jīng)濟體。民眾感到生活壓力巨大,窮人掙扎在社會邊緣,72%的新加坡人認為自己“不能生病,因醫(yī)療費用高昂”。民調(diào)機構蓋洛普2012年底公布對148國15萬人的調(diào)查結果,新加坡人的幸福感最低,只有2%雇員對自己的職業(yè)有滿足感,而同年新加坡人均GDP位列世界第五。新加坡發(fā)展經(jīng)濟并沒有提高民眾的幸福感和生活水平。如果新加坡不能及時調(diào)整福利政策以適應民眾生存和發(fā)展需要,殘酷的現(xiàn)實會逼迫以外來勞工為主的底層民眾逐漸喪失對政府的信任,轉(zhuǎn)向以更加暴力的手段表達心中的憤懣。
挑戰(zhàn)五:新生代國民政治參與訴求強烈,對威權政府和精英統(tǒng)治帶來沖擊。2011年國會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支持率走低,家長制作風飽受詬病,僅獲得60.1%選票,輸?shù)?7個席位中的6席,首次輸?shù)粢粋€集選區(qū)。對人民行動黨來說,這已經(jīng)構成一次嚴重的“政治海嘯”,以往不容置疑的地位受到撼動。許多民眾并非真心希望反對黨執(zhí)政,而是為了讓政府里有更加多元的聲音,讓人民行動黨更注重傾聽民意。在經(jīng)濟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是另一大挑戰(zhàn),他們比父輩有著更多的政治參與訴求,要求更多的民主、更加透明的信息、更多不同的聲音、更多反對黨議員進入國會、更多政治競爭,要求允許民眾對政府的重要政策發(fā)表意見,打破精英統(tǒng)治的傳統(tǒng),變“為民做主”為“讓民做主”。同時,互聯(lián)網(wǎng)和社交新媒體的興起,更是大大降低了政治動員的門檻,提高了公眾政治參與度。這些均為普通選民提供了政治參與的可能,對新加坡的威權政治傳統(tǒng)造成沖擊。
總之,新加坡內(nèi)部的權利協(xié)調(diào)、利益分配和民主協(xié)商機制出了問題,伴隨著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的多重轉(zhuǎn)型,這些問題已成為誘發(fā)沖突矛盾、動搖社會穩(wěn)定的新增風險源,而新加坡政府對由此產(chǎn)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重視不夠、評估不足、治理不善,從而使其陷入“中年危機”。
(作者單位: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尹霞 馬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