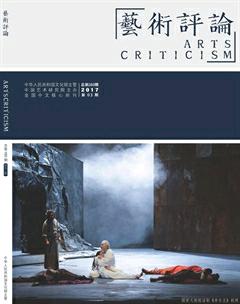陳映真與理想主義之困
劉奎
2016年11月22日,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在北京病逝。陳映真深受魯迅影響,是臺灣左翼文學的旗手,對海峽兩岸的作家都產生過深遠而重要的影響。本欄目特邀請海峽兩岸的兩位學者,對陳映真及作品進行重讀和述評,以紀念陳映真先生。
臺灣作家陳映真逝世后,坊間出現了不少談論陳映真的文章,部分媒體也有相關紀念,很多人在評價陳映真的時候,會提到理想主義者這個詞匯。在現在的社會語境下,部分人或媒體在用理想主義者來定位陳映真的時候,既是在借此緬懷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表達我們自己的文化鄉愁,也不乏是因難以充分理解陳映真的當代意義而采用的權宜說法,更有甚者則可能將這個詞匯等同于“落伍”之意。在我們看來,與其將陳映真標簽化地定位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倒不如試著去追溯他所理解的理想與他談論理想主義的方式。或者說,陳映真的當代意義或許并不是為這個社會提供一劑貼著理想主義標簽的強心針,而是他在理想缺失的年代如何理解理想主義,如何將理想主義付諸實踐的經驗。
在談及陳映真的作品時,以他學生自稱的蔣勛著意強調了“他作品中豐沛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并且說這是他對陳映真作品“不能釋手的原因” [1]。陳映真的作品確實有很多涉及有關理想的議題。無論是他早期作品如《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醫生》《加略人猶大》,還是后來的《賀大哥》《山路》《鈴.花》等,均是如此,如康雄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鄉村的醫生》中青年吳錦翔在戰后重新蘇醒的社會熱情,希望通過鄉村教育使下一代“建立一種關乎自己、關乎社會的意識”“務要使他們負起改造的責任” [2],還有《鈴.花》中持有革命理想的高東茂,《山路》中為革命理念默默付出一生的蔡千惠,更不必說《趙南棟》中所寫的監獄中那些堅定不移的革命者群像,都是讓人動容的理想主義者,至少也都抱有特定的理想和信念。
不過,陳映真筆下雖然懷抱理想主義的人物眾多,但前景又往往較為晦暗。無論是他早期小說中色彩模糊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后期作品中形象逐漸明晰的革命人物,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以失敗告終,理想主義都遭遇了重挫,如一度自認為再次覺醒的青年教師吳錦翔在絕望中終與康雄一樣走向自殺;蔡千惠在漫長的日常生活中淡忘了曾經的使命,在意識到這個問題后也以消極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獄中誕生的革命之子趙南棟更是徹底走向了墮落,等等。無論是其早期小說中人物的找不到出路,還是后期小說中革命理想被遺忘的主題,都體現了陳映真小說內含的歷史悲劇性。
從這個角度而言,陳映真算不得一個革命的樂觀主義者,或許也正因如此,蔣勛在提到陳映真的理想主義之時,著重于情感和美學的角度,強調的是陳映真小說感傷與憂郁情調與他們青年成長中的迷惘相契合的一面。這種偏重美學的理解,雖然也揭示了陳映真筆下理想主義的復雜性,但也無意中剝離了他筆下理想的歷史性,因為即便是從美學的角度來看,陳映真早期作品中的詩意風格,憂郁和感傷的情調等,與西方類型化的感傷小說也有所不同,與“五四”時期郁達夫式的自敘傳也有差異。簡單來說,經典的感傷小說如王爾德《道林 ·格雷的畫像》等,作品中的敘事者往往沉溺于自我與自我影像的封閉鏡像中,如臨水的納瑞斯一般是一個封閉的認知結構,而陳映真小說中的感傷與憂郁,固然也來自敘事者的顧影自憐,但小說往往帶有社會分析的視角,小說的詩意風格或感傷氛圍,多是源自現實對理想的阻隔所造成主人公視域中歷史遠景的缺乏,也就是說小說的感傷與憂郁是由社會結構帶來的,而不僅僅是認知結構帶來的。
陳映真筆下理想主義的歷史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筆下理想世界的具體歷史與社會內涵,一是他談論理想主義
的歷史語境,這實際上也是個二而一的問題。雖然陳映真筆下的很多人物帶有政治與社會的理想情懷,但在涉及理想社會的具體圖景時,又往往顯得異常謹慎,他很少像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梁啟超那樣熱衷于描繪未來社會,也與 20世紀 20、30年代的革命作家允諾一幅勝利的歷史畫面不同,他筆下的人物所追求的理想社會似乎都不太具體,即便是《蘋果樹》中詳細羅列的“幸福”的具體所指,如“一碗香噴噴的白米飯,澆著肉湯”“房子又高又巧,紅的墻,綠的瓦”“那個時候,再沒有哭泣,沒有呻吟,沒有詛咒,唉,沒有死亡” [3],等等,要么過于具體,要么過于抽象,缺乏新的社會與政治的生產性,并未從社會組織與制度等角度提供新的愿景。而在有的作品中,理想世界又往往因缺乏歷史感而流于浪漫,如《獵人之死》中,阿都尼斯設想的未來圖景,“那時辰男人與女人將無恐懼地,自由地,獨立地,誠實地相愛” [4]。或許正因陳映真并未正面描述他的理想世界,以致蔣勛在談論這個問題時也只能付諸猜測:“這個理想究竟是什么,我想,或許陳映真也不清楚,他只是模糊的感覺到,有這樣一個東西,深藏在人的心靈底層,可以使我們互愛、互助,免去貧窮、病痛、殺伐和不義。這個理想,不是什么主義,也不是什么具體社會改革方案,卻是人類心中普遍感覺到的對同情、對善良、對真理的永不放棄的追求吧! ”[5]陳映真筆下的新世界就如魯迅所設想的“黃金世界”一般,是關于未來的烏托邦想象,但又不愿填充具體物,最終讓它以留白的方式存在。但陳映真果真自己也不清楚他的理想社會嗎?或者說他的理想社會僅止步于人道主義式的對“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的同情嗎?可能并不完全是這樣。
陳映真筆下人物理想主義的源流并不難厘清,而且有著極為具體的現實性和歷史性,這就是中國現代左翼知識分子的文學、思想理論與實踐,以及共產黨的理論與社會實踐,這在冷戰時期的二元格局下其實更容易理解。 20世紀 50年代國民黨對臺灣的共產黨和左翼知識分子進行了清剿,左翼書籍被列為禁書,造成空前的歷史斷裂。即便如此,還是有少部分人能閱讀到這方面的書籍,陳映真小說《某一個日午》就描述了一位父親發現他兒子偷讀禁書的情景:
木箱的鎖果然是開著的。他翻著自己一直秘藏的里頭的四、五十年前的書箱、雜志、剪輯和筆記,發現每一頁都涂滿兒子的新鮮的眉批。房先生茫然地翻著,漣漣地淌著淚。他仿佛聽見兒子的聲音在信上說:讀完了它們,我才認識了: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幾年的生涯,都不過是那種你們那時代所惡罵的腐臭的蟲豸。我極向往著您們年少時所宣告的新人類的誕生以及他們的世界。 [6]
房先生的兒子偷讀他父親私藏的大陸二三十年代的書籍,而了解了“他們的新世界”,這也成為他進一步認清當下社會現實的資源。這個情節可能帶有自傳色彩,因為陳映真也有偷讀禁書而得到啟示的經歷,他在回答某雜志的訪談時就曾提及,“六○年代初葉,我因讀到一般讀不到的書,思想‘左傾了。于那時,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殘破的中國,并且對共產黨寄予很大的希望” [7]。這些書雖大多是《政治經濟學教程》《大眾哲學》一類的馬克思主義入門書籍,但為他提供了認識世界的鑰匙。同樣關鍵的是,他更早地閱讀了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作品。據他回憶,早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就讀過收錄有《阿 Q正傳》的魯迅作品集,并深受影響,“這本破舊的小說集,終于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 [8],后來他更是坦承“魯迅給我的影響是命運性的” [9]。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入門讀物和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批判傳統外,他對革命的認識,也有來自現實的社會接觸,如他被捕入獄后與外省政治犯的接觸,這種經歷在小說《趙南棟》中有所體現。《趙南棟》中的趙慶云在獄中見證了來自大陸的難友林福添、蔡宗義等人的斗爭過程,他們不僅具有理論的深度,在面對苦難時也能保持樂觀與從容,“以他們赴死時的尊嚴和勇氣,安慰和鼓舞了許許多多在押房中苦悶、懷疑、掙扎著的臺灣籍年輕的黨人 ”[10],這也讓一度迷惘的趙慶云從他們身上找到了具體的祖國和奮斗的方向。因此,陳映真筆下的理想主義雖然來源頗為多元,但左翼的傳統則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論資源和實踐傳統,理想社會的最終形態也或多或少地指向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左翼政治圖景,而60年代則更是具體地指向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
正因陳映真筆下理想主義的這種具體性,在臺灣六七十年代的戒嚴體制下,按趙剛的說法這是一個“留頭不留左”的時代,也是內戰與冷戰重疊的“極端年代” [11],陳映真是不可能將這個與敵對陣營密切相關的理想社會描述得那么清晰具體的;而其筆下理想社會并無定式的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為了保持理想社會的開放性,這實際上也是繼承了魯迅以來的批判傳統,對一切本質主義式的描述保持警惕。不過,與描述一幅田園牧歌的社會場景相比,陳映真顯然對理想主義在社會現實中的遭遇更感興趣,甚至可以說,陳映真筆下的理想主義更多地呈現為理想的受挫,也可說是理想主義精神在現實困境中的“鍛煉”過程。
陳映真筆下的理想主義基本上都呈現為受挫的狀態,這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歷史體驗和社會觀察的真實,在他看來,“特別在臺灣,理想主義受挫折、失敗,是生活上的現實。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吧,美國第七艦隊封鎖了臺灣,臺灣進行了相當徹底的肅清。進步的學生、青年、教授、新聞工作者、文學家和藝術家、工人運動者和文化人在臺灣的歷史舞臺上消失。剩下來寥寥無幾的、異數般的理想主義者,是殘缺的、不完全的、破相的。理想主義的勝利,首先必須要有堅強地為理想前仆后繼的人的存在。如果有人寫了一個‘積極的、‘光明的斗爭,在臺灣,那是騙人的” [12]。如果我們參照陳明忠的回憶錄《無悔》,以及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臺共黨人的悲歌》等系列報道,便能明了當時的歷史語境,國民黨為了肅清島內的左派勢力,進行了一場殘忍程度不亞于 1927年四 ·一二政變的剿殺,在理想頻受摧殘的風聲鶴唳中,侈談理想確實是自欺欺人。但這并不意味著理想主義的破產,相反,這既是理想主義接受檢驗的時刻,也為甄別理想的歷史有效性提供了可能。
理想主義不是空疏的口號與吶喊,不是止于書面的廉價烏托邦,而是人們經受苦難的考驗,經由現實的斗爭,在充分認識到其社會位置和歷史使命后生成的迫切愿望。較之空疏地談論理想主義,陳映真的確更為重視理想的承載者及其主體精神,而且往往讓理想主義者遭受各類的挫折,這包括政治環境的高壓、民眾的誤解、倫理的挑戰及庸常生活對理想的耗損等。正如趙剛所說,“陳映真是一個永遠的后街作者、后街思考者。他總是站在黑暗、卑下、貧困、受辱的后街,在那里尋找力量看到光明。他要為所有被這個時代所壓制所涂銷的聲音與足跡,透過他的書寫被救贖回來” [13]。其實他有時候做得更徹底,常將理想主義者置于更為絕望的領地,描寫他們“在組織性的恐怖中怎樣睥睨黑暗和死亡” [14],受挫者也很少有機會重新崛起,而是走向沉淪或走向生命的終結。他絲毫不愿給出廉價的允諾以便投機者或意志軟弱者可以蒙混過關。這種方式與魯迅的“絕望中的反抗”相類,在棄絕了希望之后的反抗或許才是主體意志確立的最佳契機,正如小說《賀大哥》中男主人公所表達的,“無寧是清楚地認識到不能及身而見到那‘美麗的世界 ,你才能開始把自己看做有史以來人類孜孜..地為著一個更好、更公平、更自由的世界而堅定不拔地奮斗著的潮流里的一滴水珠。看清楚了這一點,你才沒有了個人的寂寞和無能為力的感覺,他用英語說,并且也才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愛的、信賴的力量” [15]。理想在經歷了類似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后,才能讓人意識到自己在現實中的真實處境與歷史中的位置,從而保證其理想的真實性、迫切性與有效性。或許也正因如此,在20世紀 70年代末陳映真才能選擇從人民中國的視角重新確認其中國認同和革命理想。學者賀照田已詳細指出了他 80年代理想主義重構的這種現象 [16]。而他之所以能夠重構,在筆者看來,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他實踐理想主義的一貫方式,即從理想之困的角度認識并實踐理想主義,從這個角度出發,理想固然與人的全面解放這個總體視野相關,但更具體地體現為歷史實踐中的理想主義精神。
正是基于對理想主義的歷史真實性的認識,陳映真對虛假的理想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進入 20世紀 80年代后,臺灣的政治高壓雖得到一定程度的紓解,但理想主義并未因此而走上坦途,而是面對著來自消費社會世俗化及工業化的現代化虛相的新挑戰。對于消費社會所帶來的人的物化,及其所確立的新道德倫理觀,陳映真作了深刻的剖析與批判,如對擁有極大市場的倫理道德觀如 “只要努力,窮人照樣出人頭地”等,他就揭露了其隱含的意識形態陷阱,“這樣的道德,是實際上存在著社會差別的社會中流行的。在個別案例中,它有真實性。但從政治經濟學上看,就不是那么樂觀了。但這樣的 ‘道德,正是鼓舞著人背棄自己的出身。成功的人,光榮地升上更高的社會層級;失敗的人,懷憂以歿” [17]。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陳映真揭示出這類倫理道德實際上是服務于統治階層的虛假意識形態,除了對底層的安慰與驅導作用外,不僅不具有社會生產性,而且具有欺騙性。如果說這是對臺灣社會的內部階層結構的批判的話,那么,對工業化虛相及其相關的“美國夢”的批判則是基于世界結構的分析。這除了多篇的論說文外,他的小說《唐倩的喜劇》和“華盛頓大樓”小說,便對臺灣一度流行的“去去去,去美國”的“美國夢” [18],以及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運動作了形象而深入的批判。《云——華盛頓大樓之三》中專門設有 “American Dream”的小標題,來自美國的總經理艾森斯坦向臺灣下屬細致描繪了跨國公司所帶來的新的“美國夢”,但緊接著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卻在母公司與本土商人的雙重打壓下歸于失敗,不得不說這是對美國夢欺騙性的無情嘲諷。而對于臺灣工業化的“虛火”,他從世界經濟的結構分析了臺灣經濟的邊陲性和附庸性格,重新將臺灣錨定在第三世界的舞臺。這也是他批評文學領域中的現代主義思潮和消費主義風尚的結構:面對盛極一時的現代主義,他指出其殖民文化的性格,號召藝術家回到現實中,注重自身知性與思考的培養;而對于文學的消費主義,他則一再呼吁“文學應該負起解放的任務” [19],并將其他第三世界文學中的優秀作品視為這方面的典范,強調的都是民族的獨立、文學生產者的本土關懷和主體意志。而他自己也通過參與社會運動、創辦《人間》雜志等社會文化活動,積極介入社會現實。
在長期的寫作與社會斗爭中,陳映真從未試圖通過高懸理想以獲得同情,相反,他對那些廉價的理想給予了無情的批判,同時選擇將理想和理想主義者投入現實的熔爐予以鍛造,以鍛煉人的主體意志。這也提醒我們,理想主義從來不是高歌猛進,而是要在歷史的曲折中迂回前行,非理想主義的時代反而是孕育、鍛造并檢驗新人和新理想的契機。當下有人視陳映真的理想主義為“落伍”,是這個時代理想主義陷入困境的表征,而這也正是我們重讀陳映真并繼續實踐他的理想之路的時代意義。
本文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十年來臺灣社會思潮的演進與人文學術的發展(1950-2010)》基金資助,項目批準號: 16ZDA138
注釋:
[1][5]三十年代文學的承傳者——談陳映真的小說[I].陳映真作品集(第5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186,186-187.
[2]陳映真.鄉村教師[I].陳映真作品集(第1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29.
[3] 陳映真.蘋果樹[I].陳映真作品集(第1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 112.
[4]陳映真.獵人之死[I].陳映真作品集(第2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37.
[6] 陳映真.某一個日午[I].陳映真作品集(第3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43-44.
[7]陳映真.答友人文[I].陳映真作品集(第8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33.
[8]陳映真.鞭子與提燈[I],陳映真作品集(第9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19.[9][12][17]陳映真、韋名.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I].陳映真作品集(第6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34,36,40.
[10] 陳映真.趙南棟[I].陳映真作品集(第5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139.
[11]此借用霍布斯鮑姆的說法,因為兩次世界大戰,他將20世紀命名為極端的年代,見《極端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臺灣在“二戰”后,既延續了內戰,更是冷戰的前沿。
[13]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M].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98.
[14]蔡源煌.思想的貧困——訪陳映真[I].陳映真作品集(第6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130.
[15] 陳映真.賀大哥[I].陳映真作品集(第3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74.
[16]參考賀照田.當信仰遭遇危機——陳映真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論(二)[J].開放時代.2010(12).
[18]除了陳映真的小說外,也可參考陳若曦.堅持、無悔:七十自述[M].新北:新地文化藝術,2016:20-30.
[19]陳映真.作為一個作家[I].陳映真作品集(第8卷).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