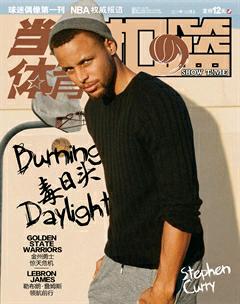毀譽先驅
段超

如今的勇士隊無疑是聯盟里最成功的球隊之一,他們用不斷的勝利讓聯盟相信了小球投射也能取得成功。有人說勇士隊的前身,或者說現在小球風盛行的先驅者是“風之子”引領的那支太陽隊,其實這并不準確。如果真要探尋勇士隊的前身,可能要追溯到1995-96賽季,而那支球隊那套陣容所做的一切,還要從他們的時任主帥迪克·莫塔的煩惱說起……
絕望起點
1995-96賽季,小牛隊幾乎陷于絕望之中。莫塔此時所執掌的這支球隊幾近癱瘓,或許他有著洞悉未來的本事,可他所拿出的應對之策在當時看來和抵死掙扎沒什么分別。賽季過半,小牛隊里充斥著傷病和各種各樣的意外,甚至于整支球隊幾乎找不出可以出戰的前場球員。好不容易湊成的三J組合,早早就被打散了,賈馬爾·馬什本只打了18場比賽就因為膝蓋手術賽季報銷;波佩耶·瓊斯因為膝蓋肌腱炎無法上場;特里·戴維斯則一直都是傷病纏身;切諾基·帕克斯總是受到背肌痙攣的困擾;羅伊·塔普利倒是沒有傷病,但他因為再次違反強制性毒品測試的規定被聯盟禁賽了……達拉斯只能用一些平時的第三、甚至是第四選擇的球員來充數。
誠然,身處絕境之時兵行險著才是有機會逆轉現狀的惟一出路,然而莫塔卻是個風格傳統的主教練,數十年的執教生涯他都墨守成規地堅持著中鋒至上、低位為主的戰術套路。“為什么要我改變呢?”賽季之初,他就是這樣反問記者約翰內特·霍華德的,“這一套總能奏效呀!”可當賽季行進至此,小牛隊的殘局已經無人可用時,同樣的戰術肯定行不通了。由于隊內沒有能夠執行背打戰術的中鋒,甚至連大前鋒都捉襟見肘,球隊的進攻根本無法從低位發起。沒有這種類型核心球員的小牛隊不得已走向了另一種極端。莫塔啟用了賈森·基德、球隊剩下的最好的中鋒洛倫佐·威廉姆斯和三名身高在1.98米左右的側翼球員同時首發。一夜之間,小牛隊將他們原本場均21.4次的三分球出手數驟然提升到了場均接近40次。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原本的三分球出手數就已經領先全聯盟了。
“如果比賽里大家在外線投射的手感不錯,那就表示我們已經走上了正軌。如果我們投得不夠準,那只說明我們投得還不夠多。”基德說道。
僅僅八天的時間里,小牛隊打的五場比賽全部都追平了、或是創下新的聯盟三分投射紀錄。其中擊敗籃網的比賽他們出手了49記三分,對手只在三分線外出手了5次,這一紀錄直到本賽季才被麥克·德安東尼率領的火箭隊超越。令人唏噓的是,這種全新的進攻方式之所以能夠提前誕生了二十年,完全是出于無奈。“整個晚上都在發生這樣的事情。”當時正效力于籃網隊,生涯后八個賽季都在小牛度過的中鋒肖恩·布拉德利說道,“我們每投進一記兩分球,他們就會回敬我們一個三分球。”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NBA并不以三分球為重,取勝最好的方式依然是在低位擁有像“大夢”奧拉朱旺或者是“鯊魚”奧尼爾這樣的內線殺器,側翼再布置一到兩名外線射手,用來針對防守球員的包夾戰術。這在當時是被認為利用球場空間、內外線進攻平衡最合理的戰術搭配,沒有誰會專門設計哪種戰術是以三分球本身為主要進攻手段的——所以莫塔的戰術會顯得格外另類。小牛隊在進攻時,一眾射手在跑動中迅速落位在三分外,基德則在半場進攻中低位單打身材較為矮小的后衛,試圖吸引對方的協防,接著會有一系列的戰術配置讓外線依次出現兩到三名射手獲得遠射三分的機會,并且還經常伴隨著手遞手傳球和曲線跑動,這都是當年最有效戰術打法的標志。
“我們一直在不停地持球突破然后再分球。”球隊里在小球戰術中擔任前鋒的喬治·麥克勞德說,“有很多打法都和現在金州勇士隊非常相似。我們會在弧頂快速掩護、低位掩護并延阻防守者,總之在弱側能找到很多方法來制造進攻機會。”
新鮮手法
小牛隊推出這樣的戰術以其“大逆不道”的顛覆性瞬間就震驚了全聯盟,當然,多數的反應還是吃驚之余的看衰。雖然類似的進攻戰術在其他球隊里也能見到,而且大部分也是精心設計的,但對于時間和空間的把握讓小牛隊的打法獨一無二。在傳統保守的進攻戰術中負責傳導球的隊員,在這里同樣會被要求果斷出手投籃。一支飽受傷病困擾、或者疲憊不堪的球隊是無法保證進攻的耐心程度的,所以他們寄希望于所有被創造出來的機會,任何一個空位機會都會出手。“當球員有機會出手的時候,主教練總是喊著讓他們快點投籃。”時任助理教練基普·莫塔說道。而球員們也的確這樣照辦了。
小牛隊的球員們喜歡這個外線火槍手的角色。自從開始執行小球戰術后,麥克勞德場均出手的三分球次數甚至比當時兩支NBA球隊的出手都要高,而他那個“公爵”的綽號也正是由此而來。隊內得分王吉姆·杰克遜被隊友稱為“懷特亞·厄普”。“因為他總是在外線開火。”威廉姆斯向記者這樣解釋道。全隊都會叫基德為“霍樂迪博士”,而盧修斯·哈里斯,因為他那致命的外線投射,所以獲得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綽號。托尼·杜馬斯是一名極具爆發力和運動天賦的球員,自然而然地被隊友們稱為“比利小子”。“因為他既年輕又極具破壞力。”威廉姆斯說道。
小牛隊的訓練也因為這種絕望之中產生的戰術而變得“喪心病狂”,球隊要求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外線進行投籃練習,每名隊員,包括具備投射遠距離兩分球能力的中鋒,都被要求再增加射程。那個時候,NBA的三分線還很規矩,三分線弧頂和底角到籃筐的距離是相同的,對投射的要求比現在要低一些。聯盟大多數的球隊都在利用這種改變,但是沒有一支球隊能像達拉斯人這樣做得如此淋漓盡致。莫塔每個比賽夜都在激勵著自己的球員。如果球隊在比賽里出手了30次三分球,他就會要求大家準備好下一場投出35次。大家做到了的話,那么再下一場就試試投40次。如果剛過半場就已經投了20次,那就努力讓整場的三分出手數達到50次。
莫塔最有名的一個事例就是他曾明確指示球隊里的中鋒去干擾對手的罰球,因為他認為在規則里并沒有明令禁止這樣做。他不會放過哪怕是最微小的優勢,因為隨便哪一種打法都有可能是其他球隊完全無法適應的極端打法。對手們都不愿意和小牛隊比賽,而且也沒有誰能和他們一樣打球。“他們就像是掃蕩者一樣。”太陽隊當家控衛凱文·約翰遜說道,“比賽里你絲毫不能放松警惕。他們會不斷施壓,用三分球的方式擊潰你。他們簡直就是在滿場飛奔。”“不過還有一點就是,如果他們投不進三分球,那他們就輸定了。”
致命缺口
然而即便達拉斯人能投進那些三分球,他們依然避免不了輸球。使用小球陣容能給球隊帶來無盡的錯位機會,小牛隊固然可以利用麥克勞德拉到外線錯位單打對方的大前鋒,可他們脆弱的前場陣容也同樣無法抵擋對方兇猛的低位進攻。“防守端我們的確存在著對位上的劣勢,但是我們在防守中也一直在輪轉,不斷給對手設置著陷阱。”麥克勞德說道。
現在的NBA規則更有利于這種瘋狂的戰術,比如防守球員可以先發制人,占據球場上的有利位置來防止對手突破,或者給對方制造協防的假象,其實并沒有協防過來。但,在1996年,聯盟的規則是要求防守者必須明確目標,要么防守對位球員,要么上前包夾,任何在協防路線上的逗留都會導致非法防守的吹罰,那是只屬于NBA的、特定年代的特殊規則。一般來說,小牛隊在這樣的打法之下每場比賽都會被吹個三到四次非法防守,這都是因為內線的防守吃緊。即便他們拿出了非常出色的防守表現,也是球員們以消耗大量體力為代價換來的。
“一般來說,我們會和對手僵持,但最終輸的卻還是我們。”麥克勞德說,“比賽里不斷協防夾擊,到了進攻端我們還要滿場跑動,有時候實在是太累了,自然沒辦法拿下比賽。”
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時候某些環境下,創新并不意味著成功,而且恰恰是失敗要占到多數。這支小牛隊的戰術詭異到令人難以置信,就像20年以后他們的后輩所做的那樣,只是他們的戰績只有26勝56負,勝利距離他們總是很遙遠。畢竟,那個時候球員們的技術水平、聯盟的規則以及陣容的架構都還不足以支撐一套如此新潮的打法。
助燃動力
達拉斯小牛隊當時擁有的球員里,最擅長打這種打法的只有賈森·基德。如果回首往日,恐怕多數人記住的只是那個生涯后期更加成熟穩健的基德,而對于當初那個初露鋒芒、年輕氣盛的基德,很多人都會記憶模糊。基德的確是個越老越值錢的后衛,在他38歲才贏得第一枚總冠軍戒指的時候,盡管第一步的爆發力早就不復存在,卻是一名絕對穩定出眾的組織者和全能的防守者。當年的小牛隊幾乎完全依賴基德來梳理球隊,對于那個時候的球隊來說,基德的價值幾乎涵蓋了全部,巧妙的傳球、穩健的組織,還有在關鍵時刻的投籃。相較而言,1996年的基德更加不可阻擋。“沒有哪支球隊能擁有像基德這樣的進攻發起者。”麥克勞德說,“沒有人像他一樣,1.93米的身高,95公斤的體重,在后場他能勝任兩個位置。想像一下,他比威斯布魯克更強壯,身高更高,而且還比他重,全場推進的速度也可能更快。他所展現的技術層次完全是在另一個次元的。”
如果拋開戰績不論,只說小牛隊的推陳出新,無疑那個賽季達拉斯是成功的,而在這份成功里,大部分的功勞都要歸功于基德。達拉斯人幾乎不再使用什么擋拆戰術,每次進攻他們就是依靠基德的突破分球,他會在每一個回合過掉與自己對位的球員,然后再把球安全地分到三分線外的隊友手里。讓基德落到低位單打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他幾乎比當時聯盟里所有的控衛都要高上一截。哪怕那個時候因為“魔術師”約翰遜的緣故全聯盟都在流行高大的控衛,在一號位上也很少有誰能在體型上限制住基德。他占據了極大的優勢,包括激發場上其他隊員之間的化學反應。
“如果我是他的隊友,我會送給他一塊勞力士手表。”莫塔在接受《圣何塞水銀新聞》采訪時這樣說道,“埃米特·史密斯就會為那些給他創造了機會的球員做這樣的事情。如果我能和基德一起打球,可能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拼命跑到自己最擅長得分的位置,他肯定能把球舒舒服服地送到我的手上。他天生就擁有這種能讓身邊所有隊友都變得更加優秀的能力。”
正是基德的存在,才把莫塔的理論變成了現實,而基德最大的依仗則是自己如風一般的推進速度。達拉斯全隊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多數量的三分出手機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德會主動將球快速推進到前場,在對手還沒有落位,甚至是還沒有回到己方半場的時候就將球送到了處于空位上的隊友手里。迅速的傳導分球會徹底改變對方本就因為沒有準備而凌亂不堪的防守局面,從而神奇地創造出很多4打3、或者3打2的機會。當然,基德也不會一味地求快,他也會有選擇性地放緩節奏讓對手不知所措,摸不到脈,從而為球隊創造出更大的優勢。而可快可慢,也是基德在策略上所展現出的最大優勢。
在他的節奏引領之下,這支小牛隊在進攻端是極度狂野無情的。即便聯盟里有個別球隊能夠跟得上達拉斯這群外線射手的腳步,他們也別想追上基德的節奏,甚至只是讓他那馬力全開的速度稍微降低一些,都會成為一項極其耗費精力和時間的任務。“很多時候,對手在防守端都希望能得到喘口氣的機會。”麥克勞德說道,“所以當你滿場飛奔外加快速出手的時候,對方的比賽節奏也會不自覺地隨著變快,但他們卻并不適應那樣快速的打法,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景。即便是放到現在,如果你想像勇士隊那樣打球,平時的訓練中你也得和他們一樣練習才行。”
失敗先驅
達拉斯小牛全隊的攻防轉換速度之快,甚至還給現場比賽播報員出了個不小的難題。球迷或者是媒體有時候在顧著手里寫的比分記錄時,會不知不覺地錯過某個快速攻防的回合。如果對手想要在比賽期間商議一下對策,也有可能一個不留神就被小牛隊甩在身后。“他們可沒有時間討論戰術。”基德說道,“我們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而這恰恰就是比賽的魅力。”
進攻上的順暢所帶來的可不僅僅是得分機會的增長,甚至還改變了隊員之間相處的氛圍。當年年輕氣盛的小牛隊球員們曾因為過于自負而付出了代價,比如吉姆·杰克遜和馬什本會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就產生了難以消除的隔閡,而基德的到來更是讓隊內未來領導者的地位有了很大的爭議。“你會在心底里希望NBA能有很大的進步,能逐漸形成成熟的機制。”基德在接受《達拉斯晨報》采訪時說,“你會認為球隊文化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沒有隔閡和爭吵存在,沒有一切內部的問題。但這是不現實的,而那樣的球隊也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
于是,馬什本的受傷成了一件喜憂參半的事情,憂的是球隊少了一個超強的得分手,而喜的是,球隊的緊張氛圍暫時得到了緩解,小牛隊開放式的進攻也因此得到了一些改觀。球隊一直在快速傳導球,球員們的工作也很簡單,進攻端他們只要努力跟著基德下快攻,就一定能得到投籃出手的機會。無論是中鋒拼了老命的跟進,哪怕只是能比對方內線球員早一步到達籃下,或者是隊內的射手們直接沖到三分線底角,籃球一定會準時準點到達,接著出手就可以了。基德、杰克遜和麥克勞德三人的場均投籃次數都超過了16次。“因為在進攻中擁有這樣的自由程度,所以每個人在打球的時候都很快樂。”麥克勞德說,“并不是只有哪位明星球員才占有多數出手權。如果這場比賽你的機會更多,或許下一場比賽就換成別人了。但是每場比賽你都不會被忽視,總會等到機會讓你進球的。”
話雖如此,不過當時的麥克勞德有時也確實過于放縱自己的自由程度了,比如在對陣籃網隊那場創下紀錄的比賽里,小牛全隊49次三分球出手,而麥克勞德一人就有20次出手,之后超越過這一紀錄的到目前為止只有J.R.史密斯、科比·布萊恩特和達蒙·斯塔德邁爾。當然,在當時的那個陣容里,麥克勞德也是惟一一個有資格這樣做的球員。在那支隊伍里,基德負責的是掌控全隊的進攻,雖然吉姆·杰克遜在馬什本缺陣時讓自己的場均得分領先了全隊,但小牛隊進攻的精髓人物卻是麥克勞德。比賽里恰恰是他為全隊進攻創造了最大的空間,三分球又是牛仔們的首要進攻手段,他的能力和基德的組織一樣,都是能夠讓小球戰術得以順利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像麥克勞德這樣的球員一旦落好位置,并給予他充分的出手權,整支球隊的進攻都會因此瞬間活躍起來。“我們得到了不少分。”基德說,“我們的確沒有贏下太多的比賽,但是至少我們在打球的時候都很開心。”
后世重提
那一年,小牛隊痛痛快快地瘋狂了一個賽季,當然,這份瘋狂并沒有讓他們獲得多高的成就,最終的成績單也不過是26勝56負,不要說及格,簡直就是個要被留級的成績。雖然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那支1995-96賽季的小牛隊是個跨時代的存在,而戰績不佳則是惟一一個阻止他們邁向偉大的障礙。畢竟,聯盟的潮流不會傾向一支被重重傷病所累、麻煩纏身、處于懸崖邊上的球隊,更不會有哪位教練會從一個賽區排名墊底的球隊身上尋找值得學習的亮點。
當然,莫塔之所以使用如此極端的戰術,也的確是被現實逼得無路可走,但卻從實踐之中了解并希望將此展現為小牛隊未來戰術的模板。可惜的是,從那以后就沒有以后了。在瓊斯膝蓋傷病痊愈以后,莫塔馬上就安排他出任首發,小球戰術依然存在,但那只是球隊偶爾為之的精彩罷了。三分球投射的數量最終也降到了他們當初堪堪領銜聯盟的水準,曾幾何時翻倍增長的瘋狂徹底不再。
賽季結束以后,莫塔自愿離職,小牛隊也在瘋狂之后重新歸于沉寂漸漸遠離了籃球界關注的視線,好不容易創造的存在感瞬間蕩然無存。而當他們重新被關注時,已經是數年之后,“瘋狂科學家”老尼爾森執掌的小牛隊了。
不得不承認,如果一件新生事物誕生在錯誤的時代,結果可能是褒貶參半的,只有等到時過境遷,后人重提之時,才有可能發現那才是偉大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