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行吟歌者讀苗秀俠《農民的眼睛》《皖北大地》
張曉東
在閱讀苗秀俠的兩部長篇小說《農民的眼睛》《皖北大地》過程中,我的腦袋里閃現過沈從文、張愛玲、蕭紅、余華、阿萊、哈耶克、畢飛宇、米蘭·昆德拉的影子,還不期然地記起過《論語》及一些西方大哲們的哲學論斷,我的這些無意識的連綴或許向我昭示了苗秀俠作品的某些品質。她不是在模仿,而是在回應一些偉大傳統的召喚。可以說,苗秀俠是位有情懷的作家,在藝術表現力上也已有相當積累,她毫無疑問地已在中國優秀作家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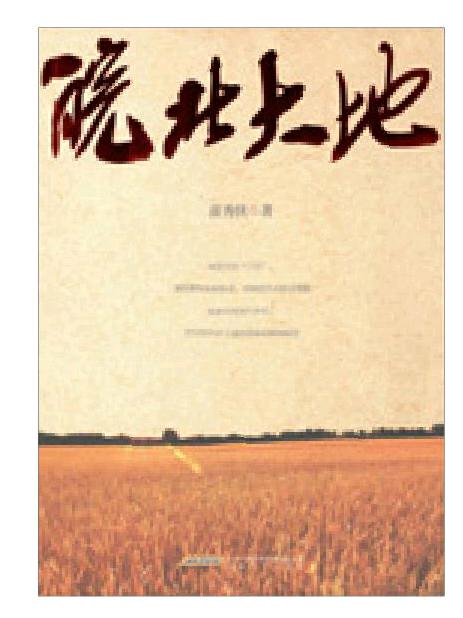
苗秀俠從來不在寫作中著意炫技,她的寫法一直“很老套”。她的這兩部近作則從標題開始就讓我眼睛一亮。《農民的眼睛》就像蒼鷹的“復眼”,很有巴赫金所言的“復調”意味,卻又聲色不露:農民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他又是小說的講述者;農民的眼睛是鄉村醫生“農民”的眼睛,又是天下蒼生“農民的眼睛”,還是躲在后面的苗秀俠那一雙深情憂傷的眼睛。《皖北大地》也很好,莽莽蒼蒼,悲壯蒼涼。扉頁上的題詞:“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大地卻永遠長存。”直接銜接《論語》中“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言雖盡于此,意卻在言外。苗秀俠懂得讓小說自己說話、讓人性說話、讓生活的必然性說話。兩部作品的命名,已足可看出作家的匠心獨運。
苗秀俠近年小說還成熟于對敘事藝術的理解。兩部作品的結構一個單純,一個稍繁復。《農民的眼睛》,敘事人農民講述了一串故事,一線到底的“糖葫蘆結構”;《皖北大地》多線結構,以大農莊、安大營、小龍河灣的農瓦房、安玉楓、老尾巴為主線,用人物的離去、歸來結構全篇,在每一個主要人物的背后牽扯出一個個廣闊的世界,縱深立體,展現了比《農民的眼睛》更廣闊的社會圖景。而在真正支撐小說的人物塑造方面,兩部作品更達到了相當的高度。《農民的眼睛》刻畫的是當代農民的群像,《皖北大地》里的人物要立體得多,農瓦房、安玉楓、老尾巴、楊二香、安云禮乃至一些著墨不多的如李文化都給人留下揮之不去的記憶。苗秀俠筆下的人物多面、變化、成長,再現了藝術的“過程性”力量。總之,我在苗秀俠近期的小說中看見了她的巨大進步,她已脫蛹化蝶。
讀苗秀俠,我不期然會想起沈從文,想起,無他,乃因“鄉下人”這個說辭。苗秀俠早已身居城市多年,是所謂文明世界里的白領精英,她的紅塵人生也早已與城市融為一體,像一尾自游自在的魚;然而,在人們通常所說的生命或性靈深處,她實在還是個“鄉下人”。而真正的寫作,從來都是靈魂的囈語,苗秀俠眷戀鄉土和所謂關懷三農的使命意識不過是自然而然的疊合罷了。表面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深里看是“生命的自然選擇。”
2012年莫言在諾獎頒獎會上的發言《講故事的人》同樣適合苗秀俠。苗秀俠也是個沉迷講故事的人,她陳述句式的小說標題就最鮮明不過地表達了這一點;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她已慢慢懂得了釋放敘事自身的力量,她也懂得自己所要站立的邊界和拿捏的分寸,“作者死了”的自覺意識讓她從自己的文字世界中抽離,她把“現場”交給了“敘述人”或者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她懂得“整體性”對于作家來說是其終生追求的目標,對人的“完滿性”的認知使她深深沉溺于人性的豐富與復雜,對真善美的渴望并沒讓她忽略對假惡丑的深度凝視。
《皖北大地》中最感染我的則是有關“人精”楊二香的篇章,特別是她和自己老公的前情往事,苗秀俠寫得真情動人。還有農瓦房對土地的癡迷也感人至深。“他喜歡順著樹身看到樹根,再目不轉睛地盯著樹根邊的地,那些被樹根牢牢扎實的地,散發出一股誘人的韻味。”“當老尾巴的幾片青幽幽的麥子地,突兀地鋪到農瓦房面前時,他的膝蓋骨不由地一軟,呼了一聲‘我哩個娘呀,撲通把自己摁跪下了。”“那些麥棵支棱著返春前柔嫩的小芽,像從土里伸出的一只只小手,拽著農瓦房的衣襟子、褲腳子、袖筒子。”“農瓦房跪趴著身子,把鼻尖杵到麥根子上,閉起眼睛,陶醉地聞著,嘴里嘖嘖有聲:‘你咋會有這么好的地,這么香的地,你咋弄的?農瓦房泣不成聲,‘你這個老頭子,你憑啥有這樣好的地塊,憑啥……”。
苗秀俠是在大地上行走的行吟歌者,她把中國鄉村的斑斕和傷痛,融注文字里面,讓文學的清音,繚繞于天地之間,撐開了逼仄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