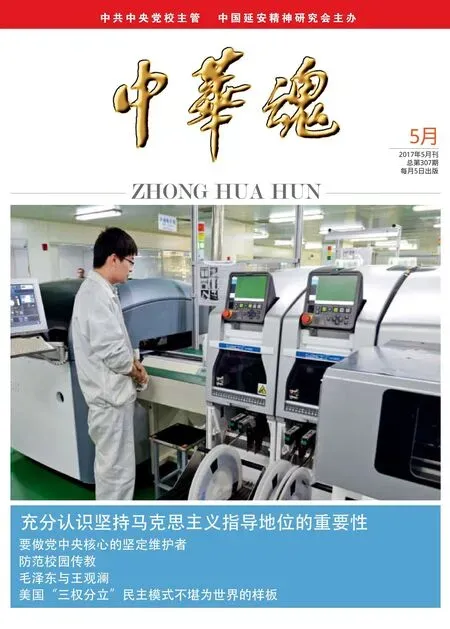我捐出了父親王琪壁的毛毯
文/王民培
未能忘記
我捐出了父親王琪壁的毛毯
文/王民培
我們的父親王琪壁是教育部的離休干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他正在西安。當得知日寇公開發動了血腥的侵華戰爭時,他立刻找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要求投身革命,報名參加八路軍,抗擊日寇的侵略。那時,他還不滿18歲。他的請求很快得到了批準,并被送往山西的民族革命大學學習、培訓。次年畢業,分配了工作。他參加革命后的第一個職務是連指導員。他深知自己連一天兵也沒當過,就直接當了“官”是組織的信任,也是肩上的重擔。所以特別努力。他當時不懂得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就是參加革命的開始,只以為是民族革命大學畢業正式參加工作才算參加革命。所以他填寫的檔案中參加革命的時間一直都是1938年。實際上應該是1937年的7月份,當然是“七七事變”以后。此事他后來雖然明白了,但他從未要求組織更改。
父親參加革命并擔任指導員后,拍了一張戎裝照片,照片上的他一派青春勃發,英姿颯爽:腰里系著皮帶,皮帶上還別著手槍。腿上打著綁腿,顯得格外利落。那照片鑲嵌在硬紙板上,父親在這硬紙板的背面寫下了這樣的誓言:
世界正黑暗重重,
全賴我輩來掃清;
黑暗凈盡之日,
乃我輩成功之時。
這誓言伴隨著父親沖鋒陷陣,勇往直前,奮斗終生。
父親被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批準參加革命后,組織上就給他們發了包括安置費、路費在內的幾塊錢的補貼。他從中拿出三毛錢,買了一條毛毯。那毛毯是用粗毛線編織而成,兩頭還留有毛穗穗,由綠色、粉紅色、灰色構成最樸素的格子圖案。父親有了這條毛毯,甚覺富足,開心。于是,不論行軍、打仗、生產、工作,他都不離開它。那毛毯為他御寒,為他防潮,或鋪或蓋都方便。打起背包來也簡捷,體積又小,被父親視若寶貝。

抗美援朝時期的王琪壁
有一次,一個戰士感冒了,還發燒。父親就讓他躺在炕上休息。又給他端來開水。然后又把自己那條毛毯拿來,疊成兩折壓在他的被子上。隨手把四角掖嚴實。說,多喝開水,再蓋得厚厚的,捂出汗來就好了。那個戰士不好意思地說,指導員,毛毯是你的寶貝,我不能蓋。父親笑著說,它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才算寶貝呢!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到底有多少人鋪過、墊過、蓋過、披過、裹過這條毛毯?真說不清。
還有一次,部隊行軍,夜宿在一個破廟里。那廟已經破得四下里漏風,更要命的是連窗戶都朽垮了,寒風長驅直入。父親就把自己的毛毯拿出來,叫了幾個戰士,一起把毛毯固定在窗框上,毛毯成了破廟破窗上的厚窗簾。別說,還挺頂用的,風頓時小多了。大家好歹能睡個安穩覺,能熬過這個寒夜,而且沒有人凍病。
又有一次,幾個人一起出去執行任務。不料半路上下起了雨。四下無處避雨。父親又是拿出了自己的毛毯,把兩個角固定在樹叉上,另兩個角人拉著,形成個斜坡狀的雨篷子,七八個人擠在“篷”下,大家稍微避一避雨,不至于都淋成落湯雞。
抗戰期間,有戰斗任務就去打仗。沒有戰斗時,部隊就練兵、學習文化,提高知識水平。毛主席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正因為學習文化如此重要,所以抗戰期間我父親不但自己在大學學習過,而且還當過聯校的校長呢。當時的小報上表揚他是模范校長,還特別舉例說,他竟然教一個啞巴孩子學會了說話。我們曾問他是真的嗎?他笑著說,實際上啞巴還是說不好話,但我確實教會他認識了600多個字。我們說,這也了不起。為了堅持抗戰,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不論在延安還是在太行山,都響應毛主席“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號召,搞大生產運動。我父親他們種的南瓜、土豆、茄子、豆角都豐收了。收獲的時候,大家一起干活。當然也有筐子、口袋可用。但是大家齊上陣時就不夠用了。于是有的戰士干脆把外面的褲子脫下來,把褲腳扎上,裝滿土豆后,再把腰扎上。然后,把裝滿土豆的褲子架在雙肩上,運回伙房的倉庫。我父親總忘不了他的毛毯,他干脆把毛毯鋪到地上,把南瓜、土豆、茄子、都放在上面。然后再找3個同志,一人抬一個角,唱著號子嗨吆嗨吆地把勞動果實抬回去。毯子臟了,抖一抖土照樣蓋。那個條件下,講不起衛生。
8年抗戰,我父親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太行山區戰斗和工作。所以他最愛唱的歌就是《在太行山上》。他那條毛毯也跟隨他在太行山里摸爬滾打,風里雨里,戰火硝煙里,地頭炕頭破廟里,不知又編織進去多少故事!
父親參加革命后,打了8年的抗日戰爭,接著又打了3年的解放戰爭。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奪取全國的勝利也指日可待。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了著名的講話。講了我黨我軍要“進京趕考”了。在千軍萬馬進京趕考之時,父親的考題竟然是“獨一無二”的!——上級命令他一個人把解放區的240箱文物國寶押運到北京。父親孤身獨膽一個人,歷盡千辛萬苦,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他把這240箱文物國寶交到負責人鄭振鐸手里,鄭振鐸驗收完畢后,感慨萬分,表揚說,王琪壁同志,一個不滿30歲的年輕人,獨自一個人從河北平山把240 箱文物國寶押運到北京,一件不少,一件沒損,了不起呀,有功勞!
1949年上半年進了北京后,父親被分配到中央教育部工作。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父親立即報名參加志愿軍。當時有同志問他:“琪壁,你不怕死啊?”他說:“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我們犧牲了那么多的同志!記得我第一次執行作戰任務時,我們出去的是12個人。可晚上只回來了6個。犧牲的另6個戰士,有的連名字都沒留下。我早就不怕死了。”很快,父親就和教育部的20多名同志一起當上了志愿軍,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線。父親被分配到東北軍區司令部工作。抗美援朝期間,又正趕上國內搞“三反五反”運動。這運動后來也波及到部隊。有一次,部隊突擊檢查了團以上干部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問題。結果我父親的情況最好,清正廉潔,沒有任何問題。為此,他還兼任了軍事法庭的陪審員。1953年,我們贏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朝鮮戰場停戰了。父親回到北京,仍在教育部工作多年。1985年離休。2009年逝世,享年90歲。他先后在教育部工作生活達46年之久。
多年來,那條毛毯爸爸媽媽一直用著。直到1961年我考上大學后,爸爸把它傳給了我。爸爸說,這條毛毯是我參加抗日戰爭的紀念,它跟著我在太行山轉戰了8年。后來又用了這么長時間。也是咱家的傳家寶了。現在你上大學了,送給你。又能用,又有紀念意義。
從此,我就一直用著這條毛毯。從1937年至今,這毛毯也有78年的歷史了!它見證了我們艱苦的8年抗戰,也見證了我們國家的天翻地覆的變化。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代表我們全家將此毛毯捐給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作為永久的珍藏。它跟隨我父親王琪壁經歷了抗日戰爭的艱難困苦,也陪著父親迎來了抗戰的偉大勝利!它見證了歷史。2016年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社會各界捐贈文物史料展”,以紀念抗戰勝利71周年。我父親的那條毛毯也在展覽會上展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