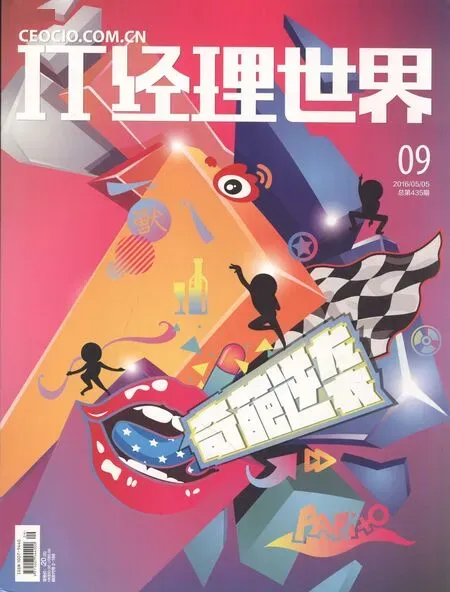“范圍經濟”將取代“規模經濟”?
數字技術正在改變一個傳統公司的邊界,甚至重新定義競爭法則。
托馬斯·史班達?作者現任英國BBC制片人、之華媒體國際主筆;常駐歐洲、中東和中國從事媒體工作逾10年。聯系:info@zhstudio.net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曾以產業多元化為重要特征的西方大型企業日益注重“聚焦經營”——這背后的動因可包括依靠產業深耕縮短學習曲線、取得規模經濟效益、夯實核心競爭力、深入洞察客戶等。久而久之,一個盛行的理念便成為:“多元化意味著危險,因為其復雜性和難以控制的規模會削弱企業取得運營協同效應;企業最好聚焦在某一個行業或若干有關聯的相鄰行業經營業務……”
然而,上述風向或將逆行反轉。美國達特茅斯大學塔克商學院巴卡拉講席戰略學教授Richard A. DAveni最近發表研究著作認為,新的數字技術正在改變一個傳統公司的邊界,使其相比以往更有能力處理復雜性、創造全新的優勢源,甚至重新定義競爭法則。
DAveni教授指出,“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云處理釋放的移動性、機器學習、以及3D打印工具等結合優勢,傳統的大企業集團將迭代出一個‘線條流暢的全新版本,我們稱之為‘泛行業型(pan-industrial)企業。”
何為“泛行業型公司”
泛行業型企業在外表上看來與傳統大企業集團無異,但在運作方式上本質迥然不同。它將由一個軟件平臺作為中樞來驅動,在整個產品線范圍來進行從產品開發到交付的全過程推動。就如同Facebook平臺之于用戶和廣告主之間不間斷的信息自動采集、聚攏和顯現一樣,泛行業型企業針對的則是實體產品和制造商生態群。
DAveni教授用假設的方式來為他愿景中的泛行業型企業進一步畫像。想象一下,他寫道,有一家叫作“通用金屬”(General Metals)的集團,基于在金屬3D打印領域的獨特專長,可以做到集三家“通用”——分別為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和通用動力公司——之大成,因而在從醫療設備到汽車和飛機制造的泛行業領域均具競爭力。歸納而言,“通用金屬”們擁有那些聚焦某一兩個行業領域的大型企業無法企及的優勢,包括——
效率提升:因整合各個業務部門的價值鏈,從而降低、采購、生產、分配和整體風險管理的成本;分攤平臺成本:盡管建立起跨行業管理復雜性的軟件平臺需要昂貴的初始成本,但有極大機會將其分攤至各個部門;生成的信息具有網絡外部性:因其能“看到”跨行業的所有相關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將不僅有助于企業本身預測和優化其經營活動,而且對其合作伙伴也更具吸引力。
此外,一 個泛行業型企業可更大程度上規避“創新者困境”。這是因為,傳統意義上成功的大型企業傾向于關注高利潤客戶,而回避(最初往往)缺乏質量標準的創新活動;而如果同時在多個行業領域經營,無論從財務還是文化驅動上而言,泛行業型企業“受制于”服務特定客戶的境地就較少會發生。
“泛行業型公司”雛形已現
事實上,上述獨特的優勢已經在一部分公司得到體現。DAveni教授在其文中列舉了位于佛羅里達州圣彼得堡的一家名為“扎比爾集成電路公司”的案例。
作為已經擁有近200億美元年收入、并奠定了全球第三大外包制造企業地位的扎比爾公司, 近年升級開發了一套基于云管理的ERP系統,來跟蹤管理各個產品線的材料去向以及下一步環節,在公司內部該系統命名為“控制塔”。
傳統的航母型企業之所以大多將業務按行業區隔來運營,是因為面對成千上萬個疊加的選項(無論是原材料也好、供應商也罷;還要牽涉到數量級別和時機選擇),沒有人能輕易駕馭這樣的復雜性。但“控制塔”可以:它儼然“將所有活動項目放入一個池子中”——因而做到跨多個供應鏈采購、獲得最優惠的價格,并安排生產進度、使工廠保持高水平運行、避免錯失交付期限等。目前,扎比爾公司在其分布于28個國家的102家工廠中相繼推行3D打印工藝,從而最終實現數字化制造的閉環。
如果說扎比爾公司的泛行業平臺打造始于供應鏈和物流實時管理的話,那么,另一家DAveni教授列舉的案例企業——通用電氣(GE)——則從投資興建2.0版的智慧工廠端發力。
GE于2015年在印度浦那投資2億美元新建的工廠可以說“鮮活地演繹了GE向泛行業制造轉型的企圖”。不同于其他隸屬于某個業務領域的GE工廠,浦那的工廠服務多個部門(例如,通過3D打印,浦那為GE的飛機、機車、燃氣輪機等多個產品線提供零部件制造)。而且,由一個名為Predix的中央軟件平臺系統來實時監控設備和流程,每個環節均做到以數字化表征(expressed digitally)、以物聯網測量(measured with IoT)、以分析技術優化(optimized with analytics)。
GE在數字平臺和3D打印領域不惜巨額投入,2016年即斥資13億美元收購了兩家歐洲金屬3D打印公司,分別為Arcam AB和Concept Laser GmbH。
從更高層面來看,向整合型制造方向發展也和GE公司的宏觀戰略相吻合。在全球各地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工廠漸次轉向本地化的大背景下,GE集團通過類似浦那工廠這樣少量的、集約化服務泛行業制造部門的機制亦有助規避非市場化的政治風險。此外,首席執行官杰夫·伊梅爾特早在2015年即對外宣布,GE的愿景是在2020年前成為世界上“十大軟件公司之一”。
現實的預判
可以說,GE公司的古老格言“在你的行業中做到第一或第二”(Being No. 1 or No. 2 in Your Industry)或將成為歷史。因為,當過去分布和相互隔絕于不同業務部門的企業活動如今變成同一項活動時,曾經的行業邊界也就分崩離析。
誠然,并非每一家公司都應轉型成為泛行業型企業。有些行業也可能永遠不會采用 (作為泛行業戰略核心構件的)3D打印技術。但可以預見的是,伴隨成本持續下降和能力上升,一個“由數字化協調生產”的制造體系未來會出現在大多數行業的至少一部分產品領域內。
此外,泛行業型企業的另一個天生“短板”是它可能注定就沒有特定的客戶。所以,與客戶建立起親密關系或成為弱項。相反,他們所能做的,卻是將客戶導向其目標市場、幫助客戶與市場之間構建起緊密的關系。因而,比起傳統上舍棄行業寬度而聚焦深耕的大公司,一個泛行業型企業很可能“即使捕捉到了客戶偏好的重要變化,卻有可能錯失了數字化信息無法做到的更微妙的跟進行動”。DAveni教授提到,這也是為什么泛行業型企業最終必須“基于地理來組織”,這樣才能“在物理維度上更貼近客戶”。
總之,泛行業型企業將會成為“新的規則下巨型而卻敏捷的、并且咄咄逼人的”競爭者,他們將打敗那些依然奉傳統經營智慧為圭臬的對手。
如果說本世紀交替之年代,華爾街更青睞行業聚焦型企業、還經常用“航母型企業的折價率”(conglomerate discount)來給那些魯莽進軍各領域多元化經營的大企業以估值上的“懲戒”的話。如果說當3D制造初露崢嶸時,支持者僅僅預測到其將推動一批具備小批量定制生產能力的“創客型制造商”的話……那么,如今潮水的方向則顯示上述見解的對立面更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