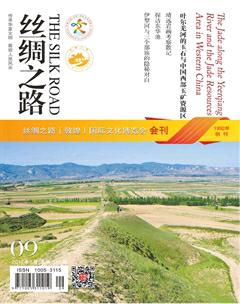喬治·何克:定格在絲綢之路上的多彩生命
趙謙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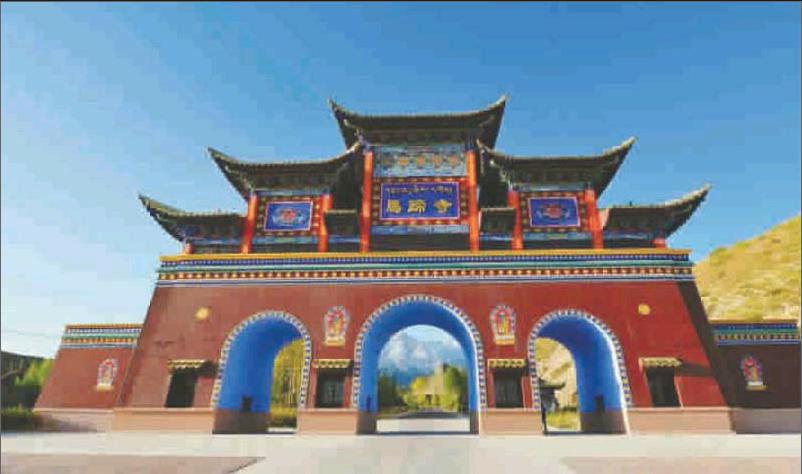
他看到了新中國
何克出生在英國中產階級家庭,1937年畢業于牛津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后,何克隨姑母穆里爾·萊斯特去美國等地進行和平宣傳,之后到達日本。當時罪惡的日本侵華戰爭已經開始,日本軍國主義在國內進行欺騙宣傳,何克在那里嗅到了戰爭的火藥味。1938年1月,何克抵達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已于1937年11月淪陷。在這里,何克目睹了日軍對中國人民的暴行,感到十分震驚。這與他在日本聽到的言論迥然不同。目睹中國人民的這些災難,何克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留下來幫助中國。
他一面擔任美國合眾國際社自由撰稿記者,一面開始學習中文。1938年夏,他來到漢口,見到了當時美國進步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從上海到海口的所見所聞,何克已覺察到真正領導抗日的力量,似乎不在國民政府,而在延安。在史沫特萊的幫助下,何克前往延安陜甘寧邊區采訪。在延安,何克看到了各階層的大批青年從全國各地,從新加坡、馬尼拉、新西蘭和夏威夷等地來這里求取真理。這一切,使他感到驚訝。采訪結束后,他重返漢口,要把看到的一切進行如實報道。這次,史沫特萊將何克介紹給了正在漢口籌劃“工合”運動,但又缺少人手的路易·艾黎。1938年10月25日,漢口淪陷,所有的記者被送往上海。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間,喬治·何克輾轉日本、北京到達了晉察冀邊區。這里的人民團結一致、滿懷豪情投身抗戰的精神讓他肅然起敬。這個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幼稚青年,通過親身的感受開始對共產黨樹立了一種新的敬仰。
晉察冀邊區司令員聶榮臻接見了何克,并熱情支持他到整個根據地采訪。他還受到了八路軍司令員朱德的友好接待和熱情鼓勵。這次采訪,何克得到了深刻的啟示,他對共產黨領導的邊區產生了很深的感情,也和邊區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何克扎根中國,開始從這里奠基。這次采訪,他用激昂的文字寫了《我看到了新中國》,該書于1945年在美國和英國出版。書中記錄了他在中國的抗戰見聞和他看到的充滿希望的新中國,使更多的外國人對新中國有了新的認識和了解。
他率領師生完成了“小長征”
邊區采訪結束后,何克接受了朱德的建議去國統區采訪和工作。1939年春,何克到達陜西寶雞,這是西北“工合”的總部所在地。何克先后擔任“工合”的秘書兼視察員。哪里有“工合”,哪里就有何克的足跡。1940年初,何克被路易·艾黎選中,成為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在創辦培黎學校初期,何克以延安革命精神和八路軍思想作風來管理學校,教育學生,贏得了師生們的一致贊揚。由于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學校迅速發展起來,培養了一批既懂文化,又掌握紡織、機械、化工、會計等專業知識的學生,并發展了機器社、制革社、面粉社、耐火磚社等 23個合作社。到1941年,“工合”已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有效地支援了中國抗日戰爭。
由于戰亂加上“工合”與國民黨之間的關系惡化,同時艾黎又被國民黨定為“親共分子”,學校在雙石鋪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無法再辦下去。經過對時局的分析,路易·艾黎和喬治·何克決定保存實力,繼續辦學,但學校必須搬遷。艾黎積極為尋找新的校址四處奔波。一次偶然的機會,艾黎同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去玉門,途經山丹。艾黎發現,山丹是中國最窮的地方,這里偏僻落后,但這里有年輕人吃苦耐勞的韌性,而且辦學的外界干擾少,符合“工合”、“開發”、“教化”的宗旨。同時,艾黎還得知這里曾是紅軍西路軍和國民黨鏖戰過的地方。于是決定“在這里建一所學校,作為人們對紅軍戰斗的紀念”。1943年12月,艾黎率領先遣組赴山丹進行建校的籌備工作,何克則留在雙石鋪組織搬遷。
要把學校擁有的全部設備搬往千里之外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最棘手的是運輸問題。巨大的困難擺在何克面前,他沒有被嚇倒。他和學校的師生們一起,研究出了各種運輸辦法:用舊的卡車輪胎制作了八輛大皮車,有的機械拆開裝上手推車,有的用騾、馬馱著,還搞到了兩輛舊卡車……總之,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交通工具,把應拿的設備全部裝了起來。
1944年的冬天,這支奇特的運輸隊伍在何克的率領下,從雙石鋪出發了。他們頂著12年未遇到過的嚴寒,踏著冰雪覆蓋的大道,經徽縣、天水、秦安、蘭州,翻越了3600~4800米高的山脈,長途跋涉1100公里,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在1945年3月,輾轉到達山丹。
他組建了三種國籍的家庭
1940年底,中共地下工作者聶長林為了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捕,按照黨組織的決定,去晉東南“工合”事務所工作。他有四個孩子,妻子還患有很嚴重的胃病。但為了革命,他已顧不上這個家了。所幸的是,在洛陽“工合”晉豫區辦事處等待前往晉東南工作的“過河證”時,聶長林結識了一位英國人,他就是喬治·何克。而正是這一次的相遇,改變了聶家四兄弟的一生。何克受聶長林的托付幫助照料留在家鄉的幾個孩子,于是兩個兄長被送入了何克的學校,聶廣沛和老三因年齡太小暫時和媽媽生活在一起。由于孩子的母親病重,無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兒院,何克和艾黎不僅親自把她送往醫院進行救治,還把孩子們從孤兒院帶回家。何克給孩子們洗澡,買了新衣服給孩子們換上。不久,孩子的母親病逝,艾黎帶著孩子回到雙石鋪,長期和何克住在一起,那時聶家四兄弟的年齡是3~12歲。就這樣,三種不同國籍的人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里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大家庭。
1944年12月,何克帶著四個養子以及雙石鋪培黎學校的所有學生千里輾轉至甘肅山丹。在這期間,有人要求收養四哥聶廣沛,但被何克拒絕。1945年7月22日,何克不幸犧牲。路易·艾黎接受何克的臨終矚托,繼續撫養著四個孩子,一直到解放后找到他們失散多年的父親為止。
在兩位異國養父的熏陶下,四個孩子日后各自在電氣工程、工業選礦、外貿等領域都有所建樹,成了新中國經濟建設棟梁之才。解放后,老大聶廣淳寫了一本回憶錄《我們四兄弟的兩位異國父親》,記錄了那刻骨銘心、博大的父愛。
一處長眠異域赤子的仿西式陵園
在河西走廊的山丹縣城南湖有一座仿西式陵園,是為紀念新西蘭著名社會活動家路易·艾黎先生和英國著名記者喬治·何克先生而修建的。前身為1945年修建的何克陵園,1979年進行了重建,1985年又進行了修繕擴建。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去世后,根據他的遺愿,將他的骨灰撒在了四壩灘,部分骨灰與他的好友喬治·何克安葬在一起,1988年4月,路易·艾黎骨灰安放園內,陵園正式更名為“艾黎與何克陵園”。園內主建筑為路易·艾黎與喬治·何克墓,墓后矗立著象征友誼的紀念碑。陵園北側為紀念喬治·何克的吊唁紀念廳,南側為喬治·何克紀念亭,上面懸掛著由甘肅知名書畫家裴建準題寫的“陶容萬有”匾額,亭前設有路易·艾黎與培黎校友當年為喬治·何克所立的紀念碑,碑文為英國詩人的題詩:
色彩絢麗的生命啊,光輝溫暖,為了他,人們一直奮發向前,他已逝去了,從此不再奮戰,在戰斗中逝者的生命卻更光輝燦爛。
1988年4月,鄧小平為艾黎與何克陵園題寫“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垂不朽”,題詞鐫刻在了陵園的照壁上。如今,在蒼松翠柏的映襯下,靜謐的陵園顯得更加莊嚴肅穆。
一座為他而建的培黎圖書館
在山丹的艾黎捐贈文物陳列館正北有一座由原文化部副部長周而復題名的圖書館,它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倡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熱情支持、甘肅省人民政府撥專款興建。
1982年,85歲高齡的路易·艾黎專程來山丹參加為他捐贈的文物而興建的“艾黎捐贈文物陳列館”竣工開館儀式。返京途中,他在蘭州稍事停留,與一部分參加慶祝活動的朋友聚會。由于這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聚會,大家非常激動和興奮。興奮之余又十分懷念早逝的喬治·何克校長。大家向路易·艾黎建議,為了紀念已故何克先生逝世40周年,希望在山丹興建一座圖書館。
路易·艾黎對老校友的建議十分感興趣,認為這是一件有關繼承“培校”傳統、振興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大事,表示完全支持。1982年9月底,他便將上述建議向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正式陳述。1982年12月2日,在慶祝路易·艾黎85歲壽辰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在《人民日報》上以《革命的好戰士、建設的好參謀》為題,概述了路易·艾黎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的業績,同時宣布為豐富山丹人民的文化生活,紀念已故前山丹培校英籍校長喬治·何克先生,將根據艾黎的倡導,在山丹興建一座圖書館。
為了擴大影響,讓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山丹,路易·艾黎不斷地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寫信,告訴他們在他的第二故鄉將興建一座圖書館。在英國的喬治·何克親屬收到艾黎的信后,通過在北京執教的班以安先生,兩次捐贈人民幣近2000元,曾在山丹工作過的新西蘭朋友艾啟赫,美國朋友瓦爾特·易斯利、巴克等人,在華工作過幾十年的耿淑麗、愛潑斯坦及夫人邱茉莉等,都慷慨解囊為圖書館捐款。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這座建筑面積1010平方米,內含可藏書20萬冊的書庫及采編室,報刊、期刊、兒童閱覽室,資料室和辦公室等設施,具有綜合性規模的圖書館,于1984年7月建成。現在這里已經成為全山丹縣人民閱讀、培訓和共享文化資源的重要設施。
一部以他為主角的史詩巨片
2008年4月1日,由中國發起,聯合德國、澳大利亞共同制作的好萊塢英雄主義國際巨片《黃石的孩子》舉行全球首映式,4月3日起,影片在全球公映。影片是根據路易·艾黎的《從牛津到山丹——喬治·何克的故事》改編的。這是路易·艾黎在喬治·何克去世后為何克的母親所寫的書,記述何克豐富而有意義的經歷,是對喬治·何克短暫而多彩的一生的介紹。
《黃石的孩子》這部影片并未把矛頭對準殘酷的中日交鋒,而是用了大量篇幅講述發生在戰場大后方的故事。影片開始不久便將日軍控制下廢墟中的南京城呈現在我們面前,充滿戰爭的味道,但經過一段戰爭的殺戮場面后,全片重心就放到了主人公英國記者喬治·何克身上,講述何克怎樣在物質條件艱難的大后方照顧60多個中國孤兒,為他們建立了一個溫馨的家園,后又帶著孩子們躲避戰火遷徙到甘肅山丹的艱辛過程。這次征程,他們穿越了歷史久遠的絲綢之路,穿過了崎嶇不平甚至不能通行的山脈,來到了廣闊的戈壁沙漠邊緣,在歷經磨難后他們成功抵達山丹。最后喬治卻因受了一點小傷導致破傷風,最終死去。但是他留給孩子們的是創造新生活的愿望、信心和勇氣。
“從1937年到1945年8月抗戰結束前的八年不到一個月的這段時間,對于喬治·何克來說是度過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國革命的鮮血和激情澆灌的一棵幼小樹苗,長成了堅實的大樹。”路易·艾黎在《從牛津到山丹》的序言中說。
中國有句古話:“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
現在,何克當年創辦的培黎學校經過搬遷和重建之后已經成為國家級的重點中專。并且,每年的暑假還會從何克的母校——英國哈彭登市圣喬治中學選送學生來培黎學校和當地的師生進行教育和文化交流。圣喬治中學也肩負著中英兩國文化交流的使命,在學校里開展豐富多彩的“中國日”活動,傳承寶貴的友誼。
英年早逝的喬治·何克將他多彩的生命定格在絲綢之路上,他留下了激勵我們的精神,也架起了一座跨越萬里的友誼之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