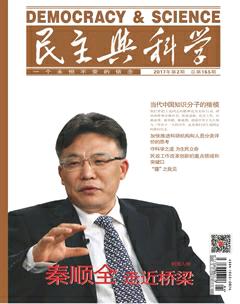從派區到背崩
周浙昆


第一次聽說墨脫這個名字是從電視上。上世紀80年代初,新聞聯播播過一條新聞:有一位來自西藏墨脫的全國人大代表,為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步行了15天才到達有公路的地方。當時我就想,我們國家還有這么偏僻的地方?于是翻開地圖看了看,發現墨脫位于西藏東南部,喜馬拉雅山脈的東段末端。由于位于雅魯藏布江大峽灣腹地,地質活動強烈,又是印度洋的暖濕氣團進入大峽灣青藏高原的東大門,降雨充沛,山地陡峭,塌方、泥石流和地震頻頻發生。冬季喜馬拉雅山被大雪覆蓋,墨脫通向外界的山路完全被大雪覆蓋達6~8月之久,因此,墨脫又有陸地孤島之稱。在2013年10月以前,墨脫是我國唯一一個不通公路的縣。全國兩會每年3月初在北京舉行,這個時候要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墨脫縣的全國人大代表這個時候要去北京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就必須要沿著雅魯藏布江大峽谷走上15天,避開大雪封山的喜馬拉雅山,然后翻山到達有公路的地方。就是雪化山開以后,進入墨脫的道路也是突兀崎嶇,險象環生,早年英國探險家F.K.Ward幾次嘗試而終究未能如愿。上世紀80年代國家組織的青藏高原科學考察,雖有幾支考察隊進入過墨脫,但都是在夏季,這幾支進入墨脫的考察隊都是趁著喜馬拉雅山冰雪消融的時候進入墨脫,又趕在大雪封山前離開。冬春季的采集對于植物區系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缺乏冬春季的標本,墨脫植物區系只能永遠披著神秘的面紗。
1990年,吳征鎰院士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種子植物區系》,獲得經費300多萬元。在上世紀90年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是基金委資助強度最大的項目了。這個項目立項之初,就把西藏阿里、墨脫、云南獨龍江等地列為中國植物區系的關鍵薄弱地區。項目立項以后,李恒教授完成了獨龍江的越冬考察,孫航、德銖等人完成西藏阿里的考察。而墨脫的越冬考察,到了1992年仍未開展。任務幾經易手,最終落到了孫航頭上。那時孫航正在讀吳先生的在職博士研究生,先生把孫航的博士論文題目定為《西藏墨脫植物區系的研究》。原來確定的幾位考察隊員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前往,孫航邀我參加,憑著幾分探索的沖動,我答應了孫航的邀請。考察隊中還有一名隊員是在標本館工作的俞宏淵。
1992年9月中旬我們開始了行程。先從昆明乘飛機到拉薩,之后又從拉薩租用一輛卡車拉著我們的行裝到八一鎮。幾經輾轉,10月初到達米林縣的派區(現在叫派鎮)。派區是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的入口處,也是那時進入墨脫的必經之地。10月肆虐了墨脫一個夏季的印度洋季風有點累了,正打算歇歇,頻度和強度都大大降低,晴天也多了起來,是進入墨脫的最好季節。此時的派區一片繁忙,墨脫一年所需的物資,必須要趕在11月份大雪封山前,靠人背馬馱運抵墨脫。我們的考察用具、文獻資料和生活所需裝在十幾個特制的鐵皮箱子中。到達派區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張羅著尋找民工,將這十幾個鐵皮箱子背進墨脫。那時派區雖然熙熙攘攘,但是大家都忙著背自己的東西,閑暇的民工十分難找,要一次找齊幾十個民工就更是困難。折騰了幾天后終于找齊了民工。民工的價格是按所背物品的重量論斤計價,約定好三日后在墨脫的背崩村交貨。
派區的海拔有2800米,從這里進入墨脫首先要翻越多雄拉山。多雄拉是喜馬拉雅群山中最矮的一座了,埡口的海拔是4200米。我們一大早起來乘上解放軍的山地車,這種車輪子十分巨大,此前我從未見過。山地車將我們送到海拔3600米的松林口,這是公路能通達的最高處了,我們從這里開始翻山。松林口處的植被是針葉林,主要樹種是冷杉和落葉松。隨著海拔的升高,冷杉和云杉逐步替代了高山松和鐵杉,樹林開始稀疏,我們來到樹線以上,群山逐漸清晰起來,待接近了4200米的多雄拉山埡口,突然間一陣濃霧從山頂襲來,十步之內不辨人馬,我們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登。當云霧散去的時候,映入眼簾的竟然是一架折翼的直升飛機和斃倒路邊的死馬,剎那間一種神秘和恐怖的氛圍在人群中彌漫開來。
這是一條神秘之路,一路上,同行的路人給我講著這條路上的故事。比如,某年某日,一解放軍女戰士獨自一人,從墨脫翻山回派區,在多雄拉山突遇大霧,不幸迷路,天色已晚仍不辨路徑,后僥幸遇到同樣迷路的路人,兩人在多雄拉山上抱團取暖,度過了寒冷的夜晚得以幸存。一開始聽到這個故事,我認為這是路人們為了消遣漫漫長路而杜撰出來的,看到折翼的直升飛機和斃倒路邊的死馬,不由自主地開始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由于這條道路的艱辛,解放軍想到用直升飛機給部隊做補給。據說為了改善部隊的生活,在直升飛機航線開通的時候還空運過一頭母豬到墨脫,還有家屬乘坐直升飛機,到部隊看望自己的丈夫。后來直升飛機在多雄拉山墜毀,這條航線也就取消了。在墨脫的部隊家屬,由于沒有能力走出墨脫,也就干脆就在部隊呆了下來。
過了埡口一路下坡,森林又出現了,這時天色已晚,我們來到了一個叫拿格的地方,這是第一天的宿營地。說是宿營地,其實就是幾個不知是誰搭在森林中的窩棚,我們吃了一點干糧在窩棚中合衣躺下,度過了進入墨脫的第一個夜晚。
第二天還是一路下坡,沿途的植被有了較大的變化,常綠闊葉林出現了,天氣也漸漸地熱起來,從多雄拉山往背崩走,植被垂直分布明顯,你可以看到我國從東北到海南的植被類型。從背崩到多雄拉山的這個大峽谷就是一條鑲嵌在喜馬拉雅山中的溝壑,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體沿雅魯藏布江、順著峽谷向上,大部分的暖濕氣團被多雄拉山阻斷,充沛的雨水滋潤了峽谷兩邊的植被。少數強大的暖濕氣團,能夠翻越多雄拉山而進入青藏高原。直升飛機從寒冷的青藏高原,進入峽谷,如果遇到強大的暖濕氣團,就像一個人突然進入熱氣騰騰的洗澡堂子,濃霧迷漫,加之峽谷狹窄,稍不留神飛機就會出事。后來得知多雄拉山摔過兩架直升機,一架在1988年,一架在1989年。邱光華1988年所駕駛的直升機曾在多雄拉山出過事,所幸大難不死,不想邱光華烈士卻在汶川抗震救災中犧牲了。
我們邊走邊采集標本,海拔下降到了2200米處,一片規模較大的木頭房子出現在了密林中,這就是汗密兵站。從派區到背崩有約90公里的路程,一般人需要走三天,體力較好的,兩天也可以走完。汗密這個兵站就是為了方便過往的解放軍戰士而修建。同行的人群中除了民工以外,還有不少解放軍戰士,他們也趁著這個時節,將一年的給養運到墨脫。戰士們在汗密休整,我們三人就老臉皮厚地去兵站混吃混喝。此時的兵站人聲鼎沸,熱鬧非凡,大雪封山以后,兵站僅留兩個戰士看守。年輕留守的戰士以大山的密林和野獸為伴,實在是難為他們了。不知是哪個留守的戰士在兵站的門上留下了一副對聯:“清燉螞蟥遍地是材料,涼拌冰雪以大山為伴”,橫批:“天天如此”。這是冬季兵站的真實寫照。
過了汗密兵站,很快就到了傳說中的老虎嘴。據說這是從背崩到墨脫道路中最為艱險的一段,山地在這里變成的峭壁,老虎嘴就是鑲嵌在峭壁上的一條小道。當我們做好各種思想準備進入老虎嘴的時候,老虎嘴的狀況超出了想象,如果沒有恐高癥,通過老虎嘴就毫無挑戰。我頗有幾分失望地問同行的路人;“這就是老虎嘴?”同行的當地老鄉告訴我,這確實是老虎嘴,我們現在走的路是解放軍在峭壁上修出來的。原來的老虎嘴是要在陡峭上攀行,稍不留神就會跌入谷底,故有此稱。由于這是一條進出墨脫的必經之路,解放軍在峭壁上炸出了一條山間小道,老虎的牙齒被拔掉了。
過了老虎嘴依次到了一號橋、二號橋,漸漸地我們來到了雅魯藏布江的北岸,這意味著背崩村就要到了。三天來一路上缺吃少眠,我們的體力早已消耗殆盡,咆哮的江水聲仿佛是給我們打了一劑強心針,讓我們鼓起余勇,繼續向前,終于來到解放大橋旁。這是墨脫境內跨越雅魯藏布江最大的橋,過了解放大橋就是背崩村了。解放大橋海拔800米左右,而背崩村卻在海拔1200米處的半坡上。也就是說我們還有400米的高程要爬,我們三人坐在橋邊,休息了好一陣,卯足了勁做最后的沖刺。我們相約一鼓作氣直抵目的地,登上背崩村。可是走了不到15分鐘,不知是誰說了一句休息一下吧,強弓末弩的我們稀里嘩啦又坐到地上。就這樣我們跌跌撞撞地進入了背崩村,開始了為期10個月的越冬考察。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生物地理與生態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