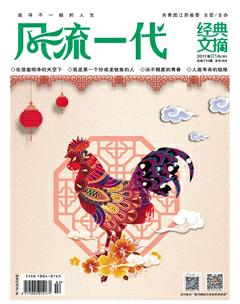“世界一流”的焦慮
陳平原
當今中國,各行各業,最時尚的詞,莫過于“世界一流”,可見國人的視野和胸襟確實大有長進。提及“中國大學”,不能繞開兩個數字,一是211,二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紀,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國大學,這自然是大好事;可中國畢竟財力有限,這目標也太宏大了點。于是,政府做了調整,轉而重點支持北大、清華等"985工程”大學。何謂“985”?就是1998年5月,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在北大百年校慶時講話,提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此前我們的口號是“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很多學者提意見,說加了這么個意識形態的限制,扭曲了奮斗目標。社會主義國家本來就不多,可比性不強。再說,整天追問姓“社”還是姓“資”,怎么可能辦好大學。終于,刪去了“社會主義”四個字,中國大學明確了發展方向。此后,我們開始以歐美的一流大學為追趕目標。
其實,從晚清開始,中國人辦現代大學,就是從模仿起步的。一開始學的是日本和德國,上世紀20年代轉而學美國,上世紀50年代學蘇聯,上世紀80年代以后,又回過頭來學美國。現在,談大學制度及大學理念的,幾乎言必稱哈佛、耶魯,連牛津、劍橋都懶得提了,更不要說別的名校。儼然,大學辦得好不好,就看與哈佛、耶魯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來,這已經成為一種新的“迷思”。過去,強調東西方大學性質不同,拒絕比較,必定趨于故步自封;現在,反過來,一切唯哈佛、耶魯馬首是瞻,忽略養育你的這一方水土,這同樣有問題。我常說,中國大學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各國大學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國大學的現狀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腳下的歷史舞臺,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而不是忙著制訂進入“世界一流”的時間表。
再說,大學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見的數字(科研經費、獲獎數目、名家大師、校園面積、師生比例等)外,還得看其對本國社會進程的影響及貢獻。北大百年校慶時,我說了好多話,有的被嚴厲批判,有的則得到廣泛贊許,下面這一句,因符合學校利益,被不斷“傳抄”——“就教學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論北大對于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樣的機遇,其實是千載難求的。”我這么說,并非否認中國大學——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在教學、科研、管理方面有很多缺陷;只是不喜歡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說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標來辦學。
大學是容納探索和思想開放的地方,它鼓勵人們不是功利性地而是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種氣氛使哲學懷疑不至被道德風尚和占上風的勢力嚇倒,它保存偉大的行為、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思想,以使對潮流的挑戰和質疑能夠得到滋養。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評如今熱鬧非凡的“大學排名”,認定其對于中國大學的發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數字,而數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為讀書人都講“仁義禮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約束力。即便是老實人,拒絕弄虛作假,可你潛意識里,著力于生產“有效的”數字,必定扭曲辦學方向。“大學排行榜”的權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鏈條,環環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來,此舉將泯滅上下求索、特立獨行的可能性。好大學必須有個性,而你那些“與眾不同”的部分,恰好無法納入評價體系。“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學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學將日益趨同。差的大學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學將因此而下降。這就好像辯論比賽,裁判稱,按照規則,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其余的平均。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見,也可能是創見。當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無效”,不計入總成績,自然而然地,你就會轉向,變得日漸隨和起來。當然,你也可以固執己見,可那就成為“烈士”了。
所謂爭創“世界一流”,這么一種內在兼外在的壓力,正使得中國大學普遍變得躁動不安、焦慮異常。好處是舉國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變;缺點則是不夠自信,難得有發自內心的保守與堅持。其實,所有理想型的論述,在實際操作中,都必須打折扣。所謂“非此即彼”或“不全寧無”,只適合于紙上談兵。今天中國,不僅僅是“開放”與“保守”之爭,在“接軌”與“閉關”之外,應該還有第三、第四條路可供選擇。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并非“自古華山一條路”,而很可能是“條條大路通羅馬”。對此,我們必須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連標榜“獨立”與“創新”的大學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家坤摘自新京報書評周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