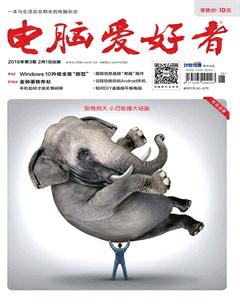忘記數碼相機 華碩ZenFone Zoom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之所以無法完全取代數碼相機,就是因為后者擁有光學變焦這一殺手锏功能。而華碩ZenFone Zoom,就是一款將數碼相機殺手锏功能為己用的專業拍照手機。
光學變焦需要精密復雜的物理結構,勢必導致手機厚度的超標。而華碩ZenFone Zoom卻放棄了傳統的伸縮式變焦鏡頭,而是改用了兩次反射的潛望式鏡頭模塊,將10枚高透光的精密HOYA鏡片硬是塞進了僅有11.95mm厚的機身內(最薄處僅5mm)。此外,該產品還采用了一體成型的航天級6063鋁合金框架,后蓋也附上了源于意大利制皮技術的真皮表層,在把握手感上堪稱一流。為了在后蓋容納碩大的圓形鏡頭模組,ZenFone Zoom放棄了ZenFone家族長期以來堅持的音量鍵后置、電源鍵頂置的結構,而是將它們都集中在機身右側,在使用上更加順手。
作為專業的拍照手機,華碩為ZenFone Zoom準備了單獨的兩段式拍照快門和錄像快捷鍵,在熄屏狀態下就可一鍵進入拍照/錄像界面,在體驗上無限接近數碼相機。此外,該產品還引入了鐳射自動對焦和PixelMaster影像處理技術,前者可將對焦速度縮短至0.03秒,而后者則帶來了多達18種的豐富拍照模式,哪怕是菜鳥也能通過不同的模式拍出意境獨到的好照片。
在硬件方面,ZenFone Zoom選用了英特爾凌動處理器平臺,Atom Z3580擁有2.3GHz主頻和強悍PowerVR 6430 GPU的優勢,就性能而言處于Android手機陣營的中高端水準。而4GB內存、標配64GB存儲空間以及支持9V/2A的快充技術,也讓ZenFone Zoom有了更多殺入高端手機戰場的底氣。可惜,ZenFone Zoom沒能引入時下流行的指紋識別技術,并因獨特攝像頭的空間占用而放棄了雙卡雙待能力。
編輯點評
華碩ZenFone Zoom是一款專門為拍照而生的手機,可實現3倍光學變焦,并具備高度實用的4級OIS光學防抖功能。如果你是一個攝影愛好者,喜歡輕裝簡行的旅行,一款ZenFone Zoom就可兼顧手機和數碼相機的任務,何樂而不為呢?

?真皮工藝的后蓋手感出眾

?獨立的拍照和攝像快捷鍵

?支持128GB存儲卡擴充

?真皮掛繩用起來更像DC
網絡:移動聯通雙4G(單卡) 屏幕:5.5英寸IPS(1920×1080像素) 處理器:英特爾Atom Z3580
內存/存儲:4GB/64GB(支持128GB存儲卡) 攝像頭:500萬/1300萬像素 電池/重量:3000mAh/185g
3DMark:(Unlimited):20340 安兔兔V5.73:48042 安兔兔V6.0:61368 魯大師V7.3:34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