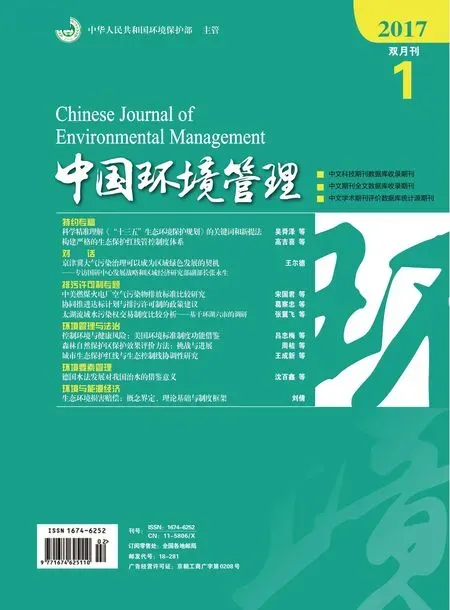太湖流域水污染權交易制度比較分析
——基于環湖六市的調研
張翼飛*,劉珺曄,張蕾,覃瓊霞
(1.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上海 201620;2.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全球氣候變化與綠色經貿研究中心,上海 201620;3. 浙江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杭州 310018;4. 浙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杭州 310018)
太湖流域水污染權交易制度比較分析
——基于環湖六市的調研
張翼飛1,2,3*,劉珺曄1,2,張蕾3,4,覃瓊霞3,4
(1.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上海 201620;2.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全球氣候變化與綠色經貿研究中心,上海 201620;3. 浙江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杭州 310018;4. 浙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杭州 310018)
太湖流域作為全國經濟發達的地區之一,水環境污染成為制約太湖流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作為水污染權交易制度實施最早的流域,該制度在太湖流域理論與實踐層面探索經驗的總結對排污許可制度的應用和排污權交易的推廣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緊迫的現實意義。本文通過對嘉興、湖州、蘇州、無錫、常州及上海地方經驗的調研,從制度設計、產權界定、信息披露、制度效率等方面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市場主導型的水污染權交易模式可以顯著提高政策績效,而交易市場的規模是交易制度推廣實施的關鍵,最后,提出建立太湖流域統一水污染權交易市場等的政策建議。
污染權交易;太湖流域;統一交易市場;市場規模
引言
太湖流域a位于我國長三角地區,是全國經濟最發達、河網最密布的流域之一,其中太湖流域總人口5971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4%;2014人均GDP為9.7萬元,大約為全國人均GDP的2.3倍[1]。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太湖流域的生態環境被不斷破壞,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容量,表現為太湖流域整體水環境惡化。根據國家地面水環境質量的標準,1960年時期太湖屬于Ⅰ至Ⅱ類水質,而后到了1970年代變為Ⅱ類水,進入八十年代后期,太湖流域已經發展至Ⅲ類水,有些湖體甚至達到Ⅳ類水和Ⅴ類水,到了九十年代,太湖流域近三分之一的湖體為Ⅴ類水,平均水質為Ⅳ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太湖流域的水環境狀況仍然普遍超標。富營養化導致藍藻事件頻發,嚴重影響太湖流域水環境安全并制約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08年5月,國家發改委頒布《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總體方案》,至此治理太湖水環境問題被正式提上議程,其中水污染權交易成為治理太湖流域的重要經濟手段。太湖流域作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卻面臨嚴峻的環境資源危機,同時作為水污染權交易最早的流域,具有典型的借鑒意義。
本文通過對環太湖流域(上海、嘉興、湖州、蘇州、無錫、常州)六市水污染權交易政策實施進行調研,從案例分析的視角梳理與總結環湖六市的實踐經驗。然后,從制度經濟學視角對六座城市進行橫向維度的比較分析,分析了制度設計、產權界定交易、信息披露、制度效率等方面的差異,并對差異的原因進行探索。最后提出建立全流域水污染權交易統一市場的政策建議。
1 水污染權交易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Coase(1960)根據產權理論通過市場來配置排污權是解決環境污染的有效機制[2]。隨后Dales(1968)首次提出了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概念,認為環境的外部性可以通過排污權交易來改善[3]。Montgomery(1972)論證了實現排污權交易機制能夠有效控制減排成本,顯著優于傳統分配機制[4]。目前國內的研究主要有水污染權有償使用的必要性、交易制度對企業行為影響和政府分配指標的績效研究。
1.1 水污染權有償使用的必要性研究
沈滿洪(2010)在生態經濟化的實證分析中,以浙江省嘉興市的排污權交易為例提出了生態經濟化假說,并求證了排污權有償使用這一生態經濟化制度安排的均衡條件[5]。劉文琨(2011)對水污染物總量控制在國內外發展歷程進行梳理,提出由于水污染權交易具有費用有效性、管理成低、有利于達標、能夠緩和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矛盾等優點[6]。畢軍等(2007)通過初試分配定價模型揭示現行的排污費制度并沒有完全反映真正的環境價值,有償使用下的排污權價格應為排污收費的4~6 倍[7]。王金南(2014)梳理和分析了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的實踐探索并指出,排污權首先通過有償方式取得,隨后在交易市場上進行再分配,最終形成排污權有償分配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能夠提高地區減排效率[8]。Marchiori (2012)針對不同主體主導下的水污染權交易進行比較分析,得出有償使用水污染權能夠提高社會總體福利[9]。
1.2 水污染權交易制度對于企業行為的影響研究
喬小南(2012)通過遞歸模擬說明排污指標不同分配對于經濟績效的影響,證明了當排污指標傾向于技術進步的企業能夠提高企業利潤但會加深地區間的經濟差距,若向技術劣勢企業分配,會導致企業利潤降低,但能夠提高消費者福利水平[10]。周樹勛(2012)對排污權交易的浙江模式,杭州、嘉興、紹興等地梳理,指出自實行排污權交易制度以來2010年全省水環境功能區達標率較2005年高0.5%[11]。柳萍(2012)根據浙江省排污權交易經驗,揭示了排污權交易制度對于促進環境保護和節能起到重要作用,同時對美國排污權信用制度進行總結對比,得出市場主導及規范透明的交易體系是浙江省排污權交易主要實現目標[12]。Fare 等(2013)采用DEA模型,對排污權交易的方式進行擴展,得出生產者之間進行排污權交易提高企業減排效率,存在潛在經濟紅利[13]。
1.3 指標分配對交易績效的影響研究
劉年磊(2014)根據水污染總量控制目標分配的研究得出,地區間的合理總量分配機制可以提高減排效率,對于實現不同地區間協同控制以及水環境質量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4]。吳瓊(2014)根據2004年至2014年近十年的排污權交易政策梳理發現,雖然排污權交易的二級市場因為技術、法律等因素沒有完全形成,但卻實現了倒逼效應,促進地區環境監管能力[15]。王潔方(2014)根據總量控制下流域內不同的初始分配方式得出逐步提高競爭性的排污權分配比例,從而實現排污權交易市場有效性[16]。
排污權交易政策是通過市場機制來改變企業經營決策和排污行為,實現改善環境的經濟激勵手段。但由于各地區管理體系、地方市場化進程的差異,導致排污權交易制度在各地區應用呈現顯著差異,進而影響到實施績效的不同。同時,已有文獻揭示的對于浙江地區應用的成功經驗,為何沒有在相鄰的江蘇省和上海市推廣?政策實施績效的決定因素是什么?如何推進水污染權交易制度在流域乃至全國實施的環境改善效果?上述問題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本文將基于環湖六市的地方實踐經驗的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究。
2 太湖流域水污染權交易制度演變分析
水污染權交易是基于地區水環境可容納污染物總量的基礎上,將富裕的水污染排放量作為環境商品,以貨幣為計量方法將排污量進行調劑,同時激勵企業通過技術進步的方式改善污染狀況,從經濟和環境的角度提高環境污染治理效率,減少治理成本。面對水環境容量的短缺,水污染權交易制度逐漸在太湖流域范圍內展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2.1 第一階段——上海閔行、嘉興秀洲區級層面試點
1985年,上海市人大在黃浦江上游實行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1987年在閔行發生了中國第一例水污染權交易。2002年4月嘉興市出臺有關秀洲區水污染排放總量控制和排污權有償使用管理法案。同年10月,在“全區首批廢水排污權有償使用啟動儀式”上秀洲區11家企業參與了排污權有償使用。
2.2 第二階段——嘉興市排污權市場市級層面試點
2007年9月,嘉興市頒布《主要污染物排污權交易辦法(試行)》方案,2007 年11 月,嘉興市成立了國內首個排污權交易中心,各縣(市)設立分中心,并頒布《關于進一步規范排污權交易工作的通知》。在水污染物排污權交易上,嘉興市成為全國第一個全面推行排污權有償使用制度的地級市、也是第一個成立了排污權有償使用的專門機構——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
2.3 第三階段——太湖流域全面實施排污權交易
2008年5月國家發改委批復并公布《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總體方案》,方案指出要施行水資源有償使用,并將化學需氧量(COD)、氨氮(NH)、總磷(TP)和總氮(TN)確定為太湖流域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2008 年11月20日江蘇省太湖流域化學需氧量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開始試點。2009年3月,浙江省正式啟動國家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至此,各地便全面開展污染權交易制度(見表1)。

表1 環湖六市排污權交易制度出臺時間

續表
3 太湖流域水污染權交易制度的實踐經驗分析
3.1 交易制度最先在上海實施,環境改善顯著
1987年上海市閔行區通過無償使用的方式完成了全國第一例水污染權交易(上鋼十廠與塘灣電鍍廠),至2002年,上海市閔行區污染權交易共計40多例,涉及到的企業由80多家。截至2004年,閔行區的工業廢水處理率、廢水排放達標率已達100%,城區河流水質達標率也均達100%。
上海作為實施排污權交易最早的城市,由于無償出讓的初始分配方式和相關管理制度的滯后,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后又因污水“排海”工程的實施,到2005年后水污染物排污權交易在上海逐漸減少,到2013年底,閔行區擁有排污權許可證的企業只有4家,其中擁有廢水排污權的僅為2家。
然而,排海工程的實施雖然控制了上海地區內的污染物排放,但是卻將污染負荷轉移到了海洋,對海洋環境造成較大影響。自2009 年以來東海的二類水質海域面積銳減,2012 年僅為2009 年1/2,遠超過全國的變化率。在三類水水質海域中,2012 年比2011 降低0.3 萬平方公里。但四類和超四類的海域面積急劇增長,增速高于全國變化率[17]。尤其是超四類海域面積,2012年是2009年的2.1倍。盡管東海污染加劇的因素很多,但上海“排海”工程造成了收納水體的污染負荷增加。
由此可見,作為試點最早的地區,排污權交易的減排績效可見。但因排海工程,導致可交易的排污權規模減少,使得交易市場萎縮并逐漸消失。
3.2 政府主導交易體系較規范,企業激勵不足
3.2.1 蘇錫常地區協議交易
蘇錫常地區排污權交易模式基本是以政府指導下的協議交易。2008年1月江蘇省物價局和省財政廳聯合出臺了太湖流域排放指標有償使用收費標準,規定直接向環境排放水污染物的6個主要行業COD排放有償使用收費標準為4500元/年/噸,污水處理廠COD排放有償使用收費標準為2600元/年/噸a數據來源:2012年江蘇省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報告。至2014年,蘇錫常地區已相繼出臺地方法規近10例,包含從“有償使用”的通告以及“進一步定價”b筆者根據蘇州、無錫、常州三市環保局政策公開欄目統計所得。。
2011年5月,無錫市環保局出臺《無錫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實施細則》的通知。2014年蘇州市按照江蘇省太湖辦要求,全力推進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為了進一步強化環保倒逼機制,到2014年年底,排污權交易中心已進行了近10宗交易,其中處理的2宗交易中二氧化氮交易金額為每噸4480元。截至2014年年底,常州市110家重點排污企業開展了水污染物排污權有償使用,成立了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的工作機構,除已有的“常州市環保科技開發推廣中心”,掛牌“常州市排污權服務中心”;同時,環境保護局會同常州市財政局、物價局等部門共同討論起草了《常州市排污權有償使用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及實施細則》,推進交易的實施。
值得注意的是,蘇州市實施的排污權交易對象主要是二氧化氮和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在水資源有償使用方面,蘇州市曾投入建設和推行過水污染權交易,但未有交易案例。蘇州市有償使用交易雖能在環境能源交易中心平臺上看到企業的減排指標等,但該平臺并未開發競價交易的功能,全市已達成的交易基本是協議交易。交易雙方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并在2010年后無實質性交易。之后由于經濟形勢等原因,自2011年后水資源有償使用、排污權交易被暫停。
因此,盡管排污權交易在江蘇省穩步開展,但政府主導下的交易模式使得交易成本高,排污權交易價格偏離市場價格,無法正確反映環境容量的稀缺性。擁有富裕排污量的企業往往存在惜售心理,導致交易規模不足,再加上經濟形式等外部因素,排污權交易的政策績效亟待提高。
3.2.2 無錫江陰地區示范效應初現
無錫市的江陰地區是江蘇省排污權交易的示范區。2009 年初,無錫市江陰地區在政府指導下開展了排污權有償使用的試點工作,其運行模式主要是以政府為中介引導企業相互之間進行污染指標的調節。與此同時,環保部等籌備搭建排污權的交易儲備中心及交易平臺。截至2014年底,江陰地區共核定排污權有償使用單位730家,征收排污指標有償使用費用累計7700多萬,共363家新、改、擴建項目的企業參與交易,污染物有償使用的累計交易額6081.2萬元[18]。江陰市排污權交易的主要特征是在總量控制的基礎上對于地區內所有排污企業固定價格征收,針對業績不景氣的行業進行關停并轉,將富裕的排污權進行余量調劑,在江蘇省境內開創了污染物排污權交易的示范效應。
江陰市采用所有排污企業統一收費,同時,只要直接或者間接向大氣或者水中排放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都必須進入排污權有償使用的環境政策管理體系中。雖然統一收費對象能夠使得核定對象明確,但整個無錫市由于支柱產業多為老企業,征收難度較大,僅經濟較為發達的江陰城區采用此方式。
由此可見,盡管江蘇省開展排污權交易較早,政府已營造了良好的排污權交易基礎,但除了無錫市的江陰地區,其他城市進程緩慢。2009年11月常州市成立排污權交易中心至今尚未發生排污權交易;2012年12月成立的蘇州環境能源交易中心直至2014年10月才真正運作第一起排污權交易,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主導的模式盡管在初期有助于制度的建設和管理的規范,但對企業激勵不足,同時固定的回購價格影響價格機制的發揮。
3.3 市場主導交易激勵企業革新
3.3.1 嘉興海寧市差異化指標體系
與蘇錫常地區政府主導模式不同,嘉興市以市場主導機制為主,這樣的交易模式更有利于激勵企業主動參與排污權交易。以嘉興海寧市為例,和嘉興市秀洲區“秀洲模式”利用水資源有償使用置換環境容量的方法相比,海寧市則在總量控制的基礎上,施行差別化分配,推進環境容量市場化配置。
2013年9月,海寧市政府基于原有的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模式,提出了環境資源要素綜合配套改革方案,創新性建立了“產量論英雄”的指標激勵和分配機制,排污權指標采用“區域—行業—點源”的分配方式。首先,確定區域總量目標,其次建立“產量論英雄”的績效評價體系,最后進行指標差別化分配。

表2 海寧市排污權指標差別化分配流程[19]
通過市場化手段對環境容量進行初始分配與有償使用,使得嘉興海寧市的水環境治理獲得了顯著成效。同時也有利于政府激勵和引導排污權交易的二級市場。2014年海寧市應核減總量指標為90噸,實施差別化排污權配置后,核減總量為141.93噸。同時,海寧市積極開放二級市場,形成了政府負責儲備調節、市場引導流轉主體的格局。通過企業與銀行間富裕排污權的抵押融資、出售拍賣、租賃等金融業務來盤活存量,充分發揮排污權可配置、可交易的特征。
3.3.2 湖州市引入第三方核查機制
2009年6月至7月,湖州市在制定排污量核定規則的同時,開展市區排污總量核算。在吳興區選擇“金能達”、“三友”兩家印染廠開展老污染源第三方總量核查工作試點。與海寧市依靠政府法規進行差別化分配有所不同的是,吳興區“第三方強化核查”是由有資質的中介機構出具主要污染物排污總量核查報告,確認現狀排污情況,再組織局總量處和監察支隊等技術人員,并邀請企業總量核查報告編制的中介機構有關技術人員共同參與,現場認真核對企業審批或驗收確定的主要產污設備與現狀的差異,最終確定企業主要產污設備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通過對老污染源第三方總量核查工作,強化了企業排污總量核查規范性,有效地促進了市區老污染源排污權有償使用的全面推行。
自2009年湖州市試點實行排污權有償使用與交易制度以來,至2014年年底,湖州市三縣及市本級共受理1021家企業實施了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實施有償使用和交易的主要污染物有化學需氧量4241.5噸、氨氮315噸、總磷2.8噸、二氧化硫12 451噸。
湖州和嘉興兩市基于地方特征的創新管理方式可以激勵企業和加大監管力度,但是各地區不同的確認方式、執行標準和政策使得排污權交易總體規模較小,交易成本較高,其可復制難度較大。

表3 環湖地區排污權交易模式比較
4 環太湖流域水污染權交易制度比較分析
環湖六市在排污權的初始分配、價格確定、交易平臺、信息披露等方面都基于各地區社會經濟環境特征,進行積極探索。主要可以分為以市場為主導、有償使用的“浙江模式”,以政府為主導、有償使用的“江蘇模式”和以政府為主導、無償使用的“上海模式”。
4.1 制度設計與激勵機制
4.1.1“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
從排污權交易試點的浙江、江蘇兩省的情況來看,江蘇省通過出臺《太湖流域綜合治理管理條例》《太湖地區城鎮污水處理廠及重點工業行業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等條例,督促地方組織開展水資源有償使用以及排污權交易,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模式。但市場交易并沒有實施,雖然無錫和蘇州先行,也只有江陰市實現了排污權租賃。政府對于排污權的產權界定較為模糊,價格有待進一步優化。
浙江省總體是在政府監督下的市場運行機制實施排污權交易。例如嘉興市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權儲備機制;湖州市根據治太實際情況引入三方核查機制以及增加總磷、氨氮的交易指標;紹興市則將排污權作為生產要素,進行排污權融資抵押等。可以看出,浙江省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模式,由省政府支持監管和提供平臺,各地因地制宜推進實施。這樣的制度模式,有利于經濟市場的自行調節與發展,根據供需產生一個合理的價格水平,但跨市之間的交易存在一定的阻礙。
4.1.2 直接與間接的激勵機制
江蘇省對于水污染權交易的激勵方式主要是財政撥款的直接激勵。2010年12月3日江蘇省環保廳下撥蘇州市關于太湖流域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工作的運行維護經費;2011年12月3日江蘇省財政廳又追加款項作為排污權交易試點工作的補助。常州市在排污權價格體系的建設上采用新老企業區別對待的方式,政府對老企業予以一定的優惠,回購價格高于老企業的初始價格,低于新企業的有償價格。
浙江省將排污權交易與產業升級等結合在一起,設計系列激勵機制,先將排污范圍內的企業進行“三三制”的排名,分為“先進企業”、“一般企業”和“落后企業”,再根據各企業的完成情況采取不同的激勵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辦法:差異化減排、排污權指標激勵、超額減排激勵、淘汰落后激勵、先進地區激勵,從企業到地區多層次鼓勵開展排污權交易。對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激勵制度實施、淘汰落后、產業提升、污染減排等方面成效明顯的地區,在省級污染減排專項資金、污染整治專項資金等方面給予補助。
4.2 交易相關方分析
4.2.1 管理部門與企業的作用
在一級市場上,江浙兩省管理部門主要職責是核定排污總量,制定排污權有償使用基準價格和回購閑置排污權,是排污權的供給方。而企業則是購買方,即需求方,在上海則是無償配給。有所不同是,在核定排污指標方面,嘉興市主要是針對新企業,鼓勵老企業申購,但并不強制;而湖州市則是對新老企業統一實行標準,通過第三方機構對老企業的核查報告分配排污權。江蘇省和嘉興市類似,只將重點排污企業和新建項目企業納入,對于參與水污染權交易的對象條件不明確,關于老企業是否能申請水資源有償使用也并沒有明確的條例。
在二級市場上,嘉興市和上海市管理部門主要扮演的是調節、儲蓄企業之間富裕排污權的第三方,而買賣雙方都是企業。不同的是嘉興市是通過企業在排污權交易中心通過競拍方式獲得,而上海則是在政府指導價格下進行交易。在湖州,因為企業對于排污權的“惜售”,市政府正在積極探索二級市場的開放,希望以此來激勵督促企業減排。而江蘇省除了江陰市處于探索階段,其他城市還沒有開放二級市場。
4.2.2 交易成本分析
在水排污權交易中,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尋成本和談判成本[20]。主要集中在為了了解交易對象、市場排污權供給數量以及價格信息所花費的各種時間和機會成本,以及在確定完交易后,買賣雙方對水污染權交易價格等其他條約討價還價時產生的成本。從地方經驗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個地區的交易制度與辦法都各有不同,數量眾多。在完成交易時進行的合約履行以及信息搜索都不相同,沒有統一的規范,達不到規模效應,因此多番交易的成本就相對較大,也不利于省內跨區交易,全面推行面臨阻礙。
4.3 市場運行的有效性依賴于信息披露程度
雖然浙江省搭建了交易平臺和環境能源交易所,但是企業并不能完全從公開的信息中了解到自己所獲得的收益,也不能確定自己的策略是否使得利潤最大化。從博弈論角度而言,嘉興市開展的排污權拍賣和競價就是屬于這一類型的動態博弈。即參與者是相互獨立的,每一個參與者對排污權估價的二分之一作為投標價,便能反映出投標方在拍賣過程中遇到的最基本的得失權衡,價格越高越有可能獲得排污權,但是企業并不知道對方在下一輪是否是棄權,也并沒有完全了解對方企業的信息,所以浙江省的排污權交易雖然是動態博弈,但是還處于不完全信息狀態。
就江蘇省而言,管理部門在制定政策措施時,“自上而下”制度的基礎信息是不完全的,無法完全掌握企業排污和流域水質的情況,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不對稱信息。而蘇錫常三地由于擔心外部經濟環境的改變將影響現行排污權交易方,故推廣緩慢。綜上所述,在一級市場的初始分配上,信息披露和共享急需進一步加強。
4.4 政府主導型監管直接,市場主導型減排績效好
4.4.1 監管力度
不同的監管模式對制度的實施產生的效果呈現差異。江蘇省的交易模式是依靠各市相關管理部門來監督實施,這種監督方式雖直接易行,但因為信息主要是排污企業自行提供,在制度未能實現激勵相容時,監督效果受到質疑。浙江交易模式主要依靠市場力量推進,若存在交易紛爭,管理部門將介入進行協調工作。而湖州市提出的第三核查的機制,由第三方機構提供可靠鑒定報告,可以有效改善對企業監督問題,從而達到比較有效的狀態。
4.4.2 減排績效
通過不同的制度以及交易方式,各省市所達到的減排效果有顯著不同。浙江省交易和上海市交易對于水環境改善有著顯著作用,2014年在總磷參評和總氮不參評的情況下,總體達到了Ⅲ類水體[1]。而江蘇省的減排速度明顯比較緩慢,以無錫市為例,雖然在“十一五”期間13條主要出入湖河流中有12條河流水質達到或優于Ⅳ類,與“十五”末相比,Ⅱ~Ⅲ類河流增加了2條,劣Ⅴ類河流減少了5條,但是其工業廢水排污量還是遠高于其他環湖流域城市。

表4 環湖流域水污染權交易制度比較
從制度類型、激勵機制、產權界定、制度效果這四個尺度比較兩省一市的交易實施,如表4所示。在不同的制度設計下各省市在初始分配市場以及二級市場上存在差異。以政府主導的排污權交易(蘇錫常地區)主要是以初始分配為主,雖然有典型示范區域,交易相關方較明確,并且引入排污權租賃的交易模式,但蘇錫常地區二級市場并沒有進行交易,其租賃與回購制度設計對于企業的激勵作用較小,無法完全落實到位,存在產權界定不清晰,交易成本高等問題,水環境的改善不顯著;而市場主導的排污權交易(浙江嘉興)雖然有良好的二級市場,僅對新建企業,交易規模較小,不可跨區縣交易。同時與鄰近地區湖州市相比,存在交易主體、交易指標和交易價格的不統一,使得價格較低地區的企業存在“惜售”心理,阻礙交易制度的推廣。由此可知,要使水污染權交易市場穩健的運行,需要以整個流域為單位,政府確定總量,市場決定價格,確保一定交易規模基礎上,推進交易市場的運行。
5 建立流域統一的水污染權交易市場
太湖流域各地不同的污染物核定方式、交易指標差異,難以開展跨區交易;價格偏低,使得排污量富余方存在著“惜售”心理;污染物之間的不可轉換性進一步減少交易規模。因此,為確保排污權交易在太湖流域環境改善中的作用,急需建立以流域為單位的統一排污權交易市場a在課題進展討論中,浙江大學范柏乃教授啟發指點。。
5.1 統一污染權初始核定
水污染權初始核定屬于一級市場體系的范疇,就已開展的地方經驗來看,對于水污染權初始核定方式各不相同,蘇錫常地區主要依靠企業上報數據的方式核定排污量,而湖州等地區則是依托第三方核查機構所出示的環境評估。因為第三方的核查機制具有社會監督性,應當將其作為環湖六市初始核定所需排污量的主要方式,地區可再根據每一企業減排任務達標完成率來分配排污指標。同時,形成流域協調意識也十分重要,排污技術較為發達的地區(如湖州、嘉興)可以通過流域管理局將富裕的排污權轉讓給工業比重較大的地區(如錫常地區),在企業交易的同時,形成流域范圍的跨地區交易。
5.2 統一交易平臺
從案例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各地都設置有排污權交易中心與儲備中心,如上海市、蘇州市增設的環境能源交易平臺、嘉興市排污權交易中心、常州與湖州市排污權儲備中心。不同而分散的交易平臺使得企業搜尋成本較高,且存在交易壁壘,因此統一排污權交易平臺顯得十分重要。建設整個環太湖流域的水污染權交易平臺,實現規范有序的排污權交易市場,不僅能夠降低企業之間的搜尋交易成本,而且能進一步擴大水污染權交易規模,使得排污權的交易范圍覆蓋到整個流域,交易機制得以真正運行。
5.3 統一交易程序
在交易過程中存在各類交易成本,如企業搜尋成本、議價成本、機會成本等。如這類成本不能有效的降低,直接會導致企業污染治理成本過高,對水污染權交易的積極性降低,并減少因環境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從而無法實現規模化的水污染權交易市場。太湖流域工業污染的重要污染源是蘇錫常地區重工業,及浙江省部分傳統印染造紙行業,流域內企業數量多、范圍廣,交易成本問題尤其突出。在交易進行過程中,除了作為排污權供給方的政府和需求方的企業,中介機構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環節(圖1)。因此,應效仿嘉興市興業銀行對于排污許可的抵押貸款的經驗,鼓勵金融中介機構參與水污染權交易體系中,為企業提供交易信息,價格調整及競價功能,等到市場完全成熟時,可以提供相關租賃、抵押、貸款等業務。
二級市場水污染權交易價格主要由供需的市場機制所決定,可以借鑒國外流域管理經驗,在環太湖流域建立“交易信用”機制[22],將交易比率納入水污染物排污權初始定價模型中。企業可以根據交易信用評級來選擇購買對象,同時對于需要出售排污權的企業,也可以因其良好的信用度獲得更多的利益。而納入交易比率的主要目的是根據不同水質在流域內進行比重分配,污染較為嚴重的地區應當給予較高的交易比重,而水質較好的地區則可以相應減少,這樣不僅使得水環境有了針對性的改善,也使得水污染權交易成為一項地方性質的任務,以此對各地區交易規模及情況進行考核。

圖1 水污染權市場交易流程
5.4 統一交易對象
水污染權交易對象可以分為主體和客體,主體一般是指參與交易的企業,客體主要是排污指標。統一水污染權交易對象可以增加交易量,擴大規模。從現有實施情況來看,各地對于參與排污權有償使用的企業劃分不一,例如江陰和湖州地區新老企業都需進行排污權有償使用,而在浙江嘉興市只對新企業征收排污權有償使用費。由于水環境容量的短缺,凡是需要排污的企業都應進行水污染權有償使用。
而在交易客體方面,各地對于污染物指標劃分也不同,例如湖州市將總磷、總氮、COD均納入排污指標,而嘉興市只對COD和二氧化硫進行排污權征收。由于太湖流域污染源中涵蓋總磷及總氮,同時也是總量控制的指標,因此應將總磷和總氮納入水污染權交易的對象,同時為了保證交易規模,對不同污染物實現統一污染當量換算,如COD與總氮、總磷之間通過流域制定技術標準,實現換算。
5.5 統一管理機制
排污權交易制度通過發揮市場機制,實現非市場的商品——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將非市場化商品實現市場運行,急需管理部門在產權界定、初始分配、信息披露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務。首先,相關流域管理部門應當統一儲備各地排污權,而地方政府必須基于流域的總量指標開展排污指標的初始分配及發放。其次,在進行水污染權二級市場交易的過程中,流域管理部門應當充分發揮地區間協調作用,各地區管理部門應起到監管市場和引導企業的作用(圖1)。目前,關于企業排污等信息及數據庫的建設、二級市場交易平臺建設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仍不完善,亟待相關管理部門的投入與建設。同時,在一級初始分配上應加大第三方核查,二級交易市場上依托供需機制,確保市場機制的運行績效。
[1] 水利部. 太湖流域及東南諸河水資源公報[A/OL]. 2014 (2015-11-09) [2016-12-06]. http://www.tba.gov.cn//tba/ content/TBA/lygb/szygb/0000000000008320.html
[1] 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60, 3(1): 1-44.
[2] DALES J H. Pollution, Property and Prices: An Essay in Policy-making and Economic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8: 10-12.
[3] MONTGOMERY W D. Markets in licenses and efficient pollution control program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2, 5(3): 396-418.
[4] 沈滿洪, 謝慧明. 生態經濟化的實證與規范分析——以嘉興市排污權有償使用案為例[J].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10(6): 27-34.
[5] 劉文琨, 肖偉華, 黃介生, 等. 水污染物總量控制研究進展及問題分析[J]. 中國農村水利水電, 2011(8): 9-12.
[6] 畢軍, 周國梅, 張炳, 等. 排污權有償使用的初始分配價格研究[J]. 經濟政策, 2007(13): 51-54.
[7] 王金南, 張炳, 吳悅穎, 等. 中國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 實踐與展望[J]. 環境保護, 2014, 42(14): 22-25.
[8] MARCHIORI C, SAYRE S S, SIMON L K.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water rights buyback schemes[J].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2, 26(10): 2799-2816.
[9] 喬小楠, 段小剛. 總量控制、區際排污指標分配與經濟績效[J]. 經濟研究, 2012(10): 121-133.
[10] 周樹勛, 陳齊. 排污權交易的浙江模式[J]. 環境經濟, 2012(3): 55-57.
[11] 柳萍, 王鑫勇, 任益萍. 排污權交易制度與價格管理研究——以浙江省為例[J]. 價格理論與實踐, 2012(4): 13-15.
[12] F?RE R, GROSSKOPF S, PASURKA C A JR. Tradable permits and unrealized gains from trade[J]. Energy economics, 2013, 40: 416-424.
[13] 劉年磊, 蔣洪強, 盧亞靈, 等. 水污染物總量控制目標分配研究——考慮主體功能區環境約束[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5): 80-87.
[14] 吳瓊, 董戰峰, 張炳, 等. 排污權交易: 漸呈蓬勃之勢[J]. 環境經濟, 2014(1-2): 37-41.
[15] 王潔方. 總量控制下流域初始排污權分配的競爭性混合決策方法[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4, 24(5): 88-92.
[16] 國家海洋局.中國海洋統計年鑒[M].海洋出版社,2010-2013.
[17] 丁純潔,瞿建華.江陰新聞:江陰排污權交易試行5年 730家企業告別“免費午餐”時代[N/OL].(2014-05-04) [2016-07-08]. http://www.ijiangyin.com/article-299808-1. html
[18] 周樹勛.排污權核定及案例[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9] 埃瑞克·G·菲呂博頓,魯道夫·瑞切特. 新制度經濟學[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1998.
[20] 袁群.國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經驗對長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啟示[J].水利科技與經濟,2013,19(4):1-4.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in the Taihu Lake Basin—Based on the lnvestigation of Six Cities
ZHANG Yifei1,2,3*, LIU Junye1,2, ZHANG Lei3,4, QIN Qiongxia3,4
( 1. Business Schoo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2. Research Center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Econom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3. Center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18;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
As on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ed areas, water pollution have become a serious constrain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hu Lake basin.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earliest basin carrying out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the summary of the policy experience in Taihu basin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on the promotion of setting up emission permits and operating pollution emission trading. From the investigation in Jiaxing, Huzhou, Suzhou, Wuxi, Changzhou and Shanghai,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in the aspects of system design, property right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ystem efficiency. As a result, we find that market-orientated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ystem performance, and the size of the trading market is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ding system.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how to unify the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according to these problems and discoveries.
pollution emission trading; Taihu basin; unified trading market; market size
X321;D922.6
1674-6252(2017)01-0033-08
A
10.16868/j.cnki.1674-6252.2017.01.033
a 本文所指太湖流域包括:蘇州、無錫、常州、湖州、嘉興、上海青浦地區,由于安徽省占地域面積只有1%,故忽略不計。
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編號:14ZDA071);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40901291)。
*責任作者: 張翼飛(1975—),女,教授,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全球氣候變化與綠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生態資產評估、排污權交易制度,E-mail: Yifei_zh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