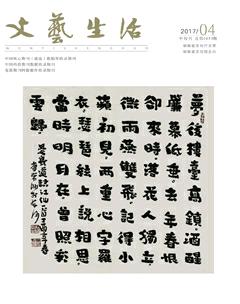“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的電視媒介儀式研究
王登羿
摘 要:“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融合電視晚會、娛樂綜藝、明星、全媒體互動與線上購物于一體,以電視直播儀式性晚會的形式,助推“天貓雙11”購物狂歡浪潮。一個因購物狂歡而誕生的節日,一場全球數億人次觀看以購物狂歡為主題電視儀式性晚會,在資本與電視合謀的媒介儀式傳播中,傳媒消費主義色彩愈加凸顯。
關鍵詞:媒介儀式;電視晚會;天貓雙11
中圖分類號:G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11-0104-01
當媒介本身成為一種儀式或集體慶典,從“傳播儀式觀”角度看,媒介不只是在空間上對信息的傳遞,更是參與到現實建構和意義闡釋當中。“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并非簡單通過電視和網絡平臺直播,傳遞“雙11”這一購物狂歡節日到來的訊息,這樣一臺晚會在短短兩年時間,就成為“雙11”重要的組成部分和人們關注的焦點,正是因為其以儀式性媒介的身份,參與到了“天貓雙11狂歡夜”這一節日的現實構建與意義闡釋的過程,不斷激發大眾購買欲,對“物欲之神”頂禮膜拜,悄然影響著大眾行為邏輯,從“儀式性欣賞”到“大眾狂歡”。
一、“儀式”與媒介儀式傳播
何為“儀式”?相關的探討遍及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各個領域。儀式最初只是一個宗教概念,后來被人類學家普遍地用來指稱那些具有高度形式性和非功利性的活動。 “儀式”作為社會群體定期重新鞏固自身的重要手段,因其所具有的獨特的構筑社群共同體的重要功能,而成為東西方文明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部分。無論是身體在場亦或是精神在場,通過“儀式”都可以結成臨時或長久的共同體。
通過儀式特征來分析“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我們可以看到,“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使得分散在五湖四海,等待11月11日零點開始購物狂歡的受眾,在長達近四個小時的直播晚會中,穿越空間阻隔,同步參與到這樣一場為購物狂歡準備的儀式進程。20世紀50年代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提出了“儀式性傳播”模式:“傳播的儀式觀不是指空間上訊息的拓展,而是指在時間上對社會的維系,它不是指一種信息或影響的行為,而是共同信仰的創造、表征與慶典”①, “其核心則是將人們以團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禮。”②“天貓雙11狂歡夜”通過一場儀式性晚會將一場購物狂歡變為神圣典禮,以對“物欲之神”的膜拜,讓受眾陷入非理性的購物狂歡。
二、“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的儀式性傳播
“電視直播晚會”這一形式增強了“天貓雙11狂歡夜”不同于普通日期的特殊性。在對“儀式”的定義中,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其區別于一般日常活動的特殊性,是對日常生活的強調和超越。阿里巴巴集團希望通過這樣一場電視、網絡全媒體直播的儀式性晚會,把“雙11”從原本單純的承載日期信息中解放出來,賦予其“購物狂歡節”的儀式意義。對“天貓雙11狂歡夜”儀式“內涵”進行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的提煉出“狂歡——購物——快樂”之一循環機制,在整個儀式性晚會當中不斷重復,從而使大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樣的行為預設。看似沒有任何強迫,完全自發的,充滿自由意志的購買行為背后,實際早已受到商業資本的操縱。而“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這樣一場儀式性晚會的目的,正是為了淡化直至掩蓋掉操縱大眾陷入非理性購買行為邏輯的現實,引導受眾接受“自由的購物”便可“自由的生活”,并以此獲得快樂的思維邏輯。
“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成功實現了對于“購物狂歡”這一行為“信仰”式的塑造。“天貓雙11狂歡夜”總銷售額作為每年購物狂歡節大眾極為關注的焦點,事實上已經成為一種“消費圖騰”式的存在。通過電視儀式,將分散于各處的觀眾,通過儀式性晚會消弭空間上的距離感,從而實現共同體的凝聚,進而完成“購物狂歡” 信仰的塑造,使得觀眾清晰、自主的接受晚會所要傳達的意圖,以“神圣化”的儀式包裝達成高質量的傳播效果和功能實現。
三、與資本合謀的電視媒介儀式
但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天貓雙11狂歡夜”晚會的儀式性傳播,實際上是大眾傳媒通過媒介儀式與商業資本合謀參與現實構建與意義闡釋的過程,暗含著消費主義肆意滲透的風險。消費主義對于日常生活的侵襲,并非來源于抽象的理論層面,成熟的商業市場與觀念,是消費主義發揮影響的重要載體。從消費主義的發展軌跡來看,經濟領域雖然是其產生的根源,但快速的發展和擴張與高度發達的大眾傳播媒介在全世界范圍內對其的傳播密切相關,對于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消費主義轉向,我們要有足夠的警惕。
今天的電視將通俗化力量發揮到了極致,卻絲毫不會觸及人們的思維結構。象征的革命會觸及人們的思維結構,“改變我們的觀察和思考方式。”③但當我們開始正視目前電視領域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尋求解決之策時,往往會發現,陷入了一個又一個死循環,變革意味著極大的風險,競爭邏輯與商業資本都不允許這種風險的出現。而更令人感到無奈的是,當我們回望電視發展初期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會發現,那時的電視利用自己壟斷性的信息傳播手段,給大眾“強加了有文化追求的產品”④,而今天的電視,淪落為一味迎合、討好受眾的通俗化甚至粗俗化的文化產品的傳播平臺,一味地討受眾歡心,并非一個大規模傳播工具民主性的體現。
注釋:
①②詹姆斯·凱瑞,丁未(譯).作為文化的傳播[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③④皮埃爾·布爾迪厄,許鈞(譯).關于電視[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