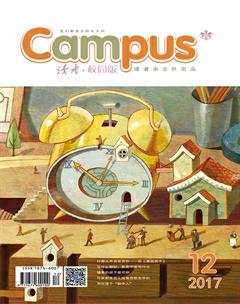寫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寫作文
張大春
我在小學五年級時遇到了俞敏之老師。俞老師教語文,也是班主任,辦公桌就在教室后面,她偶爾會坐在那兒抽沒有過濾嘴的香煙,夾煙的手指被熏得黃黃的。俞老師打人,她的兵器是一根較細的藤條:有時候抽抽屁股,有時候抽抽小腿,點到為止。那一年教育政策定案,初中聯考廢止,風中傳來的消息就一句話:比我們高一級的學長們都無須參加聯考就可以進入中學了。而俞老師卻神色凝重地告誡我們:“你們如果掉以輕心,就‘下去了!”
五年級正式開課之前的暑假,學校還是依往例舉辦暑修班,教珠算、作文。俞老師使用的課本很特別,是童書作家蘇尚耀寫的《好孩子生活周記》。兩年之后我考進另一所私立初中,才發現蘇尚耀也是一位語文老師。
初見蘇老師,是在中學的校長室里。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學沈冬獲派參加臺北市中學生作文比賽。行前,校長指定高年級的語文老師來為我們“指導一下”。蘇老師摘下老花眼鏡,端端正正插在胸前的口袋里,問了兩句話:“你們除了讀課本,還讀些什么書啊?除了寫作文,還寫過什么東西?”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師,想起了《好孩子生活周記》,但是我連一句話都沒來得及回答,蘇老師就自己回答了:“我想是沒有的!”
寫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寫作文
在校長室里,蘇老師并沒有提供什么作文方法、修辭秘籍,只是不斷提醒我們:“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至于我們所關心的比賽,他也只是強調:“參加就是參加了,得不得獎只是運氣,不必在意。”
我和沈冬運氣不錯,拿了個全市第一。為什么說“我和沈冬”呢?得獎的雖然是我,可是我一直認為,臨場慌張匆忙,忘了檢查座位,很可能我們錯坐了彼此的位子。因為我深信自己寫的那篇文章實在是爛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我把獎品推讓給沈冬,至于寫著我姓名的獎狀,則收了壓在抽屜底。
蘇老師從此成為我私心傾慕的偶像。每當我在校園里看到他抱著課本踽踽獨行,就會想起他的話:“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話里好像有一種很宏大的鼓勵。
回頭從寫作文說起
俞敏之老師平時說話簡明扼要,句短意白,從未賣弄過幾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辭手法”。印象中,她常鼓勵我們多認識成語,不是為了把成語寫進作文,而是因為成語里面常常“藏著故事”。但是一旦罵上了人,她的話就無消無歇、無休無止、“綿綿無絕期”了。我甚至覺得,若不是因為在拈出差作文時可以痛快罵人,她可能根本不愿意上這堂課呢。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了“載欣載奔”這個成語,俞老師給畫了個大紅叉,說:“怕人家不知道你讀過陶淵明嗎?”“讀過陶淵明就要隨手拿人家的東西嗎?”“人家的東西拿來在你家放著,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適嗎?”
現在我已經想不起來是在什么樣的上下文之間用了這個成語,但是俞老師足足罵了我整整一個課間,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強調的是文言語感和白話語感的融合。同樣是“載……載……”,我們在使用“載歌載舞”時或許不會感到突兀,而用“載欣載奔”形容高興奔跑時,卻難掩那雅不可耐的別扭。
五年級下學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師出了個作文題:“放學后”。我得的是“丙”。非但成績空前的差,在發還作文簿的時候,俞老師還專門用我的那篇作文當反面教材,聲色俱厲:“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個十萬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寫的是四個字、四個標點符號:“打啊!殺啊!”——這當然是指放學之后校車上最常聽見的打鬧聲。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寫道:“我是坐校車上下學的……”
俞老師搖晃著我的作文簿,接著罵:“‘打啊、殺啊跟你坐校車有什么關系?文從字順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嗎?上面一個字跟下面一個字可以沒關系嘛,上面一個詞跟下面一個詞也可以沒關系嘛,上面一句話跟下面一句話也可以沒關系嘛!”你已經聽出來了,老太太說的是反話!接著,隔了五六個同學,她把作文簿扔了過來,全班同學一時俱回頭,都知道是我寫的了。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對我說。
小學、中學一起畢了業
從俞老師帳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過我語文的還有六位老師,幾乎每位老師都當堂朗讀過我的作文。那些一時為老師激賞、同學贊嘆的究竟是些什么東西,我連一句、一字都記不得了,印象深刻的偏只有“載欣載奔”和那篇《放學后》中的蹩腳的起手式。兩番痛切的斥責,字字灌耳,不敢忘卻。
初中畢業前夕,高中聯考在即,我帶著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記》,在理化教室旁的樓梯上攔住了蘇尚耀老師,請他給我簽個名。他從中山裝胸前的口袋里取出老花鏡戴上,工整地簽下了名字。我問他:“為什么您說,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寫作文?”
他乍沒聽清,我又問了一次,他沉吟了一會兒,才說:“作文是人家給你出題目;真正寫文章,是自己找題目,還不找人家寫過的題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覺小學、中學一起畢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