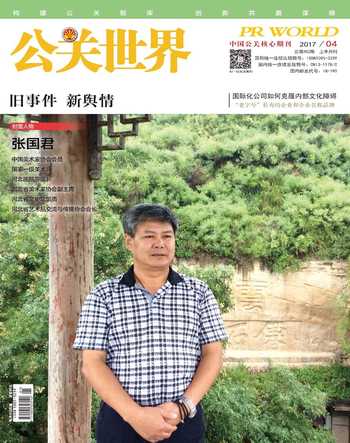宋代士大夫交游宴集中的公關心態
肖瀟
由于宋代統治者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士大夫整體地位之高,社會影響力之大,以至于形成“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使整個士大夫階層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十分活躍。兩宋時期士大夫交游宴集活動豐富多彩,士大夫關注自身的生存意義和生活質量,按照自己的意志與需求選擇交游宴集的對象和內容,進行主動而自覺的休閑活動,蘊含其中的公關心態也隨之浮出水面。
一、愉悅耳目 聲色犬馬
步皇親貴戚之后塵,宋代士大夫多參與享受型歡宴,多表現為飲酒、狎妓、享樂、嬉戲。宋代統治者對士大夫的休閑活動持鼓勵態度。宋太祖自導自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大戲,自此,官方多用豐厚的物質賞賜和優厚待遇引導和鼓勵官員士大夫“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王明清《揮塵后錄》中記載風流才子大學士蘇軾“春時每遇休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后,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尤未罷,列燭以歸。城內士女云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盛事也。”蘇軾為求“眾樂樂”,于春日美景之時邀集賓客,攜帶妓女,游湖賽舟,場面熱烈,成為城中吸引眼球的公關盛事。
宋代士大夫沉醉于內容豐富的交游宴集活動中,王夫之于《宋論》中講到:“一時人士,相率以成風尚者,章蘸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清歌妙舞,狎邪冶游,終日疲役而不知倦”,南宋更是“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林升有詩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聲色犬馬中完全地追求感官刺激和身心愉悅。歐陽修在一次和幕僚宴飲聚會后作詩稱:“繞郭云煙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霜林落后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斜日照青松。會須乘醉攜佳客,踏雪來看群玉峰。”佳客環繞,美酒相伴,想必宴飲是歡暢盡興的,賓主雙方單純地在歡洽中體驗休閑樂趣。
士大夫聚會時還往往增加一些娛樂活動來調節氣氛。柳永《笛家弄》中提到“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呼盧即樗蒲,是唐宋時期流行的一種賭博方式,在宴飲時倍受歡迎。晏幾道《清平樂》又道“畫堂秋月佳期,藏鉤賭酒歸遲”,其中藏鉤也是人們宴飲歡聚時的游戲,將一枚小物件藏于某人手中,猜中者為勝,不中則罰酒,通過這些娛樂活動佐酒,賓主皆輕松暢快,其樂無窮。
兩宋酒肆茶坊、瓦舍勾欄遍及大街小巷,堪有“花陣酒地”之稱,這些都為藝伎侑酒、按管調弦提供了絕佳場所。文人騷客流連于青樓酒館,與藝伎交往頻繁。晏殊熱衷于宴請賓客,把酒言歡,并佐以藝伎,酒興之余喜作詞“獻藝”,如《破陣子》詞云:“燕子欲歸時節,高樓昨夜西風。求得人間成小會,試把金樽傍菊叢。歌長粉面紅。斜日更穿簾幕,微涼漸入梧桐。多少襟懷言不盡,寫向蠻箋曲調中。此情千萬重。”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并有美女相伴左右,把酒傍菊,任無數愁緒傷懷滑落于杯盞蠻箋之上。美姬侑酒勸觴,文人陶醉其中,內心的千種風情、萬般思緒都在這杯盤之間得到釋放。
二、文藝品鑒 會友求知
宋代文人士大夫多才華橫溢,并具有一定的藝術素養,因此志同道合之輩多借宴集交游之機進行詩文唱和、品茶聽琴、書畫珍玩鑒賞等活動,以此尋求知音,陶冶情操,切磋文藝。
如北宋仁宗年間,當世才子歐陽修、宋祁、王洙、李淑、楊儀、刁約、王舉正等館閣侍從文人七人,就曾春集東園賦詩唱和。宋祁在《景文集》中總結此次雅集時云:“是集有三勝焉,地之勝,時之勝,賓之勝。三者先具,吾人所以擠天下細故,彷徉蕭散而自適其適也……輕風舞于快余,鮮云曳于曬表,樂斯詠詠斯陶……”此番雅集,歐陽修得詩《春集東園詩賦得節字》,宋祁得詩《春集東園詩賦得筍字》,其他人也分別作詩如“得蕊字”、“得萼字”、“得蒂字”等等。
北宋哲宗年間有一次大型的宴集活動,名噪一時,此次集會被認為是繼書圣王羲之組織的“蘭亭雅集”之后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文人集會。大畫家李公麟乘興而作《西園雅集圖》,可謂情景再現。卷中以寫實的方式描繪了眾多文人雅士、社會名流,如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秦觀等人,在駙馬都尉王詵府中作客聚會的情景。畫中之人或揮毫用墨、或吟詩賦詞、或扶琴唱和、或打坐問禪,每個人的表情動態在李公麟筆下皆栩栩如生,人物衣紋、草石花木、松檜梧竹、小橋流水,極園林之勝,處處顯得精致而明快,瀟灑而雋逸。畫中,這些文人雅士皆衣著得體,動靜自然,風云際會,一展才情;而書童侍女之輩,也都舉止斯文,落落大方,賓主風雅,極宴游之樂。大畫家米芾為此圖作記,即《西園雅集圖記》,并作文稱頌:“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如此。嗟呼!洶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哉。”
南宋著名詞人辛棄疾愛宴飲,常常大擺筵席,邀集佳賓前來切磋詩詞文章,岳珂《桯史》記載:“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局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每吟誦到如此得意之作時,就拍著腿大笑,遍問客人此句如何,大家都嘆譽贊賞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遍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辛棄疾往往置酒延客,席間令歌伎演唱,遍問客人自己的文章詩詞哪里不妥,如果客人謙遜不答或是語焉不詳,或所言不合心意,則默然揮動羽扇環顧四周。
宋代是我國茶文化的鼎盛時期,品茶會和斗茶會不勝枚舉。由于官僚貴族的倡導示范,文人僧徒的崇奉傳播,市民階層的廣泛參與,飲茶在精神文化領域成了一種流行時尚。品茶作為閑暇之際的高品位活動,受到士大夫推崇;也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成為士大夫社會交往中的一種媒介,品茶和茶藝鑒賞在士大夫宴集聚會活動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陸游有詩云“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與友人靜觀分茶技藝,閑閑地品一品茶香,使君子之間心靈相通,思想凈化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宋代茶藝還追求高雅的藝術氛圍,吟詩、聽琴、觀畫、賞花、聞香等成為茶藝活動中常見的休閑項目。梅堯臣詩云“彈琴閱古畫,煮茗仍有期”,真乃雅事。宋代有諺云“燒香、點茶、掛畫、插花為‘四般閑事,”反映在宋徽宗的《文會圖》和《聽琴圖》中,則生動地再現了宋代士大夫雅集時將茶、酒、花、香、琴、畫等藝術形式完美融合的情景。
宋代士大夫還熱衷于收藏和鑒寶,他們往往追求一種博古通今的學術趣味,展示了士人生活的高端格調。他們在休閑、舉辦雅集與音樂會時,往往都會陳列古董,以供清玩。從劉松年的《博古圖》和《圍爐博古圖》中可以看出,士大夫們在鑒賞古玩時,會擺上茶具,煮水品茶,好不清雅。難怪王國維感嘆,“漢、唐、元、明時人之于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
為了滿足審美和社交的需要,士大夫在形式多樣的雅集活動中展示著自身的特色與情感,張揚個性的同時,也在群體的力量中找到自己的歸宿,個體風采與群體認同感交相呼應,維護良好而持久的公共關系,為士大夫的各種交游宴集活動注入了強大的生機與活力。
三、君子有黨 積極入世
宋代士大夫追求群體認同感,他們的集會很多時候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或功利目的性,政治責任感強,傾慕“君子之交”,在欣賞對方的同時,也希望得到對方的欣賞,在開拓政治前景的同時,保持著自信的氣質和惺惺相惜的公關情感。
沈括的《夢溪筆談》中記載了一則著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北宋仁宗年間,韓琦任揚州太守時,官署后花園中有一種名貴的芍藥盛開,一枝四岔,每盆都開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紅色,一圈金黃蕊圍在中間,因此被稱為“金纏腰”,又叫“金帶圍”。此花不僅花色艷麗、奇特,而且傳說此花一開,城中就要出宰相。當時,同在大理寺供職的王珪、王安石、陳升之三人恰好在揚州公干,韓琦便邀請他們前來一同觀賞。飲酒賞花之際,韓琦做出了頗有深意的舉動,他剪下這四朵金纏腰,給在座的賓主四人每人頭上插了一朵。說來也奇,此后的三十年中,參加賞花的這四個人竟先后都做了宰相。這就是有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此后作為一則佳話,流傳甚廣。
事實上,“四相簪花”這樣的“賞花會”本身所呈現的正是宋代上層社會交往方式的一個側面,士大夫藉由類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彼此聯絡情感,并且建立自己在上層社會中的聲望,這種獨特的文化風氣,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或同僚之間舉行便宴時簪花已成為社會的一種習俗;并且這些場合也是他們取得各方面訊息的重要來源。此外,當時士大夫對于“祥瑞”的附會也反映出知識分子對于攖紫奪朱的公關意識。
古往今來,“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深入人心。“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遠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是儒家社會的主流意識,入仕做官,建功立業,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宋代士大夫主張“君子有黨”,呼吁帝王應明辨“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朝廷則無朋黨之憂。士大夫往往滿腹經綸,懷揣理想,有著一展才華、經邦濟世之渴望。為了更好地施展政治抱負,希望在自己周圍建立起一個強大的政治集團,而將固定的交游宴集關系引入政治生活,形成良好而持久的公共關系。
后人尤其是讀書人談起“四相簪花”盛會,無不心向往之。這則故事符合中國人祈盼封侯拜相的最高理想,表達了人們強烈的功名思想。反映了士大夫積極的入世心態,包含了豐富的政治哲學,通過宴飲集會展示自身的風度和修養,打開人際關系。儒家思想是不提倡隱者式的封閉生活的,它主張積極地參與社會交往,直面社會,關心民生,強調禮樂秩序,表達的是一種協調社會關系以使之和諧的政治主張,其主旨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四、攜友同游 恬淡超然
士大夫由于特殊的人生際遇,或退出政治舞臺,或自然地功成身退,多表現為隱逸交往,如閑云野鶴般的與僧道交游。司馬光退居洛陽時,曾與道人樂全子同游洛陽附近的佛寺道觀和山林勝景。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錄》中記載:“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內 ,并轡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急下院,促嵩陽,造崇物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巡會善寺,過寰轅,遽達西洛……”宋代士大夫深受佛道思想浸染,對游覽佛寺道觀等宗教場所有一定的情結,在宗教神靈的庇佑下尋求心靈的解脫,忘卻塵世的煩憂,完全達到精神的返璞歸真。
退休士大夫也有機會參與宴集,被稱為“怡老會”,是為了老年文士和退休官員怡情養性而舉辦的群體活動。各地怡老會有不同的名目,如李昉在東京汴梁組織的九老會;徐佑在蘇州舉辦的九老會;文彥博在洛陽舉辦的五老會、耆英會;司馬光在洛陽舉辦的真率會等等。舉行地點多是城市郊區環境優美僻靜之所,老年士大夫生活無憂,遠離廟堂,閑暇時通過這樣的聚會既可欣賞郊外風光,又能與老友伙伴攜手言歡,修身養性,恬淡愜意。
“五老會”時文彥博有詩云:“四個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難論”,又說“如今白發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綬人”,最后抒發閑適之情。任杰詩云:“太平只恐罩嘉魚,松菊清涼月影疏。”很多人都表達了和唐代白居易同樣的感受:“此會從來誠未有”,希望能夠“茲事實可矜,傳之足千祀。”可見一些退休士大夫不滿足于獨自一人孤芳自賞,希望老有所樂,參與到昔日同僚和好友的聚會中,為行將老去的年華平添一絲樂趣和希冀。
宋人馮時行曾在蜀中為官,退休離任前在郊外與友人們宴飲閑游,并在文章中談到:“昔人謀于野則獲,閑暇清曠,有爽于精神思慮,游不可廢如此也!又說所與游,皆西川各侈喜事都耶。”拋卻功名利祿的羈絆,單純地與知交好友攜手同游,享受優哉游哉的休閑時光,何嘗不是人生中一大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