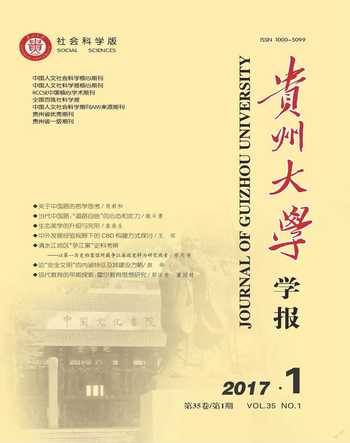“慎終追遠”衍義
劉靜
摘 要:喇叭苗是貴州眾多民族的一支,他們同安順的屯堡人同源,都是屯堡文化的產物,但其文化的最終展現形式卻不一樣。雖然被認定為苗族,他們卻依然堅持著對原初文化的保持。喇叭苗以華夏農耕民族“慎終追遠”的文化特性來展現自己的文化自覺。通過對現象的研究開啟對喇叭人文化“體”的追尋,通過尋求他們文化的源遠流長性,來探討喇叭苗對自身文化的認可和對本民族的認同。以期用其文化的“體”的來支撐其民族文化的“用”,并從中闡述喇叭苗人文化自覺的特性。
關鍵詞:喇叭苗;慎終追遠;祖先崇拜;文化自覺
中圖分類號:C9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7)01-0099-04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17.01.16
“慎終追遠”是華夏農耕民族文化特性同是也為一個民族的認同奠定了極具現實性的心理基礎,它更是百姓在“安身”之時的精神寄托,是一種終極的“立命”之求。無論在何時在何地,“慎終追遠”對中國人都有著廣而久的影響力。而民族的文化自覺則包括對自己民族的認可,文化的認可也包括對其他文化的一個融合,其實是一個民族文化合金性的一種發展。貴州的喇叭苗是一個時代特殊經歷的存在,他不同于安順的屯堡人,雖然二者的成因極為相似,要么是駐兵屯田的后人,要么是移民開拓者的后人。喇叭人大多生活在貴州北盤江上游的崇山峻嶺之中,在幾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基本上過著自給自足的半封閉式的生活。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特性,貴州喇叭人在1983年左右才正式被定為苗族,在此之前,他們都自稱為“喇叭人”。雖然生活環境艱辛,但喇叭人從未忘卻自己的來路,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并用自己的方式克紹箕裘。他們游離于各族之外,又與各族生活在一起,與之不斷發生文化的碰撞。由于一種固執的堅持,讓他們成為了有別于漢族,又有別于傳統苗族的存在。下面將從“慎終追遠”的角度尋找喇叭苗的文化的“體”或是他們文化的源頭,通過喇叭苗人在文化上的自覺來闡述其文化的特性,以期對其民族文化的“用”有所支撐。
一、“三洞桃源”:“追遠”的祭祖文化
曾子有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1]50,不管是“慎終”還是“追遠”,皆要求后人以嚴肅的態度,以極致的悲傷體現對過逝父母的敬愛,對遠逝先祖的追念。換而言之,“慎終追遠”培養了一個民族最為基本的感恩情懷。在喪中“盡其衰”,在祭中“盡其敬”的過程中形成溫柔敦厚的品質。它強調的是“孝”“悌”的終端,從所求的立場以精神寄托的方式來踐行“厚”的品德。畢竟,淳厚的道德品質依賴的是后天的教化。在民間,“慎終追遠”的一系列儀式便充當了禮義教化的承載體,在誠心正意的祭祀禮儀中潛移與默化,從而形成了一個溫和敦厚的民族。
貴州的喇叭苗是一個喜歡“追遠”的群體,他們是軍事遷徙的產物,史書上有載在普安縣一帶“有老巴子”他們“亦苗類”,大多由“湖南”移居于這一地區,這些被稱之為“老巴子”的人“服飾與漢民同”[2]228語言也相對通俗易懂。在貴州府縣志輯的記載則相對詳實一點,據載當年來自于湖廣的兵士們肅清當地的匪患后“不思遷鄉”,很多士兵選擇“贅苗婦”[3]就在本地安家建業,繁衍生息。經過長時間的文化融合,他們的男子仍然堅持著漢人服飾并堅定的認為自己是漢族的后人,故也被周邊的人稱之為“老漢人”或是“湖廣人”,而女子因母族的原因則守住原本的紅苗仡佬的服飾風格。喇叭人是個堅持的群體,他們在對先祖的追懷上從不含糊。無論是屯兵后人還是開荒的平民,都證明了喇叭苗是一種移民文化的衍變,他們的先祖都烙印著農耕民族的標志,而溫柔敦厚的人格正是農耕文明最具特色的產物,這種人格的培養是希求穩定減少社會動亂的一個心理訴求。《左傳·成公十三年》曾有載,一個國家的大事“在祀與戎”,國家之大事一般有二,一是祭祀,二是戰爭。“祭”代表著國家的統一,民族的融合。對共同祖先的崇拜標志著一個民族的凝聚之力與向心之力,能使人從血親上的“祖先認同”走向一個民族的認同。明洪武時期的屯兵行為促成了喇叭人族群建構的原初推力,但是一個族群的建構還需要一個共同的心理基礎,“慎終追遠”則為喇叭人提供了一個安身的崇德心理。在今天喇叭苗人家中基本都有神龕,里面供著“天地君親師”及先人的位牌,以此表達喇叭人對宇宙天地、家鄉故地、父母先師的情感認同和精神皈依。
喇叭苗還有一種特別的祭祀存在,即“三洞桃源”與慶壇風俗[2]229。因喇叭人的先祖大多來自湖南西部的桃源洞一帶,他們不光是在口音上帶有湖南邵陽的湘方言,后人還專門設定一些儀式去祭祀先祖。由于族群繁衍和遷移,喇叭人離開了原本居住的地方,為了表示對先祖的“追懷”,他們用三節竹子代替祖先居住的桃源洞(此洞分為三層分別為上洞、中洞、下洞,供奉著過逝的先祖與神靈),將其打通,在內里裝入大米、黃豆、白銀等,再用五彩線裝飾裱上紅黃紙,安插在神龕處,以便在家中侍奉祖先,在對先祖與神靈的敬畏中希求他們的庇護。必要時喇叭人還會專門開慶壇儀式,在家堂屋里安立娘娘壇來納吉避兇。慶壇活動一般是以儺戲的形式再現先祖的豐功偉績及族群的遷移史。在過去他們將慶壇時間定為三年一大慶,一年一小慶,通過各種法事及重新書寫祖宗的牌位等行為來表示對先人的敬畏,對舊土的緬懷。慶壇儀式一般由專門的人來主持,喇叭人稱之為“端公”。在儀式上,端公頭戴花冠,身著法衣,主持一系列的法事,諸如有歡度小妹仙娘、采花合神、子孫為祖宗上糧等程序。無論哪種儀式,先祖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們相當于近似神的存在,子孫們通過膜拜近似于神的先祖,來有所敬畏,有所期求。喇叭人的“三洞桃源”與湖南湘西的“慶娘娘”有些類似。這種信仰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農耕民族的“追遠”和“求安定”的行為,具有準宗教性的功能與內容。他們將祖先神化,在“慎終”的過程中追懷先祖,以達到“民德歸厚”的教化功能。不過現在很少見到這種民俗活動了,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很多的民俗基本淪為一種歷史資料被保存起來。喇叭人的慶壇活動雖然成功的申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后續的傳承卻成為了一個問題。
由于當年的各種原因,遷徙過來的喇叭人一般會以血緣或是同鄉關系不離散地形成“共井”的小聚居生活空間,因而現存在的喇叭苗自然村落基本是一個姓氏,擁有著共同的祖先。喇叭人也特別喜歡修定家譜或是族譜,一來可以“慎終追遠”便于共同祭祀,以加強群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二來以此彰顯與周邊民族的不同之處。
不管是“慎終”還是“追遠”,它們在世俗當中的承載體便是“孝”。“孝”本身也是品德形成的一個基礎,可謂仁之本。在過去,統治階層強調孝治天下,利用血脈親情去維持社會的穩定性,喇叭苗的產生本就是當時社會政治的一個產物,歷經了背井離鄉的戰爭與遷徙,他們更能體會到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是何其的重要,而“追遠”的祖先情節便成為了子孫們克紹箕裘最為樸素,也是最為有效的方式。這也是一種最為鄉土的文化認同。
二、喪葬習俗:以“孝”為紐帶的“慎終”文化 祖先解決了來路問題,那么一個族群的何去何從則是一個當下之人要慎重思考的問題了。而“慎終”最好的方式則是教化,可謂“孝悌行於家,而后仁愛及於物”[1]48,以“孝”作為仁德的根本來教化民眾,這是儒家最常用的手段。喇叭苗的喪葬習俗最能體現“慎終追遠”的現實載體——“孝”。喇叭苗同本地的其他族群不一樣,他們并不主張花大量的人力物力長時間地去辦一個葬禮,他們奉行的是“喪與其易也,寧戚”[4]53,一般選擇量力而行。他們在喪葬儀式上會有一個報恩儀式,唱頌一些《報恩歌》、《孩兒祀》等報恩古文,譬如如果是女性亡故,在做法事的過程中會唱《懷胎記》,其內容如下:“正月懷胎在娘身,無蹤無影又無行,三朝一七如露水,不覺孩兒上娘身。二月懷胎在娘身,共悶眼花路難行,口中不說心里想,兒在腹內母知音。……十月懷胎在娘身,娘在房中受苦辛,兒奔生來娘胎奔死,命隔閻王一張紙。”通過對母親懷胎十月的艱辛的唱頌,一面表達對老人生養之恩的感激,一面期翼逝者生生世世安康。喇叭人在整個喪葬儀式中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悲戚的情感,他們在儀式之后還強調長時間的紀念,譬如在喇叭苗有些聚集地就規定孝子們在逝者入土為安之后還必須守孝120天,且在守孝期是不可以剃頭的,以示感懷父母的生養之恩;在老人過世的三年內,年節期間要在門上貼“孝對”即不用紅紙寫對聯,改用綠色或是黃色的紙寫對聯,以表示對逝者的緬懷,且生者在大年初一都要帶上酒肉和水果去墳頭給逝去的長輩拜年,要連拜三年。供養父母是一切善的源頭,在《孝經》中也有言,以孝來報父母之恩,這是道德教化的根本,善事父母,是愛人的基本,而愛人則是人之為仁的方式之一。這種約定俗成的喪葬風俗習慣讓他們無形地教化著后輩子孫,讓其形成一種最為淳樸的善惡觀。通過“孝”來規范小輩的行為范則,本身便是慎重的對待族群的來路,以一種最本性的方式展望族群的去路。喇叭人從孝的踐行中達到“仁”的品質,從而實現社會教化的功能,并在這個過程中強化族群的凝聚性。
當然他們仍然堅守著“質有其禮”,當“儉戚”不能夠擔當時,便要“與禮之本相近”[4]53的規則。喇叭苗特別注重墓碑文化,他們以墓碑作為“慎終”的載體,在先祖的墓志銘上詳實的記載了家族來自于哪,經歷了什么大事件,由此來教化子孫。他們將“孝”定為建立在血緣鏈條之下的倫理約束,為逝者守孝不僅僅是期盼逝者能有一個好的靈魂歸宿,更是后人對慎終追遠的倫理訴求。他們在悲慟中又充滿了希求,在追遠中思索“終”的歸宿,因為逝者是回到了祖先的懷怉,從此享受子孫的祭拜讓靈魂回歸到永生般的歸宿地,便可作為祖先神的存在而庇護子孫。喇叭人的喪葬以“稱情而立文”為旨,只有這樣才會“至痛極也”。[5]371畢竟“喪禮,衰戚之至也”[6]252其內涵也是通過喪禮將民眾的情感加以引導,使之在“衰戚”中不斷記憶過逝父母的生養之恩,不忘卻先祖的開疆之功。喇叭人將喪葬習俗由外而內,形成了敦厚樸實的民風,這在本質上是從人文角度對喇叭人的生活進行一個合宜的價值引導,在日常當中加入了道德的賦義。以此自覺培育子女對父母的感情,展現喇叭人的文化自覺,從而對整個族群的道德風華起到一定的作用。喇叭苗便是通過對先祖、父母的敬重來加強現實中各群體的聯結,最終達到一個教化的功能。因為慎終追遠的文化不是單單連通著先祖,它也連通著子孫,乃至整個家族成員,這也是中國農耕民族“齊家”文化的體現,當然這是有著相當的社會心理基礎的。在最初,喇叭苗的先祖是因戰勝了本地的仡佬族,獲取了有利的生存空間,使得他們對社會的穩定性要求更高,尋找一條具有相當穩定性的聯系紐帶。從這個現實的角度出發,早期的喇叭人不得不尋求家族的庇護、祖先的祝福,他們沿用了先齊家再談治國的套路。一個人在家里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便可立足于世了。而齊家文化的開展,其必要前提就是擁有共同祖先的家族的凝聚。“孝”便是建立在血親的生命鏈上,通過祖先、父子、子孫而達到源遠流長的目的,使大家族制社會化,這正滿足了喇叭人的需求。
中國的農耕民族習慣在追求安身的居所時也要為自己的靈魂尋找“立命”之處。“慎終追遠”的情懷則為喇叭人提供了一個共同族群所認同的情感寄托。他們能通過孝來親自體證“追遠”從而“慎終”的情感生活,在一次又一次的群體祭祀中達到一種族群的認可。由于喇叭人這種極致的故土情節,讓他們在喪葬習俗中感受了強烈的回歸心理。這種建立在共同祖先下的“追遠”文化讓他們進一步認可現世中的身份,從而“慎終”,能夠獨立于其它民族,未被本地的仡佬族或是布依族所淹滅,乃至形成了特有的族群——喇叭苗。
三、婚嫁民俗:對傳統“禮”文化的維系
婚嫁對與任何一個民族來就都是至關重要的,它代表著種族的繁衍,不僅可以從客觀上反映著當時人的精神,也可從微觀上呈示著那個時期社會的經濟、民族心理、審美意識、倫理道德、宗教觀念等諸種因素發展變演的軌痕。對喇叭苗來說,婚嫁的民俗則體現了他們對傳統儒家禮制的維系。禮義的教化只是為了引領喇叭人在社會秩序的普法性,一則是為了現下社會的可秩序性;一則是為了“追遠”自己祖先的文化。當然“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為禮之本也”[4]P53,任何“禮”都必須有 “質”的維系。雖說當年由于繁衍后代的需求,很多男子娶了當地仡佬族的女子為妻,但他們仍固執的認為自己是漢人的種,卻又在服飾上被仡佬族同化,而成為一種特別的民族。不過他們在心理上對自己的族群身份從未放棄過。這也是從文化上對族群的“始”與“終”的慎重,本就是喇叭人特別的文化心理結構。他們平時所崇尚的“禮”及倫理制度便無形中將個體、家庭凝聚在一起,從“質”上與“文”上對“禮”進行維系。所謂“人情者”無非要求大家“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 [6]618,人們的情感是人教化人的根基,禮制必然建立在人情之上,喇叭人的婚嫁習俗則體現了這點。他們傳統的婚姻習俗基本保持了遷徙過來時的特性,受到了儒家禮教的影響。嫁娶的早期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經過掛八字(又稱寫紅)、認親、挑酒(提親)、送日子、結親、發擔(接親)等程序,類似于《儀禮》當中的士昏禮,以人性情感的層次來強調家庭的價值,以規定的儀式來使婚姻符合道德的要求。譬如,他們在接親里,會用“白話詩”來表達對“禮”、“義”的維護,其中有首遞戥詩:“左拿戥來右拿坨,戥坨原來是公婆,相依為命不可缺,百年相好子登科”就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儒家的人倫情感,用戥坨來比喻公婆,以強調婚后生活的禮制。再有一首拜父母詩 “父母生身德地天,一心栽培費心田,受今兒女一素拜,萬望寬心放海涵”,在新婦進門的同時不忘父母的恩德,這是喇叭人用最直接最樸實的情懷來安正禮義人倫。姻親關系將締造一個小型的社會,如何讓這個小社會存世呢?喇叭人不談明天道,致至法,但深切的明白道德教化是為人的一種責任,要將一個族群延續下去,就得遵守先祖的禮法,保證現下社會的可秩序性,本身就是一種“慎終追遠”的態度。
早期的喇叭人不僅在婚俗的儀式上遵循禮制,在意識形態上也強調以夫家為主的婚姻觀。他們強調父系權利的重要性,主張冠夫姓,可娶外來女子為妻,但男性必須維系父系的傳統及文化,因而子孫基本能夠保持遷徙過來時的漢文化。這也是他們自認為是“漢人種”的表現。當然由于一些地域原因,喇叭苗的婚俗也有著自己的特性。譬如,他們在對戀愛對象的選擇上,傳統的喇叭人會選擇以對歌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愛戀之情。當然隨著社會的前行,人們消費觀念、價值觀念都會有所改變,喇叭苗的婚姻觀也會隨之有所變化。
婚嫁代表著他們對未來生活的展望,預意著吉祥與美好。但是無論是哪種習俗都不能缺失道德禮義的牽制,規矩之下才會有方圓。婚嫁習俗是喇叭人文化的一種鏡像,通過它可以折射出族群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喇叭人的婚俗是通過對昏士儀式的保存來展現出對族群繁衍的重視,把家族價值放置于人性情感之中,并以此作為教育的方式來維系禮文化及寄托他們的倫理價值觀念。正因為喇叭人對“慎終追遠”文化的堅持,才得以確認自己族群的存在,并為自己的群體確定方向和意義。
四、結語
孔子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1]106,當年的喇叭人沒法選擇不入危、亂之地,只能依靠自己的雙手去建設。他們用幾代人的心血在屯兵戰略之后開辟出一處風俗仁厚的“里仁”之處來安身,這同他們本身所帶來的漢文化及他們所受的人文教化是不可分割的。“慎終追遠”的文化讓他們“本立”從而“道生”[1]48,孝悌的血緣親情成為樸素社會秩序的一個基石。他們也將這種精神往外推衍,喇叭人深知“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5]592他們追懷先祖,卻也慎重地對待子孫,喇叭苗歷來注重以“禮”教化后輩,以一種樸素的方式承擔著“詩禮傳家”的傳統。雖然地域偏僻,甚至可稱之為貧困,但喇叭人從來不放棄受教育的機會,這是喇叭苗與周邊其它苗族、彝族的一個最大差別。一個傳統喇叭人聚集的村寨,后輩年青人大都是依靠讀書而出人頭地。一旦離開村寨,喇叭苗亦十分重視反哺生養之恩,在喇叭苗的村寨都會花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去修撰族譜強調家風家訓,在“追遠”的過程中不忘來路,不忘感恩,從而在“慎終”中不忘教化,以達到“民德歸厚”的狀態。
但在今日之中國,很多地方的農村正經歷著一種自然原初文化的迷失過程,社會的變遷、現代化的轉型一直在破壞和解構鄉村文化。鄉村文化無非是村民們自然形成的風俗、生產方式等等,而現代化的進程讓原本自然而成的主體不知道如何自處,喪失了個性的主體,文化便無載體可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面臨著“體”“用”的自處,因為在很多時候人們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何以為“體”何以為“用”。一種喪失了“體”之源的文化,勢必會導致無以為“用”現象的出現。一些民間的文化習俗或是傳統要么就寄放在博物館成為純學術緬懷的對象;要么則淪為經濟的婢女,變成無根、無本的存在。貴州喇叭苗的文化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當現代化的元素打開通向外面的大門時,他們開始向往外面的生活,這種過渡直接導致了文化之“體”的淪喪,在一些自然的民族村落里甚至形成一種文化的真空地帶,年青的喇叭苗并無多少民族文化上的自覺,很多民眾也開始漸漸忘卻自己的來路,心靈緬懷的對象顯得蒼白無力。他們世代堅持的文化并沒有形成一種與時俱進的自覺,很多地方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態度呈現出一種放任自流的消極無為狀。喇叭苗文化的源頭正是其文化的“體”,只要能繼續“慎終”的“追遠”,獨特的喇叭人必能夠為其文化的“用”尋找到有力的支撐,并將其文化踵武賡續,讓它以一種新的形態延續下去。
參考文獻:
[1]〔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杜文鐸,等點校.黔南識略·黔南職方紀略[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3]楊傳溥.貴州府縣志輯.民國普安志[M].巴蜀書社·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2006:553.
[4]劉寶楠.諸子集成:論語正義·八佾第三[M].長沙:岳麓書社,1996.
[5]〔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荀子·禮論[M].北京:中華書局,1988.
[6]〔清〕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