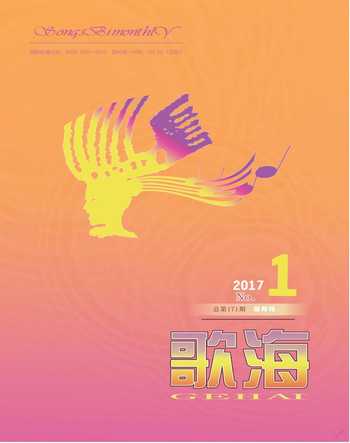施尼特凱“復風格”作品中的微復調技法
李鵬程 哈靜
[摘 要]微復調原本是利蓋蒂在20世紀60年代初首先運用的一種復調織體,作為他的同時代人,施尼特凱迅速將這一技法吸收到自己的“復風格”作品中來,不僅豐富了自己多元拼貼的手法,還發展了微復調的運用方式。通過介紹施尼特凱對微復調技法的接受過程以及他對利蓋蒂微復調技法的分析,最后舉例論述施尼特凱是如何將這一技法融匯到自己的音樂語言中來的。
[關鍵詞]施尼特凱;微復調;技術特點;復風格
施尼特凱(Alfred Garriyevich Schnittke,1934-1998)是20世紀下半葉廣受歡迎的作曲家,這個生于蘇聯卻沒有絲毫俄羅斯血統(其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德國人)的漂泊者先后在蘇聯和德國定居,因此常被后人形容為“a man in between”(位于……之間的人)①。作為一個有著多元文化背景的作曲家,施尼特凱在20世紀70年代前后創作出了一批廣受歡迎的“復風格”音樂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古典與現代、嚴肅與流行、調性與非調性、崇高與卑瑣等很多對立風格被融為一體,其中運用的作曲技法也不拘一格。為了提高音樂的表現性效果,施尼特凱自由地運用了一些現代音樂技法,“微復調”即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種。
微復調作為一種重要的現代作曲技法,一般認為是經過利蓋蒂的運用后才真正形成,它不論是在樂譜視覺上還是音響聽覺上,都達到了比任何傳統復調織體更加“宏大”的效果。陳鴻鐸教授總結利蓋蒂的微復調技法具有以下幾個典型特征:1. 建立在模仿復調基礎上,先行聲部與模仿聲部常常同時進入;2. 聲部劃分微小到以單件樂器為單位;3. 各聲部均有旋律性的運動,但旋律的進行基本上限于狹窄的音程范圍內;4. 縱向上結合距離保持在二度以內,整個織體構成一個密集網狀;5. 節奏上每一個聲部都有極細微的差異。②
施尼特凱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對利蓋蒂的微復調技法進行深入研究,并迅速將這一技法運用到自己的音樂中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將微復調這種特殊的織體形態融入到“復風格”音樂中的同時,施尼特凱也拓展了這種新技法的運用方式,在具體運用中體現了鮮明的個人特點。本文將首先介紹施尼特凱對微復調技法的吸收歷程,然后舉出四部“復風格”作品的片段作為典型例證,從中看到施尼特凱是如何在不同語境中靈活運用這一技法的。
一、接受過程
1953年,施尼特凱正式進入莫斯科音樂學院,盡管學院當時奉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美學方針,但施尼特凱常私下和同學交流現代音樂作品。同樣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這個重要的歷史拐點不僅讓施尼特凱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西方現代音樂,還預示著他將伴隨著一場“解凍”,形成自己的創作理念。
得益于赫魯曉夫的“解凍”政策,1956—1964年間很多現代音樂錄音和總譜出現在蘇聯,施尼特凱如饑似渴地分析了韋伯恩、施托克豪森、諾諾、利蓋蒂等西方同時代作曲家的作品,由此開始了一系列的序列音樂創作——如《第一小提琴奏鳴曲》《鋼琴和室內管弦樂曲》等均是以序列原則為基礎寫成的。但施尼特凱漸漸發現序列的預設程序過于理性,作品的一切“秘密”都能夠被仔細分析出來,而他認為生命的過程是不可預測的,序列音樂是沒有“繁殖”能力的,因此他逐漸放棄了以序列來結構樂曲的手法。
盡管如此,早年對西歐現代作曲技法的研究和借鑒,現在看來是施尼特凱“復風格”寫作的必經之路——因為他首先要熟練掌握各種風格,才能將它們熔于一爐。如他自己所說:“在現代專業作曲家的技法手段儲備中‘莫扎特的部分約占1/4。第二個1/4是19世紀的‘技術手段。第三個1/4是20世紀的新技術。第四個1/4是非歐洲音樂傳統的技術類型。現代作曲家必須掌握所有這些豐富的手法、風格和‘語言。”①
施尼特凱在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期間(1961—1971),不僅帶領學生分析了大量當代音樂作品,還寫出了不少堪稱“精美”的現代音樂分析文章,其中就包括對利蓋蒂微復調技法的分析。施尼特凱在1970年分析了利蓋蒂的管弦樂作品《遠方》(Lontano),遂寫出《利蓋蒂的樂隊微復調織體》(Ligetis Orchestral Micropolyphony)一文,以他一貫精確的文字揭示出這部作品的奧妙所在:
“這部作品特殊的標題準確地表達了利蓋蒂的想法和技術手段。宛如一個遠方的幻影,這種頗富浪漫色彩的音樂將聽者籠罩在一張極其精致的音響網中。有時它們漸漸清晰起來,集中成一道耀眼的光束、鑄成一個奇跡,但在最后一刻,金色光環還是褪去了,消逝在迷霧中……這張極其精致的音響網實際上是由一條單旋律線條編織起來的。這部作品的微復調織體由嚴格的多聲部卡農構成,人耳難以分辨其組成部分。”②
而后,施尼特凱詳細分析了《遠方》中微復調卡農的發展歷程,并列出一張分析圖式③:
最后,施尼特凱對利蓋蒂運用微復調的根本目的進行了總結:
“利蓋蒂發明了一種擁有大量模仿聲部的復調音樂,其結構是在各個層面的精確計算中產生的。正如那些序列主義作品一樣,節奏、音色和力度從結構上被整體控制,不同的是這些要素不是以序列為基礎(即當作一個“生命公式”來看待),而是以一套理智的方法為基礎,從而盡可能地表現詩意的構思。對于利蓋蒂來說,作曲不是源于對形式的計算,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音響印象上——這是作曲家意圖的神奇顯現,它存在于作曲家的想象中并急切地想要表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技術以它全部的理性,只是實現這一音響幻想的手段,而不是構建音樂建筑的工具。兩個相對立的要素以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矛盾方式相互影響著:超越現實的詩意風格,以及精確到圖表式的結構邏輯。”①
施尼特凱和利蓋蒂的創作理念可以說是不謀而合的,即作曲技術不僅是對形式的計算,更重要的是實現音響印象的手段。20世紀80年代前后,施尼特凱在自己的“復風格”作品中創造性運用了這種精密的音樂織體,往往與其他手法相結合,出現在樂曲的重要位置,成為表現特定風格的恰當載體。
二、具體運用
(一)與核心音組結合
施尼特凱偏愛以半音列作為樂曲的核心音高材料,他的《鋼琴五重奏》《第一大提琴奏鳴曲》《第三鋼琴奏鳴曲》等均是以半音列作為樂曲的核心材料。施尼特凱的《第二弦樂四重奏》(1980)為紀念車禍身亡的導演拉薩莉·舍普琴科而作,第一樂章便是由一個半音化的四音組發展而成,核心音級集合為4-1[0123],它同時也是構成樂曲微復調織體的核心音組。
樂曲一開始便以微復調的織體呈示出這個四音組,微復調的運用使得樂曲開篇有一種獨特的神秘感:第一小提琴半音上行奏出四音組,下三個聲部則以相隔一拍的方式進行相隔小九度的卡農模仿,如果將縱向的四個音置于一個八度內,則是與橫向半音上行四音組呈反向進行的半音下行四音組G-#F-F-E。由此產生了類似于“多米諾骨牌”的連鎖效應,配以弱力度和泛音奏法,整塊音響在靜止中隱現微妙的強弱張力。
第二句的旋律依然始于半音上行四音組,同樣是相隔一拍的卡農模仿,但縱向四個音在八度內形成的卻是#F-G-#G-A的上行四音組,由此在縱向上,音域雖然在下降,音級卻在半音化地升高(如譜例中雙箭頭所示)。由于節拍的錯位,并未出現同度齊奏的音響,non vibr(不得揉弦)這一特殊的演奏法也適時地營造了一個趨于靜止的塊狀音響。核心音級集合4-1[0123]貫穿在這一段微復調織體中,直至最后的終止和弦。
弦樂四重奏因為聲部線條相對明晰,似乎難以在其中運用微復調技法。此例具備了動態化的密集音塊織體這一微復調的基本特征,通過橫向與縱向連續半音化的卡農模仿,配合特殊的演奏法和表情,以密集卡農技術形成了動態音塊織體,并且與作品的核心音組相結合,真正體現了微型復調的“微”(Micro)字,可謂“螺螄殼里做道場”。
(二)與多主題對位結合
主題對位作為一種傳統的復調技法常被用于音樂的高潮處,但將幾個風格各異的音樂主題在自身構成微復調織體的情況下同時對位,在施尼特凱之前尚無人嘗試。他的《第一大協奏曲》(1977)將原屬于不同時空的音樂主題熔為一爐,特別是第五樂章依次回顧了全曲各主要風格的主題,并在高潮處對位結合,劉永平教授稱之為“同位復卡農組微復調”,即在微型復調中采用不同音列構成的兩個或多個單卡農組以相同的結構位置作縱向疊置。②
施尼特凱的《第一大協奏曲》第五樂章“回旋曲”對全曲具有總結性意義,全曲各種風格的主題在樂章的黃金分割點上作對位結合,將音樂推向高潮:回旋曲主題(二聲部卡農)與之前樂章出現過的探戈主題(六聲部卡農)、托卡塔主題(六聲部卡農)、內心主題(四聲部卡農)、托卡塔第一插部主題(四聲部卡農)自身內部分別構成微復調織體,而這些主題又在縱向上同時結合,由此形成了類似于“宏復調”的龐大織體結構。盡管每個主題原本性格鮮明,但由于施尼特凱再次運用了上例提過的連續半音下行模仿,所以各主題的原有風格已被扭曲變形,這也是施尼特凱音樂所特有的荒誕性。經過一個高潮式的連接句后,第一樂章的“時鐘”主題再次由預制鋼琴奏出,這場群魔亂舞隨之戛然而止。
在如此“狹小”的片段內展現如此之廣的風格、表現如此之深的情感,微復調也是再恰當不過的織體了。如果說《第二弦樂四重奏》中對半音下行卡農的運用還只是以靜態渲染氣氛的話,那么這里各主題自身的半音化微復調則以微妙的動態向我們展現了在這樣一個微觀世界中,可以容納多少音樂風格。
此外,這部《第一大協奏曲》的第二樂章“托卡塔”開篇便是由細分成12個聲部的小提琴演奏的“單卡農組”微復調,巴洛克風格的主題旋律(即譜例2中的托卡塔主題)在微復調織體中衍生出了現代性的音樂風格。通過這部作品可以看出,施尼特凱對微復調的運用不僅僅是制造宏大的音響效果,更多時候是作為特定音樂風格的載體而存在的。
(三)與引用手法結合
施尼特凱對馬勒16歲時創作的《a小調鋼琴四重奏》極為著迷,并以一種紀念而非解構的姿態對待這份遺產:“我努力了幾年時間,來尋找一種續寫馬勒這個樂思的方式。后來我想作為馬勒音樂的延續并不可行,而作為一種靠近馬勒音樂的音樂——暗示手法的運用,的確是可行的,因此終于找到了出路。起初是一種紀念的嘗試,后來成為了紀念本身了。”①
施尼特凱曾指出引用手法包括再現另一時代或另一民族的特征元素(諸如旋律音調、和聲連接、終止式)以及改編性的引用。②他于1988年以馬勒四重奏第二樂章的草稿為基礎寫出了《鋼琴四重奏》,并以這部《鋼琴四重奏》為基礎發展成了《第四大協奏曲》(1988)的第二樂章。馬勒原先的主題、和聲、織體等諸多要素都被再次引用在這里,它們在古老體裁與現代技法的融合中得以涅槃重生。
施尼特凱將馬勒四重奏中伴奏音型作為《第四大協奏曲》第二樂章的引子材料,在羽管鍵琴的點綴下以微復調的織體形態鋪陳開來:弦樂組被細分成7個聲部,依次演奏這個十六分音符回繞流動的音型。值得注意的是,依次出現聲部的和聲材料與馬勒原型中依次出現的和聲進行是一致的,但在這里所有的和聲逐漸在縱向上交織在一起,流動的密集和弦形成了模糊的音塊,隨著力度的漸強音響逐漸尖銳,形成了施尼特凱音樂特有的混亂音響,同時馬勒音樂所代表的晚期浪漫主義符號在現代音樂的組織中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通過這個例子,我們看到了施尼特凱引用手法的多樣性和隱蔽性,同時也領略了作曲家對微復調技法的運用之純熟。施尼特凱將馬勒音樂的音型與和聲幾乎是原樣搬了過來,然而通過微復調織體疊加所造成的迷離效果,卻極具施尼特凱個人特色,同時也是這部作品所需要的。
(四)與十二音主題結合
在施尼特凱的“復風格”作品中,十二音主題常常作為現代音樂的象征,與傳統的調性旋律并置對比。在《為鋼琴與弦樂而作的協奏曲》(1979)這部作品中,施尼特凱運用了傳統調性(實為多調性)的動機模進手法與自由無調性段落相對置,深沉冥想的鋼琴聲部與躁動不安的弦樂聲部持續抗衡,音樂情緒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搖擺。直至全曲的尾聲,十二音原型才以一種特殊的織體組合方式露出廬山真面目,鋼琴在極高音區奏出十二音主題,弦樂組則隨之形成了密集卡農式的網狀織體——以大提琴為低音,小提琴被分成12個聲部,每一聲部隨著鋼琴彈出的十二音依次疊加,最后所有聲部形成一個十二音密集和弦,全曲在微弱精致的音響中結束。
這個具有調性因素的十二音主題由四個3音2號集合構成,其微小的音程距離恰好符合微復調對音高關系的要求;主題從句法和音高上,可以從中間均分為二,弦樂組的微復調音響也隨之被一分為兩個層次,整體最終形成一個多層次聚合的十二音微復調織體。
將十二音主題置于這樣一個微復調音響網,這是施尼特凱對微復調織體的創造性運用。由于微復調織體的音高組織與十二音主題旋律相一致,所以各聲部也不再像典型的微復調那樣呈現出一定的旋律化運動形態,但它依然符合聲部關系對比微小、旨在追求整體效果的音響綜合體這樣的廣義概念。此外,與傳統微復調織體為了追求整體化的音色而使用同一組樂器頗為不同的是,此例的微復調織體是由三種樂器共同組成的——大提琴在超低音區烘托,小提琴在中音區形成微復調主體,鋼琴則是演奏十二音主題的主體。這樣的組合使得音響更加豐滿真實,卻仍不失微復調織體特有的吊詭之感。
三、結語
本文僅挑出四個具有代表性的例證來說明施尼特凱對微復調織體的創造性運用,除此之外,他在其他多部作品中也各富特色地運用了微復調織體,如《第三大協奏曲》《第三交響曲》《極弱》等,在此不贅。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利蓋蒂是微復調技法的首創者,但這并不意味微復調的概念只能依照他的運用方式而定,更不意味著后人在運用微復調進行創作時只能模仿他的典型做法。微復調的運用方式一直在發展,其概念也尚未定型。它開辟了一條嶄新的聲部結構途徑,具體如何運用和界定,要視創作意圖和音響效果而定。
施尼特凱對微復調織體的運用是靈活多變的,拓展了微復調的運用方式,以至于有人感嘆:“雖然這種技法并非施尼特凱首創,但他的運用已成為微復調的典范。”①施尼特凱對現代技法的任何發展都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源于對作品內在表現性效果的需要。他將微復調技法與其“復風格”創作思維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在這樣一個微觀世界里實現了自己的多元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