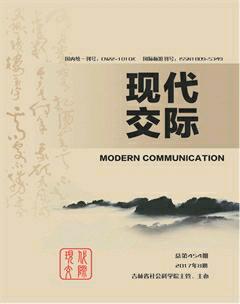“本土資源”的借鑒與吸收
吳香蕓
摘要:許多法學家主張進行法律改革,從外國“移植”法律制度。《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的作者蘇力卻主張“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利用中國本土的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法律的改革發展必須像樹木一樣把“根”深扎進我們生長的土壤里,尊重傳統,根據人們真實需求而制定,而不是靠政府強制力來推行。只有真正在理解社會的基礎上制定的法律才是適應社會的法律。
關鍵詞:蘇力 法治改革 “本土資源” 借鑒吸收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8-0053-01
一、為什么要借助本土資源
沒有憑空而來的言論主張,許多主張都必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在對我國許多法學學者提出的“變法”模式存在懷疑的基礎上,蘇力提出了要利用本土資源,注重傳統走法治改革發展之路的觀點,并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證明了借助本土資源的科學性。
(一)歷史的經驗
歷史有的時候像機器一樣在“復制粘貼”,會有一種驚人的相似度,當然也可以把這種相似理解為規律。正是基于這種規律,過往的歷史能給后世以一定的經驗借鑒,倘若歷史每一片斷都是全新的,那么傳承的必要性就會下降很多。法律制度的建構發展也是如此,正如作者在書中展示的例子一樣,西方的很多國家都是在依據本土資源發展適合本國的法律制度。
歷史的每一個腳步都是有選擇的,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所選擇的是最有利于自己發展的,選擇了自己最愿意相信的。因此習慣的傳承可以理解為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尊重傳統,因為只有那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現今社會的運作規則的背景和內涵,在考量“本土資源”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法律才是適應社會的,而不是“逆”人們對法律的期望去發展。
(二)法律的功能
說起法律的功能,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刑法那種懲罰性非常嚴厲的部門法,借助那樣的法律制度構建起一種社會秩序。作者在書中這樣分析到,“我們的任何社會活動都建立在一大串我們認為比較確定的預期上,而法律以及其他各種在功能上起作用的規則(習慣、慣例),就在許多領域保證著這個世界不會突然改換模樣,不會失去我們賦予其的意義。”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得很多東西日新月異,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能接受這不太穩定和確定的生活,這樣不確定的思緒會讓很多人陷入一種迷茫與焦慮之中。
因此制度的建立應該是給人一種確定的方向感,也只有那樣才適應人們的需要,人們才會去接受它。而經過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篩選下來的習慣傳統則在這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人們習慣了這些規則的存在,會在發生問題時下意識地運用這些規則,比如鄰里之間的調解協商。
當然現代社會的法治發展決不能完全依靠過往的習慣傳統,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過去的東西總會不適應現今的社會。因此我們既需要習慣規則的存在,同時也需要國家制定法律的出臺,在一個更大的區域范圍內需要建立一種統一的法律制度,就像羅馬帝國的“萬民法”一樣。
二、如何借鑒本土資源
(一)理解中國社會
農村的發展落后于其他地區,社會的許多發展變化都不能離開這個現實背景,農民的數量仍占據很大的比例,要倡導法治社會,必須要考慮什么是農村社會,在農村社會維持發展的規則體系能否為現代法律所吸收借鑒。
當人們賴以維持生活的秩序機制被打破的時候,當國家強制力推行這種大部分按照西方學說觀點而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的時候,必然會使其與中國傳統社會運作的規則體系相沖突。
因此無論是強調市場經濟的商法、經濟法,強調個人權利義務的民法,還是強調程序的訴訟法、仲裁法,都應該立足于中國社會,從歷史、從現實去考慮中國的經濟、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東西,只有那樣法律才不是一紙空文,才不是孤立的零散的。體系化的法律必然是與社會體系相適應的。
(二)經驗借鑒與積累
在改革開放的潮流中走進市場經濟,必定可以從改革中積累出很多經驗。中國的法治建設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需要不斷地實踐摸索總結,因為一項制度的發展絕對不是靠人的大腦想出來的,而是走出來的。
作者在書中列舉了農村和城市不同的區域改革經驗,發現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歷史上一家一戶的農業經濟制度有很多相似之處;蘇南地區迅速發展的鄉鎮企業除了其他地緣和文化因素,還有先前公社制下出現的社隊企業。因此可以看出,成功的經驗背后都有著對以往經驗的借鑒,長期實踐過的東西也許是最容易產生生命力的。
但是強調本土資源并不是說就得放棄借鑒西方的法律制度,在現今的開放世界,只專注于本國自身的制度發展變革,很容易形成一種閉塞的,為外人所不理解的制度,而這顯然不能滿足中外交流日漸頻繁的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法治的發展需要“移植”,需要在理解中國的社會以及西方法律結構、文化的基礎上移植。
參考文獻:
[1]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2]費孝通.行行重行行[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
[3]薩拜因(美).政治學說史(下冊)[M].劉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