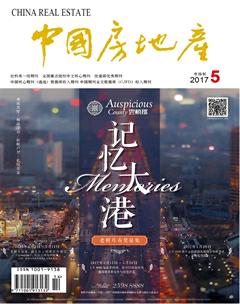萬科是如何做法務管理的
張偉
一、現狀
應該說作為一家具有30多年歷史的公司,萬科的整體管理水平還不錯。每年萬科的案件數量就是幾百件,2014、2015、2016年三年銷售收入大幅增長,但案件數量卻在下降。整個集團有將近130個專職法務,是一支精干的隊伍。萬科集團的大部分案件是與房屋銷售有關系的,占比70%多,就數量來講呈現出典型的行業特征,每當地產行業價格停滯或者下降或者國家對地產行業進行宏觀調控時,訴訟就增多。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現在市場上有一些投資客,價格一停漲,他們就要鬧退房;二是每當市場下行的時候,地產商通常會選擇快速去庫存,有時候會降價銷售,一降價銷售肯定會引起糾紛,有些老業主會砸售樓處、拉橫幅、去法院起訴,這也是他們“維權”的一種方式。
從訴訟案件標的額來看,合作并購項目占大頭。這和萬科自身拿地的方式有很大關系,因為萬科在公開市場上很少拿地.萬科70%的土地都是來自于并購、合資合作,甚至來自于破產重整。由于拿地的方式非常復雜,也就容易引起糾紛,尤其在市場上行的時候,并購、合資合作項目容易產生糾紛。所以說,地產行業有明顯的周期性,宏觀調控一來,業主就來鬧事;市場一上行,合作方就不愿意履行合同,基本上就是這么一個范式。反倒萬科和供應商的關系很好,這么多年很少發生糾紛。這是因為萬科注重保護利益相關者,萬科的理念是“為普通人蓋好房子”,與合作方之間建立和維持更加合理的利益結構。
二、新常態
2015、2016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又經歷了一輪上漲,但開發商并不是房價上漲的唯一既得利益者。以深圳為例,比如深圳賣掉10萬的房子,有6、7萬是土地成本,將近有1萬多是稅,即便管理水平比較高的萬科,集中采購建造成本大概控制在5000元以內,也只剩下1萬是萬科的利潤。事實上,從優秀的地產商角度看,并不希望房價過快上漲,因為只有在房價穩定的時候,才能顯示出管理水平的優勢,才能在競爭中勝出。萬科的管理水平高,可以因此拿到更多的市場份額。房價快速上漲的時候,誰都能做房地產,反而顯示不出我們的能力和水平。
新常態下也帶來一些新現象和新問題。未來整個市場占有率會越來越向大房企集中,目前排名前100名的地產商在整個市場中的占有率剛超過50%。在地產新常態下,可以預見行業集中度會快速上升,像萬科這樣的大型地產商應該能實現逆勢規模擴張,占據更高的市場占有率。當然,新常態下,地產行業的利潤率會下降,業務的容錯度也會下降,這就需要更加精細化的管理,對法務而言更是如此。
第一,組織結構滯后于業務發展,法務人員配置不足,層級不高。一線公司法務大多隸屬于投資乃至人力部門,比較孤單,沒有形成很好的體系,沒有形成很好的專業分工。
第二,在市場上行的時候,基本上拿一塊地就賺點錢,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大家對于風險的意識也沒有那么高,風控部門在業務鏈條中的參與,其實是不夠的,項目前端的工作法務參與得少。合作項目發生訴訟問題,很大程度上與內部法務參與的環節缺失有關系。
第三,人手比較短缺,集團內統一的風險檢查很難實施。
三、應對舉措
新常態對法務工作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從廣度上來講,要求全方位的參與具體業務,要更加深耕細作。
1.在組織機構上要升級
原來萬科由集團總部直接對接60-70家一線公司,導致總部的法務力量力不從心。過去一年,萬科對法務組織架構進行了重構,在四大區域基本上建立了法務組織,在有條件的大型一線公司建立了法務部,現在大的一線公司法務人員比集團總部法務部還多,這才是比較合理的結構。
2.在管理模式上盡可能地做到風控前置
具體來講,法務要從拿地就開始介入。正如扁鵲三兄弟,“長兄治未病、次兄治病于初起”,扁鵲的名聲最大,但扁鵲自認醫術是最差的。萬科的目標是治未病,強身健體更重要,盡可能不訴訟。
3.內部制度規范要升級
在管理模式上,盡可能往前置,走到風控的前端去,風控要到業務的前端來。從訴訟管理的機制上來講,以前更多的是事后救濟,現在要把基礎工作做實,通過一系列的舉措,從組織機構建設到能力提升到開展一些專項行動到過程中的支持,包括訴訟的爭議解決、復盤、管理改進等一系列行動,變成一個閉環的結構。很多涉及風險的事,以前業務部門是自己單干,現在要有所約束、有所幫助。
4.爭議解決方式:選擇之困——訴訟 VS仲裁
最后還面臨一個問題,爭議解決是選擇訴訟還是仲裁?傳統上講,大家普遍認為國內的司法環境不完美,訴訟兩審終審、終審之后還可以再申訴,沒完沒了,而仲裁一審終局,很簡單,所以大家覺得選擇仲裁更好。但是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讓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命題。
萬科在深圳有一個案子,合同約定是仲裁,雙方各選擇一個仲裁員。仲裁庭組成之后,對方就換了律師。經調查發現,這個首裁一直在對方律師主導的一個商業機構中當顧問。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按道理首裁和對方律師有商業上的往來,就應該回避。所以我們提出要求首裁回避,但是仲裁機構覺得很難。
這是挺麻煩的一件事,因為我們依法主張首裁回避,但是仲裁機構不愿意表態,怎么辦?如果程序就這么莫名其妙地進行下去,對我們來講也許兇多吉少。而如果看合同、看證據,那么法律人可以判斷我方不贏是沒道理的。所以重新審視爭議解決機構,發現挺不簡單的,今后是不是要選擇仲裁進行爭議解決,可能還要再掂量掂量。
作者系萬科集團法務部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