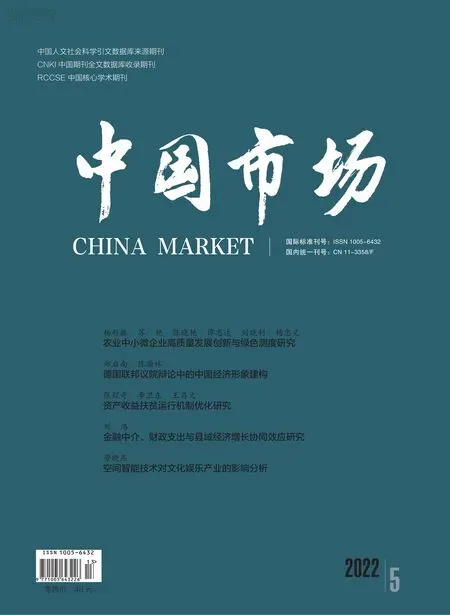《大司命》《少司命》的唱和之情
[摘要]《大司命》《少司命》是屈原《九歌》中的兩篇,其中大司命是主掌死亡壽夭的神,少司命是主掌子嗣的神,《九歌》雖然是屬于祭祀,但這兩篇的篇章中又多描寫大司命與少司命的感情之好與離別的愁苦,其中也摻雜了屈原離開楚王身邊,自己的志向抱負得不到實現的哀愁,即這兩篇不僅僅是祭歌,也是屈原個人情感的體現。
[關鍵詞]大司命;少司命;職責;祭歌;屈原
《大司命》《少司命》是屈原《九歌》中的相對的兩篇。與《九歌》一組其他篇章一樣,是用于祭神的祭歌。《九歌》是在夏代就存在的樂歌。
雖然“司命”這一名字是在古籍文獻中出現得比較多,大司命是主生死,而少司命是主兒童命運的神,但是屈原所作的《大司命》《少司命》篇章中的實際內容卻與生死或是送子之間的關系比較少,主要是在文中也提到了他們之間的情感等內容,因此可以說他們的篇名與內容之間有各自的獨立性。洪興祖《楚辭補注》中指出了這一點:“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于篇后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宋)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57.即指出《九歌》篇名的命名這并非是屈原本人所為,因此在內容上與篇名上可能會對應不起來。
《大司命》《少司命》雖屬于《九歌》祭神的一組詩中的兩篇,但其中表達的意思卻不僅僅是祭神,在篇章中又蘊含著男女之情。大司命是主壽夭、少司命主幼艾,這是已經基本形成共識的了,而根據篇章中所表達出來的意思,大司命操縱人的壽命長短,可以說是掌管著“死”,而少司命的職責是主子嗣,從某種方面上來說也是“生”的意思,即大司命、少司命是一對掌管生死關系的相對的神。
在《大司命》《少司命》性質的問題上,還涉及《九歌》寫作的時間,王逸認為是作于屈原流放之后,篇章中流露出的是慘遭放逐的憂愁哀思,但是現代研究學者多認為《九歌》是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前,其內容中所流露出來的,也多壯志、正是政治得意時期的感情流露。即無論是從哪一方面看,也是包含著屈原個人的情思。
從內容上來分析,《九歌》的中每一篇章中表達的東西與《詩經》有很大的不同,《詩經》中的《國風》篇章中有描寫男女情思的詩,但是頌歌中卻常常僅僅描繪祝頌場面等,而不包括男女感情在內。因此,《大司命》《少司命》兩篇所展現出來的,并不僅僅是作為祭歌的內容,也是屈原個人情感的表達。
《大司命》中,從“吾”“君”“女”二字可以看出,是大司命少司命的唱和之辭。《大司命》開篇說:“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大司命所唱的,是說他從“天門”中出來,旋風開路,暴雨洗滌塵埃。這即是說明了大司命的神的身份,以及其出門的排場之大,正是其本身權力和地位的象征,由此理解,不免有當時屈原正處于政治得意時期的情感。“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從女。”這是少司命所吟詠的,是少司命去追隨大司命的腳步,“生死相隨”,可見二人的情義之深。接下來的“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則是說在廣大的天下中,人壽長短都操縱在他的手中,是其職責的體現,也是大司命主生命長短的證據。“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一句說的是執行具體的任務,也可以看出,“吾”是大司命自稱的詞,而“君”是大司命稱少司命的稱呼。又之后的:“一陰兮一陽,眾莫知兮余所為。”也是大司命自己所唱。表達著他去拿走別人性命的行為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人知道的。“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何為?”在這里的文辭主要所表達的感情就是兩個人的綿綿情義與不忍離別,講思念所帶來的憂愁,是大司命與少司命情感的描寫。其中憂愁的成分如是屈原個人情感的表達,是屈原被疏遠之后,仍舊在原地徘徊而不愿離去,希望能夠保持像當年一樣為楚國效力,希望楚王能夠顧念舊情,重新啟用自己,最后一句則類似于屈原自己安慰,生死有命,而自己遠離朝廷,怕也是命運吧,這么說則是被放逐之后所作的證據了。
再看《少司命》這一篇,也是有著二人唱和的成分。“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是寫景物,其中秋天的植物,結滿果實,也是有著子孫等的象征之感。同時暗示了少司命的職責。“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其中“蓀”字是少司命的自稱之辭。“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這一句是說大司命獨與自己有情,如是屈原本身感情的移入,則更像是說屈原在朝廷內獨受重用。“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云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又是寫到了離別的凄苦,來去迅速離去,忽然而已,兩個人因為各自有職責所在而常常見面不多。“與女沐兮咸池,晞女發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則是大司命所說的,與少司命許下的情感的誓言。屈原則可以想到當年受到重用時候的景象。但是少司命自身也很忙,“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當時認為彗星會帶來災害,因此“撫彗星”,就有著驅逐災害的意思,在最后一句也很明顯地指出了少司命與兒童有關的職責。按屈原的情感來說,則仍舊是表達了自己想要回到楚王身邊,繼續為國效力,使楚國繁盛的思想。
綜合《大司命》《少司命》二者,兩人的職責是關乎生死的,一個主死,一個主生,看似是兩個極端,但是生死本身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以時間變化的迅速而言,萬物每一刻都是生死相接的,生死二事合于自然法則,大司命以其力量昭示著死的威嚴,而少司命則以桂枝等捍衛生命的力量。這是先秦時代生死觀念的體現,生死本是不能相互分離的,不僅僅是要為“生”來祈禱祭祀,“死”同樣也是強大的力量,是人類面對自然規律的崇拜。
這兩首也不僅僅是司命職責的體現,同時,二者雖然是司命,但是也是有著常人的情感,是一對“生死之戀”,相互追隨著彼此,在一見鐘情之后,既有尋常于“咸池”享受的樂趣,也會有離別的哀傷之情,具體情感之深更體現在他們言語中的相互唱和、別后相思之上。其中也體現了濃郁的巫文化的特色,作品中也涉及了楚地地域的特色。
而與屈原感情的關系上,這兩篇之間所體現出來的感情可以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有不少歡愉享樂的成分,以及權力之威盛、出行場面之大,與受到楚王重用時候的得意之情。但是后半部分則更接近于憂愁,兩篇之中的后半部分不斷抒發著離別的愁苦,更像是作于屈原被流放之后,屈原仍舊希望能夠回到楚王身邊去幫助他,同時也實現自己的政治愿望。除了這兩篇之外,在《九歌》的其他篇章中也有不少涉及愛情,而這些愛情也往往包含了無望的成分,類似于以女子比喻自己,而抒發自己的失志之痛與被驅趕出朝廷的悲傷。
可以說《九歌》是屈原在祭祀中見到了樂舞,又結合自己的情感所作的。
《大司命》與《少司命》這兩篇,是祭祀之篇章而又不僅僅限于祭祀之中,它們是楚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體現,也是當時祭祀風貌的體現,篇中著重描寫了兩個司命的情感,《九歌》篇章更是屈原個人感情借以抒發的途徑。
參考文獻:
[1](明)王夫之楚辭通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宋)洪興祖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清)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4](宋)朱熹楚辭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唐夢瑤(1995—),女,山東濰坊人,現就讀于鄭州大學歷史學院人文科學實驗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