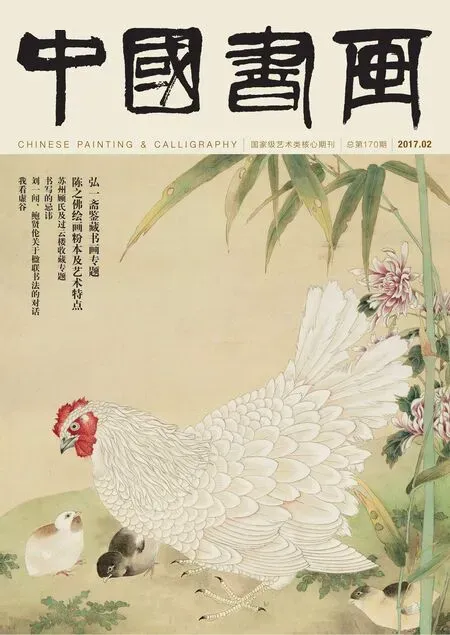書對話聯
——關于楹聯書法的對話
◇ 劉一聞 鮑賢倫
書對話聯
——關于楹聯書法的對話
◇ 劉一聞 鮑賢倫

以上組圖為秦皇島山海關“閑庭”對話現場

鮑賢倫 隸書永遇相見三言聯 131cm×31cm×2 紙本 2016年
趣話對聯與書法
劉一聞(以下簡稱劉):今天大家一起來討論對聯書法很有意義。其實對聯書法的出現和發展,主要是在清代。為什么清代會促使對聯書法的興起和蓬勃發展呢?這跟當時的“文字獄”相關。“文字獄”的發生,使原本其他領域的一些學者,紛紛轉向了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純粹學術領域。加上彼時地下出土日多,活躍于乾嘉時期的以研究小學及考據之學,并以闡述儒學經典為宗的所謂乾嘉學派應運而生。在當時那個學術氛圍之下,使專心于文字形態研究的人們,逐漸對字體本身由用筆、結體而生的視覺之美產生了興趣,于是嘗試著把這種美感實踐于書法創作之中。這就是后來被人們稱為漢碑書法的最初狀態。隨著碑體書法的日益發展,以至于后來包括像何紹基這樣的晚清書壇名家,漸漸地也把興趣轉到了篆書隸書等多種書體的創作上,所以,碑學書法的出現,對楹聯書法的創作推動很大。我跟鮑老師昨天也交流了一下,我們這次來講對聯,因為時間很有限,恐怕主要的時間還是得花在對聯的創作和對聯的欣賞方面。怎么來看對聯,它究竟有多少種表現形式,哪些對聯是我們在創作當中可以借鑒,哪些對聯對大家是一種相對陌生的形式,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我先開個頭,請鮑老師繼續講。
鮑賢倫(以下簡稱鮑):對聯從源頭上說,它確實是秦漢時候桃符來的,桃木在兩邊刻上神荼或者郁壘,或者是畫或者是寫,然后是驅鬼的,它的起點確實是很俗。后來一路發展,又說五代后蜀主孟昶那兩句著名句子開啟了對聯形式,這個是傳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是敦煌的遺書里面已經有楹貼,“三陽始布,四序初開”等一類放在一起,這顯然是和用途上是有關的,不是一般的詩詞要完成的篇章。再從文獻上看呢,我們也可以看到至少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時候,他已經要求大家寫對聯除夕貼出來,他微服私訪觀賞。明還有一點少,清更多,這些書寫對象已經文人化了。
但它從桃符到門聯然后又到楹聯,是從門上到柱子上的,然后再從柱子上擴展,廳堂什么都可以張掛。這涉及到什么?這一脈發展的話,會涉及到這樣一種形式和社會生活、和普通民眾的關系。對聯這個形式是那些民俗的因素和文人雅化后相結合的成果。現在我們講的對聯變成一個很龐雜的話題。當然,我們肯定主要集中的還是清以后文人不斷地提煉以后形成的一些創作規律和創作形式。
劉:我對楹聯書法的喜好,是在很年輕的時候。記得20世紀70年代上海辦過一個書法展,此前有個征稿,那時候只能寫毛主席詩詞和魯迅詩詞,再晚一點呢可以寫唐詩。我當時才二十出頭,興趣很高,也積極地去投稿響應。記得寫的是毛主席詩詞《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的“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兩句。因為面臨的結果是可能會被選中,所以興致非常高。那個時候展事很少,哪怕你的作品在報上登一登,也都是無上光榮的,別說能夠入市一級的展覽。寫到后來的結果是,上聯寫好了,覺得下聯不夠好,然后重新寫下聯,再寫下去又覺得下聯寫的比上聯好,所以上聯又要重新寫,就這么反反復復把家里有限的紙差不多都用完了。當時我住在上海市區東邊的虹口,要到市中心的朵云軒去買宣紙,路不算近。那時宣紙是兩毛七分錢一張的單宣,我咬緊牙關一下買了五張,用完后又去買了三張,以致口袋里錢全部掏光。待把宣紙全都用完,最終結果我仍然不滿意。從那一刻起,就暗下決心一定要把對聯寫好。也正是這個原因,在我的所有書寫形式中,對聯始終是我的最愛。
打那以后,我就開始留意上海那些老先生們寫對聯。當時討教最多的有任政先生、趙冷月先生、潘學固先生和錢君匋先生。再后來認識了謝稚柳先生和唐云先生等前輩。那時老先生大多有一種當場書寫的習慣,看他們怎么裁紙疊紙,看他們怎么用句子,這些過程對我來講既享受也很受啟發。潘學固先生是解放后文史館所聘的第一批館員,他的居所不大,當然案子也不大。在使用功能上,那張桌子跟陸儼少先生的差不多是一樣的,既擇菜剝豆,又吃飯燙衣,等所有的事弄完了以后,才可以在這個案子上寫字畫畫。所以這些大畫家、大書家當時的生活并不寬裕的。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近年來常有介紹書畫家書齋的專題,并且往往不惜用整個版面來刊登當下書家畫家的闊氣場景。記憶中有一回,但見功能齊全的大書齋里,擺放著一張碩大無比卻顯雜亂無章的畫桌,一側標配是專喝功夫茶的雅座,壁上高懸的四條屏筆勢奔騰龍飛鳳舞,發財樹特大盆景旁的美人靠上,竟煞有介事地安放了一張古琴。當時我心里就在想,這個不倫不類的地兒干脆不叫書齋也罷。
潘學固先生寫對聯是兩張紙疊完了以后放一塊兒寫的,我就問潘先生如此寫的原因。他說:“我這個桌面太小,只能這樣寫。”其實我自己家的那個案子也不大的,那時候我的那個房間既是臥室又是客廳還兼書房之用。于是我也學著潘先生的方法,兩張紙放在一塊兒寫,幾十年過去了,這個習慣一直沿用到今天。當然這樣寫也有一個好處,它可以在書寫的過程當中顧及到整個對聯創作的章法布局,可以顧及到運筆的呼應、章法的完整。
鮑:劉老師講得好聽,像講故事。對聯,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多的。原因一點都不稀奇,因為寫對聯是一個人初學創作最方便的一種樣式,兩條一裁,你說正文十個字是十個字,你把它寫完、寫端正,那就好了,能力差落個名字就可以。其實清代人上下款未必都有的,很多都是沒有上款的,而且下款也是很簡單的,后來吳昌碩他們越來越復雜,到現在花樣百出了。另外,它和書體又有關,什么書體寫對聯最方便?劉老師認為行書最受歡迎。最受歡迎沒問題的,其實我覺得最方便的還是正書,就是篆書、隸書、楷書。如果行書的話偏正一點,那些正書方便寫。行草書特別是草書比較麻煩,原因很簡單,因為它傳統的格式放在那里,是單個的字組合成的,都是不連貫的。
劉:所以說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恰好相反。
鮑:對對對,我講的是初級階段,你已經講到后面去了,我后面也要講與他相反的東西,這個就是一個矛盾。初步的時候就是正書方便,正嘛,一個一個寫下來,恰恰我是隸書寫得比較多,寫對聯更方便。后來漸漸走著走著,你能力強了,那你不要寫對聯了,但是同時你又發現對聯看起來最簡單、比較容易上手,但是它對你的制約也很大。你不正是不行的,一個字一個字還是要正。你歪倒過度,掛起來是不好看的。寫的時候歪一下看起來好像很生動,掛起來很怕人。對聯總體上來說是一個主正的東西。
我就說文物吧,鄧石如寫過一些對聯,他用草書寫,我看也不成功,因為它字過大以后,很難把控兩邊。那么寫到后來就發現怎樣突破對聯的這種情況,看起來一個字一個字,能不能大小完全一樣呢?好像未必,于是就要想辦法,在正的情況下看看邊界到底在哪里。靜的情況下不能太靜,就用一些動感,用一些線形,來增加它的動感,雖然寫的還是正書字體,但仍然有一種生機、一種活力。
除了正書正文以外,加一些款、印章等等,但是這些又要很有節制,恰到好處。印章是必須蓋才蓋,款是需要落才有,這個可能是一個原則。現在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什么呢?款能多則多、印章能多則多。
劉:鮑先生說到印章了,我來插一句,其實這是我們在創作當中經常碰到的問題。印章究竟怎么蓋、蓋在什么地方,印章在整個字幅、畫幅里面該用多大的,該用什么樣式的,甚至還要包括用什么顏色的印泥等等,都有關系的。懂行的,他一瞥就知道了作者的水平,用不著你多說的。記得有一次,謝稚柳先生家里來了一個外地朋友攜來一卷畫,說是他的老師的作品,在當地如何如何有名。先生說不必多說了,把畫拿出來看一看。孰知剛一打開,先生就把它卷起來了。來人很納悶,怎么不看就卷起來了?先生說:“印章都不會用,他怎么可能把畫畫得好?”可見打印章是很難的一件事。我曾專門請教過謝稚柳先生,印章究竟如何蓋才算妥當,先生說這個要看情況的,最忌諱的是,凡看到有空的地方就蓋印章。當然這就需要作者具有多方面的修養,譬如八大的畫面,看上去空寥寥數筆,其實很嚴謹的。他的畫面看上去空,其實是有內容、有安排的。后來人加蓋印鑒,如不得法就會破壞畫面。因此,畫畫要懂得章法,鈐印就像下棋一樣的,一子得體,滿盤皆活。先生多次講過,書畫作品上,如果蓋一個印夠了,就不要再蓋第二個了。如果蓋了兩三個還覺畫面欠缺,你自可以繼續蓋第四、第五個印,總而言之要看整個布局的需要。蓋得不恰當反而糟蹋了畫面,所以說這個恰當是很難的。
鮑:以前是畫家蓋的多一點,現在是書家超過畫家蓋的多,這個是很可怕的事。

劉一聞 行書文無事有七言聯 118cm×20cm×2 紙本 2016年
劉:近些年,我們在評選全國展的時候,經常會看到一些打滿印章的通篇無序的字幅。看到這類作品我往往會繞道而行。如此以“華”取寵,我看他不會高明到哪的。如果你真正對這門傳統藝術有一個正確認識的話,我想你絕對不屑于這樣做。再說,如果以此來標創新,那也未免太簡單太膚淺。
早幾年,我曾經對上海博物館所藏對聯做過系統梳理和初步研究,即便清代前期的其實也不多的。能夠見到的“四王”當中的王時敏的,也就是五言隸書小對,并且大多是窮款。所以這個現象也說明天底下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逐漸成熟起來、豐滿起來,并有一個表現規律的。不是你偶然看到一件東西,便憑著一己之見匆匆下結論,其實是帶有片面性的。只有歷史地、理性地來看待對聯書法的發展狀況,才可能客觀地得出結論。剛才鮑老師說到的鄧石如,的的確確鄧石如的強項是篆書隸書創作,他為此下的功夫也最多,所以文獻上介紹鄧石如,說他于乾隆庚子年在江寧半年,幾乎遍讀金陵梅家所藏,并將《石鼓文》《三墳記》《泰山刻石》和《史晨》《張遷》等碑版拓本,五十遍一百遍地臨摹。他如此大量臨摹古人遺跡,你當然可以想象他手下的功夫。我們有篆書隸書創作體驗的人,如果有機會去看看鄧石如的真跡,便一定會體會到鄧石如的書法功力所在。所以,當我們欣賞古代書法作品時,如果缺少相對的創作體驗,缺少一個相對的認識高度的話,也許你會看不清楚書法一道的真諦。反之,如果站在純粹學術的角度來觀察鄧石如的篆隸書和行草書創作的話,那客觀上此間創作形式確是有差距的。因此,我認為學術標準就應該一是一、二是二,不夠就是不夠,不管是對已經逝去的歷史作品還是對我們現在能夠見到的那些作品,我覺得都應該有一個真切中肯的理性評價。

鮑賢倫 隸書風云煙雨五言聯 100cm×23cm×2 紙本 2016年
有關對聯的內容
劉:我們平時所說的書法跟寫字,聽上去似乎所差不多,但其實不是一回事。小時候我甚至覺得把字寫得漂亮一點以后就能當上書法家,但是此一時彼一時,當我們到了一定年齡,有了一定的見識和積累之后,假如我們再來反觀書法和寫字的內涵,你就會知道此兩者是如此的不一樣。上海博物館有個書法館,我主持了多年。以往經常會碰到一些觀眾和一些愛好書法的朋友對我說:“劉老師,你來看看蘇東坡這個字寫的這么樣?算好嗎?是不是因為蘇東坡是大文學家,你們要把他的字放在里面,一定要放在‘宋四家’這么一個名稱里面?”我真的是一下很難回答他的話,我想這也許是因為他對書法藝術缺乏一個認識的基礎,所以一下無法說清楚,就像我對我四歲的小孫女進行道德教育她是不懂的。當然這僅僅是個比方且不一定合適,我想說明的是,我們平時認識書法創作實質一定要有條件,對于傳統書法的一些基本的知識需要知曉,對書法之作的高低優劣,要懂得一個大致的評判標準,不然的話,你便無法跟他說清楚。
鮑:內容文詞,這是文書關系的問題。文書關系的問題涉及到傳統書法在當代的一個生存狀態的問題。文書脫離背離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主流社會似乎也在提倡自作詩、自撰聯。我覺得提倡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希望能夠恢復到文書合一的環境中去。但是這樣做確實也是不容易的,整個變化太大。有時候我認為寫寫詩、讀讀詩還是有好處的,至少你對傳統文化的那個理解會好一些,然后你詩性的養育對整個創作在源頭上、心靈的養育上有好處,倒還不是你一定書法作品用自己作的詩、自己作的聯,除非你確實好。但是不要輕易寫,其實古人有很多好的對聯可以用的,前人也有很多好的集聯。前人不一定是古人,古人有的好的,我們的前輩集聯集的好的。浙江溫州有個王榮年寫的很好,后來中國書法介紹過他,集了很多唐宋年代的對聯,上海書畫出版社出了。這個可以拿來用,用的時候你再看看它這個上聯是某個詩的,另一個下聯是另一個詩的。你把這兩首詩再對照起來讀就可以發現他那個集聯真是很用心,就把那兩個句子單獨地看的意思,有了一個新的拓展,那種樂趣是非常好的。
我最近看沈定庵先生又寫了徐生翁的文章,他寄給我,他說你看看,這個行的話把它發表。他就寫道,這個徐生翁先生書雖然讀得不多,但是很努力地寫詩,詩留下的也很少,但是集聯留下的多了,約有一千五百對。你去看徐先生的作品。我說寫的“正”也是相對而言,他寫的就是不正,但是他站得住。我手上有幾頁徐生翁的。徐先生給人寫作品寫完送出去以后有記錄的。記錄在哪里?記錄在一個手札里,那個手札在一個不大的本子上面,幾號送出的、對聯什么內容,我看了以后基本上都是集聯。那個東西后來流到社會上,被朱昆明收藏了,他給我看,我說:很好!很好!你看我這次寫的很多也是結聯,至少選我喜歡的,這樣寫出來我就覺得比較好一些。當然別人的自撰聯撰得好的,我們也只能欣賞,也不大好用。最近有個張充和的拍賣專題,我關注她最著名的一個對子,上聯是“十分冷淡存知己”,下聯是“一曲微茫度此生”,將她的人生觀表達得淋漓盡致。
劉:所以要做到形式和內容的統一的確是有難度的,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要寫哪一步就能成哪一步。應該說,先賢留下的佳聯妙句是很多的,譬如明代有些句子通俗易懂,簡直跟大白話差不多。我記得有對明人的句子“有時淪茗思來客,或者看花不在家”,我們現在誰都看得懂,很親切自如,也不拗口,這一類的句子只要你留心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千萬注意,不要以為五個字或七個字似乎成對偶便就是對聯了,不是的。比方說白香山很有名的一首詩《問劉十九》中,末兩句“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跟對聯本不搭界的,但我也曾看到過有人當成對聯在寫。這樣的例子其實不少,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缺少這方面知識的緣故。常言道術業有專攻,每個行當自有每個行當的道道,當你一旦進入了這么一個道道,你會覺得自己曾經的淺薄無知,你更會覺得學無盡頭。
對聯書寫經驗談
鮑:對聯創作也最難。難就難在不易生動。比如在安妥中能不能寓奇造險,那奇與險又不能顯露在外一目了然;又比如在安妥中能不能營造出宏闊的氣象,這實在是考驗書家以少勝多能力的試金之石。
追求對聯的生動性當然是完全正當的。比如在一張白紙上不打格子不折格子不利用瓦當影底而直接書寫,就有助于放松一些不必要的束縛;比如“橫平豎直”的原則也可以變通,但“橫不平”比“豎不直”的自由空間要略大一些。豎直不直關系到對聯縱向氣脈的貫通,而橫平不平沒這個負擔,反倒可以利用橫勢獲得字形的張力;比如墨色變化也是應該有的,但不應該是被設計編排出程序來的那種,區區十幾字硬要弄出反差強烈的所謂豐富,實在是小兒科得很;又比如不必太在乎“毛病”,有時恰恰是一個病筆使全篇由妥帖變為了生動,病與不病真不能狹隘僵化地視之……總之,涉及生動性的諸因素都有個分寸感的問題,一般說來是有意追求而無意獲得。
我前期加框加的也多,直到我有這個想法以后,框就不加了。不僅不加框,我整個紙也不折的,一張紙拿起來看一眼,我就開始寫。如果怕出問題,太長的話,我中間折一條,對折一下,我就胸有成竹了。
劉:有本事。
鮑:不是有本事,這是我想法不一樣。你敢于把自己框起來,這是很有本事,我沒有,我要把可以脫掉的框框盡量脫掉。因為你不打格嘛,又是手寫的,字難免有一些大小不一,而且手寫的時候,我的創作是很感情化、情緒化的。所以兩張字,一張寫好了一張不好,事后我再補寫一張,會不會好?對我來說基本不會成功。好就是兩張一起好—一張壞了等于是還有一張沒用,我再補一張是補不上去的。補上去以后,它的那個精神就是不一樣,兩張是同時寫的時候,它保持的信息是最真實的。我自己看中的是真實,比如說正好這里有一個聯,那個上聯到下面字小了,小就小嘛,我再寫下聯寫到下面字大了,大就大嘛,那個小和大看起來對稱性有點問題,但是整體來看上下聯造成的那種氣氛、那種氣局是不能移動的。我再補一張的話,肯定是對不牢,所以我的這種創作具有一種個別性。必須是上聯寫完寫下聯,拼也是拼不成的。

劉一聞 行書學為愛若八言聯 180cm×25cm×2 紙本 2016年
我現在在努力,而且我還是愿意做這樣的嘗試。但是當然我很警惕,所有的這些努力,關于藝術努力的一定不能江湖化,這是劉一聞先生一直強調的,就是你這個基本的立點是一種文化的立場、文人的立場、學術的立場,不能走得太遠,因為現在對聯的核心部分它已經不是早期的普通對聯了。如果是普通對聯的話,是把它定義在習俗上的,所以它這個含義和我們現在在談的這個對聯講的核心已經有所差異。所以關于雅俗的問題、關于古今的問題、關于動靜的問題,都有一個辯證的東西。現在怎么變,我們都要看看古人,覺得他變的合理不合理。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下款,我就覺得有一個變法,大家注意到沒有?現在的很多展廳里面落款,一個姓名啪一下子跳到很上面去。現在這個是怪的,你去看清朝的沒有這種落法的。為什么沒有這種落法?他要送給誰抬高一點,把自己壓低一點。有不少聯,這次掛著的也有的,幾乎落到最后一個字去了,這個倒不要緊的,今天我們這樣落,大部分人說掉下來了、掉下來了,提上去,提到哪里?可以提到那么高。我想來想去,大家都已經很習慣了,什么原因?現代人的那種自我意識空前高揚,自己最突出、自己最重要,可以提高到醒目。

劉一聞 隸書松筋竹風七言聯 138cm×35cm×2 紙本 2016年
劉:聽起來輕輕松松,但是你仔細琢磨琢磨,如果要我照他的方式來做,我也做不成的。比方說剛才疊格子不疊格子,我都嘗試過,倒是年輕的時候敢這樣做,越是上了年紀越是想面面俱到。也許積累還不到家吧,希望到年齡后能夠做到。
鮑:我以后會疊的。(笑)
劉:我年輕的時候臨摹了大量的印章,幾乎都不打稿子,別人當時也夸我,說這個劉一聞刻圖章倒是有點膽略和才氣的。但是當我到了一定年齡以后,反而離不開寫稿了。我曾追問過自己,昔日的那種鋒芒到哪里去了?當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賢倫兄能這樣涉筆成趣地隨意揮灑,我內心的確很欽佩,起碼我做不到。此外,當然還跟每個人的性格和審美觀念都有關系。比方說我就穿不了像他這樣的衣服,仔細看看里面有很多暗花,而且是很雜亂的一種暗花,我只能一路保守地穿對稱的格子。我寫字打格子的紙,是往日一個學生打的,后來他到了外國去,我手邊就只有原來剩下的那些紙了。因為有限,每一次寫的時候心里反添負擔,所以寫出來的字雖然筆體齊整,卻大多了無生機。這種情形的發生,除了經驗,更多的是與由精神而致的創作狀態有關。
鮑:他這個方法確實也是很有他的優勢的。你像我以前也打格子,主要是我能力不夠,借打這個格子有點效果。現在一聞兄的格子這么一折以后,整個大局已經奠定無疑,然后他就會把注意力放在每個字的細部。我恰恰照顧不到細節。
劉:剛才我聽鮑兄講寫八字聯中間按一條虛線,他一看就知道怎么下筆,這個把控能力當然也跟你當領導布大局的能力有關。樣樣事都是因為平時實踐多、歷練多,所有經驗和教訓都從中而來。
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在對聯書法的創作中,首先要注意選擇恰當的內容。一般而言,主要取之兩種途徑。一種是使用現成的佳聯舊制,可以從匯集和研究對聯的專集中去查找,從這些集子中大抵都能找到可供選用的對聯,十分方便。另一種是因各人性情常識自撰新聯,這頗能顯示出一個人的才情和識見。古代童蒙學子的日課之一就是對對子,寫詩作對是很尋常之事,文人雅士一般都是書寫自制的對聯。但在當代書法家中,能作格律詩的已很少見,能作對聯的恐怕少之又少。因為創作對聯,必須語言精煉概括,結構對稱整齊,音節鏗鏘諧合,比作律詩的對偶要求更高。我們從前幾屆中國書協舉辦的楹聯大賽作品集中不難發現,那些所謂自撰的聯語,存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自作聯語,若沒有深厚的舊學根基,怕是做不好的。所以我看與其做張打油,不如以第一種途徑入手,認真研究前人的名聯佳制,這樣似乎更實在些。
其次,書寫對聯要注意在“靜氣”二字上下功夫,現在大家書寫的對聯,主要是掛在家中客廳或書房中,以清新典雅、疏朗俊逸、涵蘊深沉,給人嫻靜雋永的意境者為佳。書寫對聯,由于其特有的形式,使書寫者常有一種愜適之意,因而也更易于自由揮灑、輕松創作。這也許就是為什么現在很多書家都喜歡以對聯形式創作的原因吧。對聯主體內容寫好后,落款也能看出一個人學問修養,決不可馬虎草率。
再次,對聯創作中要注意鈴印的位置。印章其實也是一副對聯書法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能起到有效地平衡章法的作用。
還有一個引出來的話題就是所謂的審美問題。前幾天何國門寄了一本大冊子,他說是早幾年出的。以前我也曾注意過國門的創作,但是看的都是零零星星的。這次寄來如此厚厚一本,讓我看到了他的完整風貌。國門的老師、鮑兄所作的序文,讓我尤其留意。當時看了鮑兄的序,我就跟家里人講,讀書跟不讀書是不一樣的,貴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手筆寫得多好。這個好,還在優美文筆之下的精當措辭。
所謂作品的入古與否,當然是傳統藝術的命脈所在,如果你把不準這個命脈,縱然你有再多的創作手段都是白搭。入古的作品,三筆兩筆就到了這么一個不可替代的穩穩當當的位置了。我們不妨以刻印為例,如果刀筆相背不合榘度,縱然你把印面都砸爛了,還是做不到意與古會,骨子里還是新的東西。所以,為藝者一定要明白這種關系,這是我們用來衡量傳統創作的標準所在。
鮑:我補充一下,劉老師這個入古講了一個古今關系的問題,我非常贊同。前幾年“蘭亭”評藝術獎,我們兩個都是評委,他說這個評到底還是要有個說辭的,基本標準是什么,后來我說了一個詞,他很贊同,即“雅正”。“雅”是區別于“俗”的,“正”是對偏、對邪而言的。這是一個比較高級別的,不是簡單的多種樣式的問題、百花齊放的問題,還是要有一個主導性的走向。這也是呼應我們前面話題的。
責任編輯:劉光

鮑賢倫 隸書煙雨河山二十五言聯 137cm×35cm×2 紙本 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