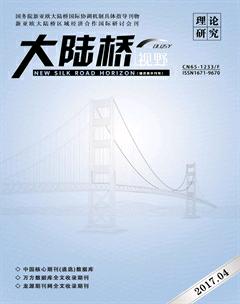以黃庭堅為例淺論宋詩對唐詩的模仿與創(chuàng)新
楊瑩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
【摘 要】唐詩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璀璨明珠,宋詩亦是中國詩歌的高峰。兩者之間因時代先后必然有著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本文從唐人及其詩歌對宋人產(chǎn)生的深刻影響出發(fā),認為宋人具有普遍的無意識崇唐傾向且對唐詩多持肯定態(tài)度。繼而引出宋人學唐現(xiàn)象之普遍這一觀點,再以黃庭堅學杜為例分析宋人對于唐詩的繼承及創(chuàng)新。最后得出此現(xiàn)象是符合繼承與發(fā)展這一藝術(shù)規(guī)律的這一結(jié)論。
【關(guān)鍵詞】崇唐心理;黃庭堅學杜;繼承及創(chuàng)新
一、宋人學習唐詩的崇拜心理
唐詩作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大高峰,對后世產(chǎn)生著巨大的影響。宋人集體無意識地接受著唐詩的影響,隱約地延續(xù)著唐詩的脈搏。他們對唐人難免有著崇拜心理,因而常將今人之詩與唐人作比較,這在大量的宋代筆記中可以發(fā)現(xiàn)。文瑩《玉壺清話》中: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畛畦,間入李、杜深格。其中就將鄭毅夫詩歌與李白、杜甫之格相比,于此只言片語中便能看到其集體的無意識的火花。不僅如此,宋人自比為李白、杜甫及唐人的現(xiàn)象,更是一種普遍的存在。歐陽修《歸田錄》中:予嘗在福州見山僧有朋有詩百余首,其中佳句……不減唐人。文瑩《湘山野錄》卷上: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這都清晰地反映出了宋人對唐詩潛意識地接受。
在接受唐詩的過程中,宋人也清晰地看到了唐詩的優(yōu)點。在當時流行著一句話“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正是宋人對于唐詩的極大肯定。從具體詩歌來說,宋人認為唐詩寫得十分之妙,歐陽修《歐陽文忠公試筆》“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凄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這無不體現(xiàn)出歐陽修對于唐人溫庭筠的欣賞之情。此類宋人贊賞唐詩之例更是不勝枚舉。
正是由于宋人對唐人的崇拜心理和對唐詩的肯定,使得宋代學唐現(xiàn)象十分普遍。
二、宋人對唐詩的模仿及創(chuàng)新
宋代詩學思潮的演變,自始至終便是在如何選擇唐詩典范的過程中推進的。由宋初的學白樂天,轉(zhuǎn)而學李商隱,或者學賈島、姚合,再進一步去學韓、學杜,最終樹立起韓愈、杜甫為宋詩的最高典范。在宋初詩壇上有著諸多詩歌流派,這些流派都各領(lǐng)風騷,但其共同特點都是師法唐詩,同時也是在探索一條屬于自己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路。盡管師法的對象與探索的方式有所不同,最終卻都不可避免地落入唐人的窠臼之中,可謂“青出于藍而未勝于藍”。然而,他們的探索并非沒有意義,也并非純粹的模仿。
北宋后期,以黃庭堅為首的陳師道、秦觀、張耒等詩人在蘇軾影響下活躍于詩壇,被稱為江西詩派。江西詩派崇杜學杜,迎來了宋代詩人學杜的第一個高潮。黃庭堅學杜,更是宋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因而以黃庭堅學杜來探討宋人對唐詩的模仿及創(chuàng)新是再恰當不過了。對于黃庭堅學杜,其實許多學者認為他是失敗的。魏泰就曾批評黃庭堅“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臨漢隱居詩話》)張戒也說他未得子美之精髓。認為其只知從形式上學杜而不能得其精神實質(zhì)的片面性。嚴羽則說:“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對此,傅明善先生認為持此論者可謂代不乏人。然而,正是這些對蘇黃詩風有異于唐人風致所表示的不滿言論,卻恰恰給我們提示了蘇黃在變創(chuàng)唐宋詩歌風貌方面的杰出貢獻,而且即使是蘇黃與唐詩的關(guān)系也并不是簡單的背離,而是繼承與發(fā)展,推陳出新的關(guān)系。對于此說法,本人十分認同。正如黃庭堅說的作詩要有所創(chuàng)新,“聽他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后人”。(《贈高子勉》)甚至于逆?zhèn)鹘y(tǒng)而動,“詩須做到眾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石林詩話》)只有這樣才能樹立起宋人自己的個性旗幟。
黃庭堅學杜并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對杜甫詩歌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根據(jù)黃庭堅本人的論述,他對杜甫的繼承主要在于句法。《冷齋夜話》卷一記載“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這段話說明黃庭堅學少陵,就是想盡量做到 “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他學的是杜甫的表達方法,不是詩歌內(nèi)容。黃庭堅對杜詩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是基于對杜詩的正確認識。《后山詩話》記載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所以不工耳 。”這也恰恰表明了山谷學習杜詩是有選擇地學,而不是盲目地照搬其創(chuàng)作方法。
另外,近人往往認為黃庭堅尊杜僅僅著眼于杜詩的句法與用典,而對于其思想方面很不重視,其實這是一大誤解。實際上,他是很注重杜甫的思想精髓的。如元豐二年三十五歲時所作的《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帝閽悠邈開關(guān)鍵,虎穴深沉樣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潛知有意升堂室,獨報遺編校舛差。” 由此可知黃庭堅在杜詩中品味到了“忠義”精神。可見,黃庭堅首先注重的是杜詩所繼承并發(fā)揚的《詩經(jīng)》所開創(chuàng)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和忠君愛國的情懷。他在晚年時期還教導后學說:“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fā)而言。”(《潘子真詩話》),“忠義”二字在此處更是有了十分深刻的表現(xiàn)。黃庭堅學習杜甫,絕不是僅僅看到了“無一字無來處”和“點鐵成金”,更包含了深刻的思想。雖然黃庭堅在實際創(chuàng)作中沒有像杜甫那樣表現(xiàn)出“一飯而未嘗忘君”的憂國憂民思想,卻也寫出了像《流民嘆》和《書摩崖碑后》這樣的刺世之作。
其實,杜甫的精髓就在于學習前人卻不模仿前人,自成一家,而黃庭堅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恰恰是學到了杜甫學習前人卻不模仿前人的獨創(chuàng)精神 。清人袁枚說:“古之學杜者,無慮數(shù)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后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與稚存論詩書》,《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一)這也正表明了上述觀點。因此,用莫礪鋒先生在《江西詩派研究》論及黃庭堅對前人詩歌藝術(shù)的繼承時所說,黃庭堅學習杜甫,就重在從杜詩中得到某種啟發(fā)而有助于自己的創(chuàng)新,所以黃詩是黃詩,并不類似杜詩。因而,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純粹模仿這一說了。
在此暫且表達我的觀點:學習前人是為了提高自己,借鑒遺產(chǎn)是為了推陳出新。因而山谷學杜而不似杜,正是其成功之處。這種學習是琢磨藝術(shù)品的創(chuàng)作途徑而非復制藝術(shù)品的學習,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創(chuàng)造更多成就的學習。
參考文獻:
[1]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中華書局,2003年.
[2]劉葉秋《歷代筆記概述》北京出版社, 2003年.
[3]傅明善《宋代唐詩學》研究出版社, 2001年.
[4]嚴羽《滄浪詩話校釋》郭紹虞 校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1年.
[5]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齊魯書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