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與防控金融風險 路在何方?
◎ 劉英團
加強與防控金融風險 路在何
加強與防控金融風險 路在何方?
◎ 劉英團

“金融業和公眾之間的微妙信任關系已經被金融危機打破了——有研究證實,此次危機是由金融業內部產生,并由金融機構和金融家所引發的。而且,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有一個共同點:債務的濫用不受任何審慎風險管理的約束,概莫例外。從2015年的千股跌停,到2016年多個銀行爆出票據問題,金融風險一觸即發。我以為,中國要對世界經濟及全世界20%的人口負責,既不能容忍金融家背叛金融的本質,更不容金融業背叛實體經濟”。也正是基于此種高瞻遠矚的視野和經濟認知,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提出了風險警示。他強調,金融領域改革的重點是“加強金融風險防控”。與往年不同的是,2017年的金融改革不僅僅是“創新”,更重要的是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金融的背叛”都是從欺騙開始。在《金融的背叛:恢復市場信心的十二項改革》(以下簡稱《金融的背叛》)一書中,美國前紐交所副總裁喬治·烏杜博士揭開了金融業虛假繁榮的真相,即“由于金融家們的背叛,金融業也背離了經濟”,“金融自身成為了目的,而不再關乎其理應發揮的社會與經濟作用”,甚至僅保留了“金融服務業”的“金融”二字,卻將“服務”拋諸腦后。從“日本夢”的破滅,到“拉美國家的負債”,再到“世界的金融危機”,首先應當歸責于金融機構,正是金融機構的金融家們引發了金融危機。作為地球村的一員,中國經濟必然與華爾街金融的榮衰深度地聯系在一起。比如,華爾街金融危機勢必波及中國資本市場,A股走勢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持有這些金融機構資產的海外投資者還可能大量拋售中國資產以回母國自救。因為不是個案,大規模的撤資不但極易誘發系統性經濟(或金融)風險,還會使不少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工作。
宏觀審慎政策主要使用審慎性工具來限制時間維度和跨部門維度(或結構性)的系統性風險累積。一如喬治所言,正是政府及行政監管部門的放任政策使得金融危機成“必然”,而這種拒不認錯、反思的行為讓公眾如何恢復對銀行的信任呢。這種否認,這種不承認對危機負有責任的做法,又怎么能夠恢復市場信心呢?如果把“引起一場金融危機”的責任推卸給“貪婪的投資者”,普通投資還怎么敢、還怎么會信任金融機構呢?要恢復公眾對金融機構的信任,一是不要再玩弄那些或明或暗的花招,以試圖向已經感覺上當受騙的顧客收取更多的費用。二是學會與公眾溝通。在服務行業,溝通能力不可或缺,而金融也是服務業。三是不要把金融危機的根源歸結到人具有動物精神的本性(恐懼與狂熱、從眾行為、依賴傾向、競爭本性,等等),尤其是政府及金融監管部門不要再去狡辯、推卸在金融監管中存在的“部分錯誤”,用自由市場理論(政策)去拆解監管中“過錯”或“失誤”是毫無意義的,邏輯上也是行不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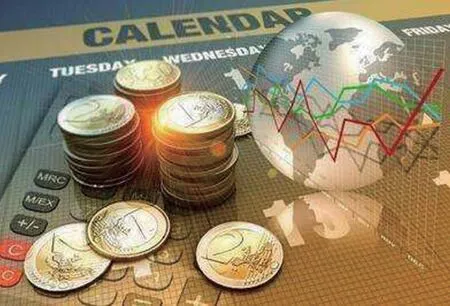
喬治認為,金融并非神話,卻被刻意地弄得神秘,甚至背離了金融的本質。“只要我們不構建合理的制度來實現真正透明誠信的管理,那這場騙局就會繼續下去。金融的不透明,并不僅僅因其復雜性所致。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一領域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玩家’不愿意讓你了解金融的游戲規則。這樣一來,他們就能繼續散播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謬論,并蒙蔽公眾的視線。”在《金融的背叛》一書中,喬治尖銳地批評金融家的虛偽和貪婪,“任何試圖聲稱自己也被蒙在鼓里的辯詞都是蒼白無力的。”當然,透過金融的蕪雜表象對金融危機的追根溯源,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給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找到幾個替罪羊,而是試圖發現政治經濟體制中隱藏的那些必須通過改革才能得以糾正的薄弱環節,以避免重蹈覆轍,或者亡羊補牢。喬治強調,金融機構不僅要服從監管,更要對其將來的發展方向,對其基本的行業原則,乃至所秉持的價值標準躬身自省。
金融風險沒有國界地域之分,也沒有預期有無之別。在《金融的背叛》中,喬治分別從“央行為何沒有洞見危機”、“債務與股本:過度負債之殤”、“次債騙局”(次級貸款)等方面透析金融的本質及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金融是經濟、社會和政治社團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就應以消費者為中心。”首先,金融規律和經濟常識是欺騙行為的“照妖鏡”,消費者(或公眾)也應對金融機制有基本的了解,或者懂點經濟常識,這不僅僅關乎自身的財產安全,還關乎市場經濟能否高效運轉。“龐氏騙局”之所以蔓不止,就是因為有大量無意識的追隨者,太多的投資者只單純關注表面回報,而看不懂背后的風險。如果普通投資者掌握基本的金融經濟規律或者投資常識,難道還會往金融陷阱里跳?其次,即便是陷入金融困境,金融家們也應該認真嚴肅地對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負責。當然,華爾街是貪婪的,不要指望金融家們汲取教訓。所以,防控金融的背叛,關鍵取決于構建何種金融體系及如何監管金融機構,以使其不觸犯道德法則和自然法。
從后果看,這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全球、至今余威尚存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發達經濟體主要金融機構業務模式、發展戰略方面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以及金融監管方面存在的漏洞。所以,喬治強調,不但消費者(或公眾)不能容忍“金融霸權”,政府也不應將“金融僅交與金融家之手”。從金融監管與改革實踐看,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系列峰會不但明確了國際金融監管的目標,還確定國際金融改革的最終方案。為響應G20峰會要求,相關國際組織積極開展研究工作,主要經濟體也強化了對金融的審慎的宏觀管理,相繼改革了國內金融監管體制。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國際清算銀行(BIS)編撰的《有效宏觀審慎政策要素:國際經驗與教訓》的報告對宏觀審慎政策的內涵、目標、組織結構安排以及職能和政策工具等進行了系統研究和分析,就如何實施宏觀審慎政策、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和恢復市場信心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作為G20成員、FSB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成員,中國不但深度參與G-SIFIs(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認定和監管要求的制定過程,還高度重視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建設,“到2020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戰略目標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強調,要“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整頓規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風險‘防火墻’”。金融改革的方向已然明了,一是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二是著力防控資產泡沫并處置一批風險點,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三是積極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處理好金融改革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關系。在《金融的背叛》中,喬治提出的停止欺詐消費者、規范薪酬制度、讓董事會真正負起責任、重整監管部門、制約金融創新、重歸透明簡單、確保資本誠信、給評級機構戴上緊箍咒、重新界定金融風險、監督資本市場中的對沖基金、讓咨詢顧問言而有信、全球監管機構協調一體化等十二項改革意見,不但擊中了金融業改革的核心,還找了準突破口,對我國防控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風險尤具參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