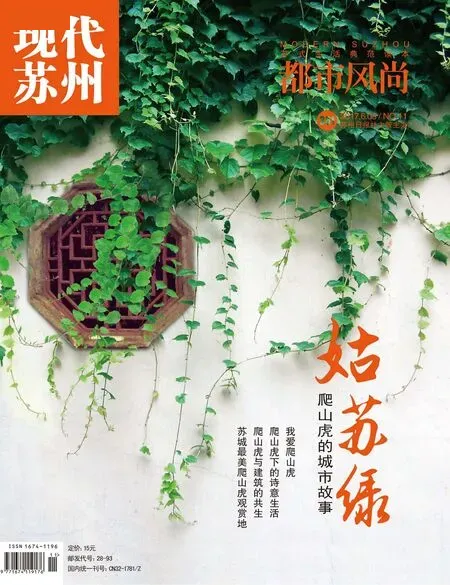有筍的季節(jié)如此清香
有筍的季節(jié)如此清香

蔡猜,1970年出生。畢業(yè)于蘇州大學(xué)。曾在《雨花》《作品》《揚(yáng)子江》等雜志發(fā)表過(guò)詩(shī)歌和小說(shuō),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參加2008年宋莊當(dāng)代藝術(shù)大展,參加再造型2012蘇州當(dāng)代藝術(shù)展,舉辦“紅酥手”個(gè)人藝術(shù)展。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ài)是永不止息。
這幾天的餐桌上,母親總是燒出一碗又一碗的春筍燉咸肉,每天開(kāi)飯前,我在房間里總能聞到一陣陣的肉香。那些香味,直到母親叫一家人吃飯才被忽略。咸肉是父親自己腌的,一塊塊曬干后放進(jìn)了冰箱里。筍是從菜場(chǎng)上買(mǎi)的,分不清是本地還是別處生的。無(wú)論它從哪一塊泥地里鉆出來(lái),我們一家都喜歡一邊嚼一邊稱贊筍的味道。等大家飯碗見(jiàn)了底,那一碗筍也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幾塊咸肉,還頑固地在碗里沉浮。
筍是那種小竹筍,在我還很小的時(shí)候,家里有一片竹園。家在河的北邊,竹園在河的南邊。去竹園的小橋是兩塊厚長(zhǎng)的石板,它的長(zhǎng)度可以容納一條船通過(guò),兩塊石板的寬度不到一米。每逢春天,我會(huì)在母親那雙大手的牽引下,穿過(guò)這兩塊石板,到達(dá)河對(duì)面的竹園,然后,四個(gè)眼睛一起偵察,有沒(méi)有筍尖從土里鉆出來(lái)。
小時(shí)候,一直不曉得筍和竹子的區(qū)別。
而大人們連我問(wèn)的原因也搞不清楚,就更無(wú)法回答我的疑問(wèn)了。而在孩子的眼中,筍跟竹子是沒(méi)區(qū)別的。一個(gè)是長(zhǎng)了葉子,而另一個(gè)沒(méi)有長(zhǎng)大而已。
于是,我得到的結(jié)論千篇一律,筍就是竹子。
可我怎么看那筍,也不像竹子。而且我發(fā)現(xiàn),那些剛冒出來(lái)的筍,樣子比竹子要少許粗些。怎么長(zhǎng)著長(zhǎng)著就會(huì)瘦了呢?只見(jiàn)小樹(shù)越長(zhǎng)越大,沒(méi)見(jiàn)過(guò)大樹(shù)返老還童,慢慢縮小的呀?這些無(wú)比深?yuàn)W的道理,就是我小時(shí)候一天到晚琢磨的東西。母親不識(shí)字,能把生活理清楚已經(jīng)不錯(cuò),哪里能回答我希望了解的事情。更何況,我問(wèn)的問(wèn)題,有時(shí)候根本也不是問(wèn)題。
植物從土地里冒出來(lái),每個(gè)春天都再來(lái)一遍,就像每個(gè)人要學(xué)會(huì)走路吃飯。
得不到答案的我,養(yǎng)成了自己觀察的習(xí)慣。那些沒(méi)被挖走的筍,很快就撥長(zhǎng)了。幾天時(shí)間,就比我的個(gè)子都高了。我發(fā)現(xiàn)筍殼脫落后,竹子就顯得青瘦了許多,而到了它長(zhǎng)出枝杈來(lái)時(shí),竹竿就更細(xì)了。
有點(diǎn)像一個(gè)青春期長(zhǎng)個(gè)子的孩子,一年中長(zhǎng)高許多,但突然你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種時(shí)候基本上沒(méi)有太胖的孩子。
一直感覺(jué)自己比兒子幸運(yùn)的事情,就是在我小的時(shí)候,我有那么多的時(shí)間,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
它們就是我的老師,用一年四季,慢慢地改變著我的感觀。
也讓我在今天意識(shí)到,那種慢慢的改變,意義如此深遠(yuǎn)。那種童年的記憶,比如今那些孩子,待在溫暖的幼兒園中,聽(tīng)著鋼琴,唱著兒歌要美妙得多。但那時(shí)候的我,特別羨慕電影里的小朋友,穿著潔白的襯衫,唱著優(yōu)美的歌謠,顯得那么幸福。
讓我久久不能釋?xiě)训拿篮茫诮裉旖K于被自己打破。
筍是季節(jié)性的菜肴,一過(guò)四月,即使再有筍從竹園里生出來(lái),那味道也不那么鮮美了。必得早春的鮮筍,味道才鮮嫩得叫人百吃不厭。
偶爾也會(huì)有些許的傷感,似乎我們每吃掉一棵鮮筍,地上就少了一根竹子。而我是喜愛(ài)竹子的人,因此還有點(diǎn)感覺(jué)罪過(guò)的想法。當(dāng)然,我的想法僅只是杞人憂天。每個(gè)擁有竹園的人,每年都會(huì)有意無(wú)意地留下一部分新長(zhǎng)成的竹子,使得竹園可以一直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