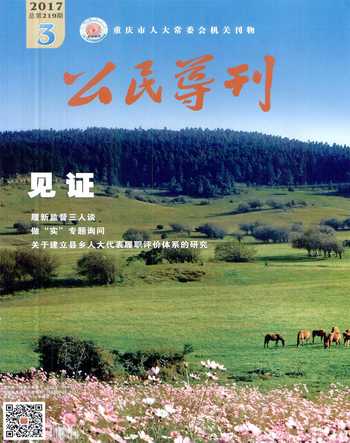留住記憶中的重慶味道
常暢
十八梯是一條絕對資格的重慶老街,坐落于重慶渝中半島,是連接重慶上半城與下半城的街道。
雖然這條老街與解放碑只間隔一條街,但卻界限分明,在解放碑,你可以領略到現代都市的繁華;而在十八梯,你就從現代都市步入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老重慶了。
在渝中區較場口往中興路的轉角處,有一條幾百米的老街,在渝中區堅守著最后的老街故事,這條被歲月斑駁的街道,承載了多少人的童年歡樂、青春記憶、老年生活。
它就是十八梯。
如今,石板階梯仍在,古老的氣息依舊濃厚。只是磚樓飄窗已朽,鐵窗銹跡斑斑,老街兩邊的老舊房屋被石灰圍墻包得嚴嚴的,早已人去樓空,剩下的只有無限的緬懷。圍墻墻面上寫上了赤紅的“行人注意安全”。
作為無數重慶人的回憶,十八梯最后的景象也將結束了,又讓多少人開始感懷:再看你一眼,在你消失前……
藏在老街里的人情味
“以前這里綠樹成蔭,走在街上都能聞到別人家鍋里的菜香。”
“老街的電線桿橫七豎八,小販的叫賣聲走街串巷,錄像廳里時而傳來一陣陣笑聲,滿街是小孩們的歡聲笑語。”
“那些老人們,常常坐在街邊聊天曬太陽,抽著葉子煙喝起茶。”
那是記憶中的十八梯。
長長的石頭階梯旁是老式的居民樓,里面居住的人家被稱為“梯坎人家”,它是重慶的記憶,在這里,每天都是人來人往,沿街擺地攤的、算命的、修腳的、賣小面的,散發著重慶獨特的市井百態,人情味十足。
66歲的段輝琪在南紀門的勞務市場邊跟賣泥鰍的聊天,邊洗自己的車子。“這些都是以前在十八梯的老熟人,見面就要寒暄幾句,有時還幫忙吆喝兩嗓子。”
“那邊還沒拆掉的紅磚房,就是我以前的家。”段輝琪指著街對面的那棟小樓說,以前的十八梯,總有些人醒得比天早。挑小面的,賣菜的,往往凌晨4、5點就開始一天的忙碌。“我當時和他們一樣,早上4點甚至更早就開始跑車拉貨了。”段輝琪以前是山城針織廠的大貨車駕駛員,每天起早貪黑的跑車,甚至晝夜顛倒。
“這個院子里住的都是我們廠里的員工,鄰里關系特別親密,想不親密也不成,出去進來的,一天不知道見多少回。”老實的房屋緊挨著,看起來就像親人那樣親密。“就算我們各進了各家的屋,也都聽的清清楚楚。哪家來了個客人,每天做什么吃的,鄰居們都清楚。”
走到以前住的院壩里,段輝琪回想起老廠長張大林。這位,無妻無子女的老廠長,病逝后,無人安葬。“當時我們街坊鄰居們自發組織操辦喪事,有把自家桌子搬出來的,有自發準備飯菜的,有拿板凳、碗筷的,就為了送老廠長最后一程。”這樣的人情味放在現在,估計不會再有了。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在十八梯的老街上,這話一點不假。鄰里之間我幫你買一斤菠菜,你給我捎帶一兩大蔥那是每天的平常事。
如今,這些院子里的鄰居都搬走了,有的住在南坪、有的住在江北,有時也會來看看,段輝琪說:“有些住不慣,總覺得缺了點什么。”就是缺了街坊鄰居的那份親熱!
城市中心的棚戶區
老十八梯,經過6年多的拆遷,厚慈街、響水橋、鳳凰臺……大多都拆掉了,留在那里的老居民寥寥無幾。
今年71歲的秦文秀,在十八梯善果巷35號住了半輩子,提起老十八梯她的話匣子就打開了。
“以前的十八梯,大多都是老集體企業、街道企業的工人,還有解放前就常居于此的居民,生活十分融洽平靜。”
從90年代初開始,十八梯就涌進大批外來人口,大量的租賃戶在歷年的亂搭亂建中,幾塊木板就能搭成一間房。到2010年,十八梯片區的外來人口已經超過50%,超出了原住居民。城市的中心淪落為棚戶區。
為什么大批外來人涌入十八梯?
秦文秀說,自1995年開始,進城打工者越來越多,形形色色,良莠不齊。他們的到來讓十八梯的氛圍開始異化,為一兩度水電費,為幾毛菜錢,可以爭論個你死我活。
“房子租金便宜也是外來人涌入的一大原因。一部分掙了點錢的居民,急急搬了出去。留下的房子就拿來出租,像我以前住的房子,也就26個平方,一個月租金才200左右一個月,小旅館一天的價格也在10元左右。便宜的租金,加上又是在重慶中心地帶,自然吸引打工者。”
秦文秀一家三代人都住在十八梯,有個活潑可愛小孫女,提及到小孫女秦文秀滿臉的笑容。“我最愛護我的孫女了,平時我都不讓她單獨跑出去耍,搬離十八梯就是為了保障我孫女的健康成長。”
對于搬遷,秦文秀從來都是站在支持一方的。在她看來,十八梯的生活氛圍、生活條件已經到非搬不可的地步了。
2012年,秦文秀正式告別了她的十八梯善果巷35號,和老伴搬遷到了江北可樂小鎮。
等待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輪蛻變
如今的十八梯已如開篇描述的那樣,住的人不在了,游客卻多了起來。
巷子里還掛有條大大的紅色橫幅“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常回十八梯看看”。
在十八梯的觀景臺上,依然有許多人來來往往,在歷時7年的精心規劃后,有著“山地城市傳統建筑技藝博物館”之稱的十八梯即將重生,重建后的十八梯,或許變得干凈,變得高雅,但在這片土地上留下的回憶,卻是永遠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