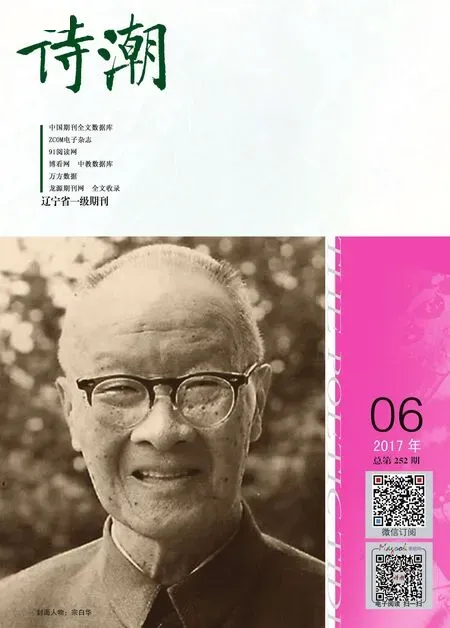時間終于讓我明白 [組詩]
蔭熊 焱
時間終于讓我明白 [組詩]
蔭熊 焱
我記得某些瞬間
十六歲那年,我做了一個大手術(shù)
全麻后醒來,下午的陽光正端著顏料
涂抹著窗口的畫板。樹枝上的鳥兒正拉著琴弦
唱出大海激越的潮音
我欣喜地摁住心跳:多好啊,我還活著呢
多年后,我在悲傷中喝得酩酊大醉
夜半醒來,頭疼若綻開的煙火
窗外的燈光仿佛勝利者不屑一顧的譏諷
大街上,疾馳的車輛掠過了呼嘯
宛如旋渦中蕩起的波濤
我沮喪地問自己:哎,我為什么還活著
再后來,很多年一晃就過去了
我記得某些瞬間,全都隔著茫茫的生死
鏡子
第一次看到鏡中的自己
是在那個嗷嗷待哺的春天
唇邊的細絨毛變成堅硬的野草
眼角的魚尾紋攪起細微的浪花
是鬢邊的一縷白發(fā)告訴我天亮了
而我做了一宿迷亂的夢
許多夢境我都記不清了
只有鏡子知道,可它一直掛在那里
始終沉默不言
是他們扶住了我
悲傷時,是酒
扶住了我
奔跑時,是風
扶住了我
我有浩大的寂寞,疼會扶住我
我有絕望的落魄,愛會扶住我
是鬢邊的白發(fā)扶住中年的霜降
是額頭上的皺紋扶住腳繭上的花朵
而歲月總是悄無聲息地伸過來一雙手
把我膝蓋上的傷痕細細地撫摸
這人間到處是坍塌的道路
一個個的背影走得歪歪斜斜
紛紛從良心的天平上跌落
我慶幸我還有文字,為我扶住了靈魂的秤砣
我一直在等一封遠方的書信
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封遠方的書信
我一直在等一輛郵車穿過晨曦的絲綢
裹住晚霞火辣辣的熱吻
我一直在等一枚信封里緘住的呼吸
寫信的人在遠方送上波浪般起伏的心情
我一直在等那幾頁薄薄的信箋
沿途為我捎來流水的歌謠和月光的夢境
想想曾經(jīng)書信往來的日子,恍惚間已成隔世
我懷念方方正正的楷書,就像淬火的鐵
在清水中抱緊錚錚的骨氣
我懷念行書如飄飛的細雨
明月的杯盞斟滿了清風的影子
我懷念狂草上的墨跡涌動著泥沙俱下的水聲
我從浪花中撿起一片片閃光的魚鱗
現(xiàn)在秋日正深,我鬢邊的青絲
已染上了薄薄的霜跡
我手機上的短信、微信中的低語
都抱不緊鴻雁的一聲脆啼
只有歲月在不停地幻變,不停地催促著人心
多快啊,這年歲又悄悄地增添了寒意
葉已落下了數(shù)秋,花已開過了幾許
我還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封遠方的書信
就像這蒼茫的人生,正在經(jīng)歷著顛沛流離
動物園
牢籠里的獅虎豹,像溫順的小貓
一日日地,消耗著生命慵懶的孤獨
圍欄中的羚羊、駱駝和斑馬
伸長的脖子,嚼不動饑腸的轆轆
只有假山上的猴子,為了游人們施舍的糖果
還在變著花樣翻跟斗
我聽到游人中發(fā)出的尖叫和歡呼
像相機的閃光
穿過動物們哀傷的瞳孔
而我們風塵仆仆,只為了滿足
內(nèi)心里拿一份獵奇逐異的私欲
我原本提著繡像的筆
只是我已不知道
我是該畫人,還是該畫動物
因為我看到的動物已變成圈養(yǎng)的家畜
我看到的游人卻在心里奔跑著豺狼和老虎
遺孤
地已荒蕪,人已遠走
在我日漸凋敝的故鄉(xiāng),苦寂的時光
落滿蒼涼的鐵銹
多少人從這里出發(fā),就不再回首
多少風刀雕面,白霜染頭
南歸的候鳥也叫不碎那一聲離愁
多年來我走過異鄉(xiāng)的車站、機場和碼頭
走過十萬里山河的花開、月明和水流
我羨慕那些年年遷徙的候鳥
北方的家園、南方的巢穴
都在冬暖夏涼地為它們守候
我羨慕那些堅守土地的農(nóng)人
生時有一縷炊煙迎接啼哭
死后有三尺黃土埋葬白骨
就連那些葉落歸根的人,那些
魂還故土的人,他們都比我有福
故鄉(xiāng)的懷抱,終是容納了他們流淚的鄉(xiāng)愁
而我顛沛半生,從高原輾轉(zhuǎn)盆地
從谷雨穿過白露,故鄉(xiāng)只是一個疼痛的名字
一場入骨的舊夢。我已無途可返
我已成為她無人疼愛的遺孤
時間終于讓我明白
層層的梯田從山腳一直延伸到山頂
像歲月中無數(shù)分岔的小徑
春天的油菜花捧起大地洶涌的黃金
秋天的稻谷點燃生活浩瀚的火焰
多少年我穿梭其間,延綿的群山撐高了天空
彈丸的村莊宛若低低的盆景
我總是向往著遠方水天一線的大海,劈浪的槳
裹著海水的藍絲綢翻身。更遠的地方是無邊的草原
疾馳的馬蹄打開月光的容顏
當我在外漂泊多年,見慣了大海和草原
我在某個秋日返回故鄉(xiāng),藍天拉著大海的帷幕
群山織著草原的裙子。層層梯田已有部分荒蕪了
但起伏的稻浪,仍在風中翻滾著波濤
仿佛生存的手掌刨開沙礫,淘出生活沉甸甸的金子
風端著顏料,為走動的牛馬
收割的鄉(xiāng)人,調(diào)和成寫意的線條
多么愧疚呀,時間終于讓我明白
我的鄉(xiāng)村有著斑斕的大美,只是作為故鄉(xiāng)的叛逃者
我已不配接受這人間豐腴的饋贈
不配獻上我廉價的愛與贊美
該拿什么來贖罪
人們磨快了刀
把豬宰了,把雞宰了
把羊也宰了
作為他們贖罪的祭品
或者,作為他們許愿的供品
擺上了神案
我常常想:也許有一天
這世界會出現(xiàn)一個新物種
在他們要贖罪的時候
在他們要許愿的時候
他們也磨快了刀,把人宰了
然后作為祭品供上神案
霧霾
有時候,我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地方
那些在霧霾中匆匆忙忙的身影
仿佛是在墳場里游蕩的幽靈
有時候,我會抱緊身子
一張張口罩閃過
我擔心,他們是不是要蒙面索命
站在三十樓高的房頂,我看不清大地上的事情
眼前若隱若現(xiàn)的高樓,仿佛只是一場幻影
但我看清了,正在一點點地潰爛的良心
無數(shù)的我,正在麻木地袖手旁觀
正在麻木地無能為力
此時我的母親臥病在床,咳嗽不息
幾十年里,她以堅韌的骨頭熬過了饑荒、災(zāi)難和窮困
卻不知道該以怎樣一個強大的肺

彭宇作品《在水一方》
來熬過這個嚴酷的冬天
送女兒出門的時候,在街邊
兩只狗戴著口罩,穿著新衣
正在蹦蹦跳跳地撒歡。我相信
它們一旦站起來,就是人形
我再一次茫然四顧,再一次確信無疑
——這真的是人間
我錯過了那些愛
母親生我的時候已經(jīng)三十六歲
成熟的風韻宛若九月沉甸甸的稻谷
并在生活逼仄的催促中,迎向冬天的早雪
我愛她
但卻錯過了她青蔥的韶華
妻子認識我的時候已經(jīng)二十二歲
窈窕的青春仿佛姹紫嫣紅的三月
滿世界都是陽光的水銀和純金的鳥鳴
我愛她
但卻錯過了她玲瓏的童年
年過三旬,我在秋天的黃昏等來女兒的降生
她多小啊,一粒白嫩嫩的芽孢
將在歲月的風雨中拔節(jié),結(jié)出她十歲的骨朵
開出她十八歲水靈靈的鮮花
我愛她
但將會錯過她白發(fā)蒼蒼的暮景
生命終將在最后放手——
我愛她們,這一生已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