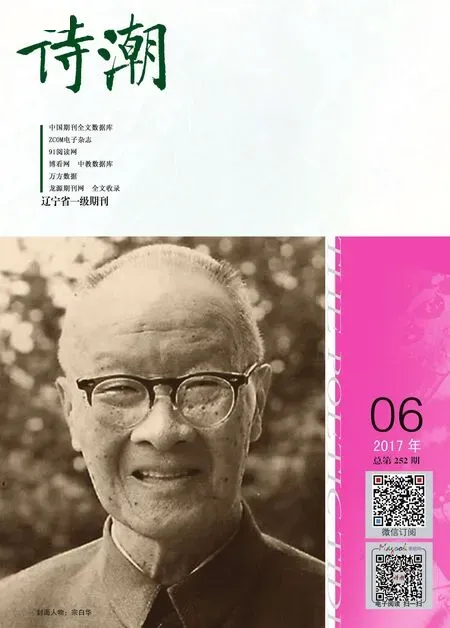在鄉土的芬芳里 [組章]
司念
在鄉土的芬芳里 [組章]
司念

司念,女,80年代末生于安徽,現居北京,文學碩士。文學作品及評論散見于《詩刊》《星星》《詩選刊》《散文詩》《散文詩世界》《中國詩人》等報刊及多種選集。
爺爺對我說
在七八歲的時候,一個夏日的午后,爺爺帶著我來到村子東邊的寺廟大墻背后。
那兒有一座凸起的墳墓,像一個小籠包,絲毫不起眼。
沒有牌位,只有野草。
爺爺戰戰兢兢地流淚,并且叮囑我不要告訴任何人。還告訴我,這是我死去的小姑姑,
她曾經給我洗過尿片。
爺爺輕輕地呼喚著她的小名:“小榮,我來看你了。”然后是爺爺無聲的傾訴。我仰起頭看到眼淚從他的眼角滑過。
爺爺告訴我,不能讓奶奶知道,仿佛,我們做了一件見不得人的事情。
這個在世界上來過十六年的人,似乎不曾來過,又似乎留下了什么。
不僅僅是一座將越來越矮的墳墓。
第一次祭祖
叫不上名字的祖先躺在山坡上。十幾年前,爺爺的遺愿是回到他父親出生的地方,與先祖共一座山坡,并邀上他兒時的伙伴、愛妻和兄弟。
最后索性帶上了他的父親、母親,父親的兄弟,父親兄弟的愛妻,或是牌位,或是白骨。
當然,還有重新打造的棺木。
環山面水的山坡一片慘黃,在冬日里寂寞著,后人似乎忙于生,忙于活,忘記了他們,只能在每年的某一天,祭拜一次他們。為他們燒一串紙錢,點一束香。
我的性別決定了祭拜的不可能性,據說祖上規定,女子不入族譜。
但在家族發黃的族譜里,有著我的族名,名曰:司馬硯。族譜里,我將被記載為爺爺的孫子。這是爺爺當族長時唯一的一次破例。
這是我第一次祭拜爺爺,爺爺的父母、兄弟、弟媳、愛妻,我記不住墓碑上的文字,除了磕頭。他們的名字,清楚地寫在族譜里,但我知道,女人們的名字前一定冠了夫姓。
我在想:我漂泊的靈魂將會在哪兒?
我未來的兒子,將被如何記載?
姑媽對我說
她是老大,在家被用作男人。
母親出工的日子,她也要出工,算半個勞力。
她還未成年,提前進入成年的勞動行列。
她去過大壩防洪,在大壩上燒火做飯,洗衣打夯,她去過田野挑土,一擔一擔的黑土壓在她的肩頭,氣喘吁吁,她在家帶過年幼的弟弟,也玩過石子和牛角。
母親托人帶了一碗咸魚,被所托之人半路吃了一半,剩下一半,被堤壩上的勞力們搶完了。

何家英︽賞梅︾
她把黑土挑完,被眼前混亂的畫面震驚,一場關于咸魚的爭斗,在她疲倦歸來時熱鬧上演。
成年后,出嫁前,她要親自去拉嫁妝,這本該是哥哥干的活,于是她把自己當哥哥。
出嫁后,她挺著笨重的身子繼續做著勞力,為沒有成年的弟弟,為男人不在家的母親。
她說著,好似在說別人的故事。
她說著,不像是苦,倒像是甜。
門口的池塘
池塘里有魚有蝦,營養著鄰里的腸胃,池塘里還有水怪,時時驚慌大人小孩。
我曾經與伙伴在池塘里戲水,雙腳亂蹬,激起泛著青草的水花,我也見過水面上漂著的小孩,肚子圓鼓鼓的,皮膚格外白。
池塘躺了許多年,清清的水,映照著四周的房屋,像一幅畫。
時間把自己分成了一段又一段,貼在房屋的門上。福、祿、壽,財、富、貴眾神延續到永恒,就像一代又一代人的念想和期盼。
多年后池塘荒蕪,被土填滿,成為大地的一部分,我知道池塘的樂于成全卻遺憾盲目的同化和追隨。
也許池塘忘記了自己的屬性和位置,退回到最早的低洼里。
也許時空屬于殘忍,記憶反而真切精準。
萬物生靈啊,你們用什么記錄自己?
租出去的土地
六畝地被分給六口人,土地種上了玉米和棉花,種上了養活我的農業。
母親曾經灑過棉藥,父親曾經摘過棉花,母親的母親除過草,母親的婆婆澆過水,母親的孩子學著大人滾過泥土。
土地還沒種完,還沒收獲完,被租給他人。
全家搬到城里。吃公糧,每天跟糧食打交道,從此不再親自耕種,就像交接了一項工作,完成了一個任務,然后,一家又一家的鄉親也離開了土地。
城里往往是這樣的:科技取代手工,模仿取代天然……
豐富的食品放置在商場貨架上,被貼上不同種類和價格。
來的人,去的人,胖乎乎,喜笑顏開,猶如年畫上的福娃,又如春天里的喜鵲,喳喳鳴叫。
人們偶爾談論起從前,憐惜從前的苦,心疼吃過苦的人。唯獨沒有心疼土地,那被拋棄的寂寞,與他們無關。
嘗試并不是所有人具有的膽量,拋棄是他們的專利。
土地從來不寂寞,只有沉默。
一切肉體和靈魂,是否最終被原諒,讓土地回答。
只有風和陽光,還是一如既往在拋荒已久的土地上搖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