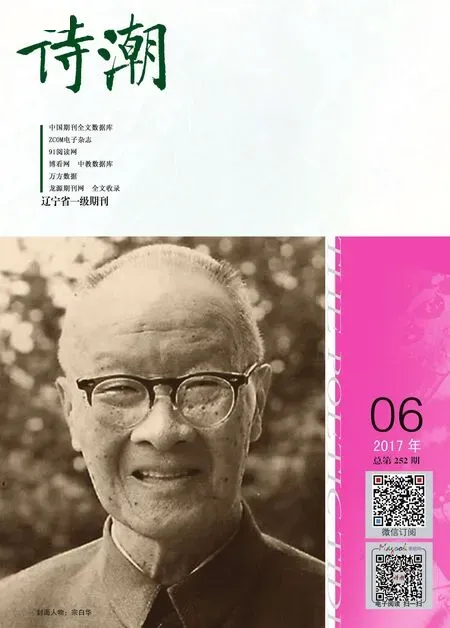一位女博士頭頂的帽子 [組章]
轉角
一位女博士頭頂的帽子 [組章]
轉角

轉角,女,本名王玉芳,1976年10月生于黑龍江。作品在《詩刊》《詩歌月刊》《星星》《青年文學》《山東文學》《東方女性》《世界詩人》《中國詩人》《上海詩人》《星河》《香港散文詩》《常青藤》(美國)等數十種刊物發表。作品多次被譯介并入選《大詩歌》《中國散文詩十年》等多部年選本,獲第八屆中國散文詩天馬獎、《詩潮》2015年度“現代詩獎”等多種獎項。曾參加第十四屆全國散文詩筆會。著有散文詩集《荊棘鳥》。現居綏棱。
夢里的兩個人
藏著恐懼消失,一些深不可測的恐懼由來已久。
我在深夜深處抵達另一處地址,暗中患有隱痛的人正徘徊在一堵墻下自言自語,遠處的黃昏憂愁起來了。我想,她富足的日子是否長出了幾片透明的黑葉子,我該給她吃些什么呢?
站姿不正,我緊貼天空撫摸她渾圓的頭顱,她的表情不得見。但那是我啊,不為任何人所知的一個長頭發少女,一只溫順的羔羊——
我知道。
我聽到她在我的下方喘息不止,急促且慌亂。而此刻,黃昏正在向她下達一份抵抗黑暗的戰書!
丑與怪物
枝條綠了,火焰融化,一小片滿月在來的路上祈禱——
樹,葉子,微瀾彈奏著人影的黃昏。
一只白鴿漂動在海上,若干丑與美轟隆隆出現。白色幼小的肢體,透明如聲浪,沉浮不定。灰暗的水面撲打一只怪物,群鷗煩惱起來了,她們該拿他怎么辦呢?
哀之所愛,這臻于同族的異類,是該拋棄還是攥緊……
黃昏躍出天空的范疇,丑的化身又被遺忘在赤裸的海上,海面呈現果子的形狀,凄清的肉身步下神樹,靠近樹下的葉子喃喃自語——
樹是海的怪物,白鴿是鷗群的怪物。
我,難道不是丑的化身?
流動性
島在無邊的黑暗中嘶鳴。
我在流水上方尋找扎根水面的樹枝和草葉,或者別的什么可支撐我游走的漂浮物。我渴望什么人此刻剪碎海上憤怒的波濤并架設一條通往天國的梯子,我自奮勇地追襲而去。
可是,若干年了,海面依舊平靜如昨日。
思忖良久,一個結論呼之欲出:我們在構陷自身的剎那可否真能觸摸到彼此,高懸上方的太陽俯瞰的只是一劑虛空啊——
所謂氣體,頗具戲劇性。
人,物,塵世。
流動著,往復著,從未回答過任何人。
三月的馬蹄
親友的城在三月混亂。
我所說的三月,銀白色,琥珀色,有天使叩擊卷發少年的抑郁顏色,他們一并詛咒我烈火一樣的激情與斗志。
死,泛著黑暗的波光與恐懼,深不可見。
他們大聲交談,一起獵色,他們不存在令人猶疑的斜暉映照一些虛空之物,他們只是喜歡吃花,看三月的馬蹄附著在空洞的陽光里分外妖嬈……
幾經輾轉,我白銀似的翅膀終于瞻望到人的貪欲。
江湖早已藏身在人們默識的空蕩里了。其實,我是愿與他們去往極樂世界的。
一位女博士頭頂的帽子
薔薇提心吊膽地開了,她恰好開在一位女博士頭頂的帽子上。
吊燈一樣搖來擺去。
一些嘈雜與驚恐裊裊傳來,自遠方的地平線,自人的肺腑……撕扯這世上唯一一個高學歷的女人。她光芒的頭發是卑劣者唯恐避之不及的災難,她光輝一樣的眼神潔凈得容不下宵小之徒一絲裸視……
可以說春天是被一群南來的燕子聒噪得不得不降臨到松花江上的。
我也是。
那叢蘆葦從干枯的深褐到薄雪融化后的焦黃像極了一朵探春的薔薇,剛好開在女博士的鬢角——
那顏色,恰到好處地湮沒了浮沉中的我。
濕漉漉的眼睛
再也沒有什么可以用來做分別的道具了。
樹根不斷挖,樹葉不斷掉,樹枝的兩旁不斷堆積枯萎這個嘆詞。追風之后,風開始向著人們想要的方向吹,不管天與地這張開合有度的大嘴吞下什么,不管不相干的借口怎樣修理淚水,雨水,汗水……
鼓聲陣陣,雷聲陣陣,桃紅迷亂了誰的心呢?
四維空間傳出雜亂無章的腳步,這些都是該被遺忘的聲音啊。而被春日驚濤拍岸后吞噬的黑夜,這巨大的黑眼珠盜取了的夜的光明——
泛出的又是誰的血花?
沙漠深處的一堵高墻
街市是自由的,沙子長出無數誘惑。
根伸到不顯眼的位置伺機而動,駱駝的響鼻,人搖晃起來了。大藍如鏡子,滲入血液的羞愧啊,如火如荼——
打開一扇門,這里有圣潔的朝拜。
人終是植物的附屬品。當我垂下眼瞼,太陽就覆滿我一身火,我充盈的細小的愿望終得以遺失。
這堵高墻終究是超過了沙漠的高度的,他憂郁孤僻。
他是憂郁孤僻的啊——
所屬的日子,所屬的可是人的煉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