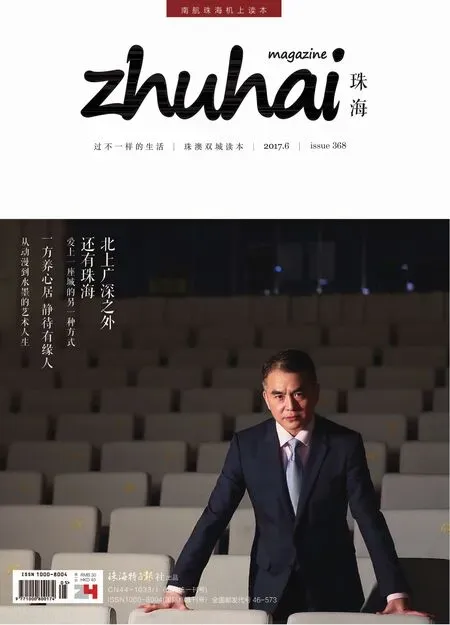北山精舍 一方養心居 靜待有緣人
文 | 孫凱 圖 | E-IMAGE攝影
北山精舍 一方養心居 靜待有緣人
文 | 孫凱 圖 | E-IMAGE攝影

北山村在珠海人眼中并不陌生,無論是老屋古宅訴說著的曾經輝煌,還是被文青們青睞的現代元素,都讓這個沉靜的小村有了許多與眾不同的活力。名聲在外卻又深邃內斂,北山村與繁華的市區生活始終保持著適度的距離,融入其中卻又自成方圓。歷史與前衛、傳統或新潮,北山村包容了生活或藝術的無限可能,一如選擇隱在這村落深處的北山精舍。
北山精舍就坐落于北山小村內一條隱秘的小巷中。走過青石板鋪就的狹長巷弄,穿行于世代生活在這里的村民的家長里短之間,很容易就會錯過精舍略顯狹小的門口,從外面看去,矗立在一片老宅中間的北山精舍,與周圍的青磚灰瓦毫無二致,仿佛它一直就在這里,只有門口掛著的木質匾額告訴匆匆而過的行者,這間已有190年歷史的老宅,如今早已不再頹廢,斑駁的青苔上,長出了新的模樣。
古村里的美學居所
北山古村,始建于北宋年間,由楊姓族氏為主體的居民組建而成,在900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嶺南文化。時至今日,村里還保留著許多一個多世紀前的老舊建筑,村子的格局也變化不大,充滿歷史文化風情的古老村落,自然吸引了許多喜愛古典文化,熱衷文創的人到來,為村子帶來了新的活力。
北山精舍,也是被這里的歷史味道吸引而來,客棧的投資經營者常姐,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北方人,在家里從事了多年酒店管理后,10年前,因為陪孩子讀書來到了珠海,從開始的只在珠海“貓冬”,到后來的長居珠海,常姐也慢慢喜歡上了這座城市,在這里定居了下來。
常姐的珠海生活與普通的家庭主婦一般無二,隨著孩子日漸長大,常姐也希望能夠讓孩子看到自己人生的另一面,而不是每次放學歸來看到的那個扎著圍裙在廚房忙碌的媽媽。為了能夠陪伴孩子一起成長,常姐萌生了開一間客棧的念頭,與自己曾經從事的管理相關,與普通酒店相比,又有一些新意和挑戰,常姐把目光鎖定到了經營一間小而美的民宿客棧上。
在常姐的暢想中,這間客棧不需要太大,有8到10間房間足矣,要有足夠的公共空間,可以安放自己的想法,最好不要新建,如果能開在一間有歷史的老宅院里,就再完美不過了。或許是緣分注定,萌生念頭的常姐決定去北山村看看,而她輾轉咨詢到的第一個“房東”就是現在北山精舍所在老屋的業主,190年歷史的老房子,曾經做過祠堂、當過學堂,基本結構依然保存完好……老房子可以說符合了常姐對未來客棧的所有預期。
就這樣,在北山古村的一間老屋之中,常姐開出了一間安放自己心靈,也給路過行者提供身心休憩的小棧,并為它取名“北山·精舍 禪意美學客棧”。
在滿足現代功用的同時,保留對古老文化的傳承和尊重,是精舍營造的靈魂,庭前影壁上原有一方壁畫,常姐和客棧的設計師也曾試著修復,但問遍村中老人,已經早已無人記得壁畫上的內容,這成為了常姐心中的一個遺憾。
與古老相得益彰的禪意生活
推開厚重的木門,穿過玻璃幕頂籠罩下的青磚墻、青石板,就走進了這方自成天地的院落,一道門隔開了外面的喧囂,成為出塵與入世的分界點。進入精舍,就能聽到輕呢般的佛音禪唱,讓人的心不由自主的靜下來,安定下來。心無雜念,靜如止水,仿佛即使在這里隨意坐著什么都不想也不會無聊,而是一種享受。
與普通的客棧布局不同,精舍的“前臺”被安排在了左右對列的兩棟客房建筑后面,一間由六根百年鐵梨木撐起的寬闊宏偉的大殿,這座大殿曾經做過私塾、當過祠堂,而今變成了客棧的接待大廳。從左側角門而入,一方池水、幾朵蓮花,還有周圍高低錯落的花木組成了一方小小院落。采訪當天的蒙蒙細雨,更是給這個畫卷小院蒙上了一層朦朧的詩意。大廳正中擺放著新中式風格的接待桌椅,而在廊下門后,則是按照古老樣式打造的書案坐椅,只要稍作布置,前臺立即變身講臺,臺下則是小桌案前跟隨先生誦讀的童子,時光,又回到了這里曾經作為私塾的遙遠過去。
前廳的兩側,被辟為了客人交流和休息的空間,左側寬大的原木桌前,是新中式風格的圈椅,后面的書架上則擺放了各類書籍,住客可以自由取閱。常姐從全國各地淘來的各種充滿禪意的小物件也點綴其間,架上還養了兩只蟋蟀,給這個寧靜的空間,增添了一絲靈動。
從桌前的圈椅延展開去,新中式風格的家居營造充斥在這里的每一個角落,長榻、案桌、地燈、圈椅、窗欞等傳統家具和屏風、竹簾、古琴等設計元素的加入,讓這里既有中國傳統神韻,又具現代設計感。
在滿足現功用的同時,保留對古老文化的傳承和尊重,是精舍營造的靈魂,就連屋頂的瓦片,都是在修復時特意從其他拆建的老宅上淘來的;腐朽的木質橫梁,也是輾轉從其他建筑中選取年代相近、粗細相等的木材進行更換。庭前影壁上原有一方壁畫,常姐和客棧的設計師也曾試著修復,但問遍村中老人,已經早已無人記得壁畫上的內容,這成為了常姐心中的一個遺憾。
精舍一共只有八間客房,每間都是有獨特的名字,分別取自《論語》《中庸》《大學》,更添書香味。最大的套房因為墻上擺著許多的古琴,故叫 “琴醎閣”。琴醎閣是客棧“最悅耳的房舍”,房間劃分成三個不同功能的空間,從總體布局到細節都做到精簡而帶著悠悠的詩意。因“樂”取名由來正是進門右側這間掛滿古琴的琴室,琴室的對面屬于房間內的起居室,房間是復式設計,共能容納7-8人,樓下有茶座可喝茶談天,還配有書房。
精舍在每個開放的空間,都會擺放靜心寧神的檀香。而在客房中會擺上,適合睡眠的沉香,以穩定心神。房間的書桌上還會放上二三本店家精心挑選的枕邊書和茶具,希望入住的客人能從中找到屬于自己內心的那一份寧靜。
靜待有緣人
修葺一座老房子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尤其是這種上百年的老屋,重新休整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遠高于重新修建一座同等規模的現代建筑。精舍的設計師黃麒和他的搭檔楊東方對此深有體會。出生于珠海唐家的黃麒可以算作是土生土長的珠海人,1995年在中央美院求學歸來后就與搭檔共同開辦了工作室從事從小熱愛卻并非自己專業的空間設計。20多年間涉足和參與了多個大型項目的設計建造,最終卻落足在了古建筑修復上。

在唐家古老院落間長大的黃麒目睹太多古老的建筑藝術精品在視線中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亡著,他認為自己應該為此做點什么。在珠海的北山村,黃麒遇到了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一群同路人,懷著對古建筑和古文化的敬畏之心,黃麒和楊東方先后參與了“停云書房”“北山精舍”“藝學堂”三個古建筑修復開發項目的設計建造。
黃麒認為,古建筑修復首先應該尊重古建筑的歷史內涵,要對這些古老智慧的傳承保留足夠的敬畏之心,所以在古建筑的修復上,他反對大拆大建的修復模式,更反對因為一些功能和美觀需要去破環建筑原有的格局和結構,這些都是先人在多年生活中總結出來的建筑智慧,雖然在今天看來有些地方已經沒有了實際功用,但它的存在依然有著歷史的價值。
因地制宜,是黃麒對古建筑修復利用的不二法門,在他參與主持的三個項目中,可以明顯的感覺到內部風格的差異,對此黃麒的解釋是:他會根據每個建筑的不同特點,結合使用性質,設計出在保留原來古建筑韻味的同時滿足不同功能訴求、風格不同的設計方案。
正是這種對古建筑的敬畏之心,讓常姐選擇了將精舍交到他們手中,讓這棟一度荒廢的老宅在他們手中涅槃重生,煥發出昔日的榮光。同樣因為對古建筑的熱愛與精舍結緣的,還有從事酒店管理運營多年的資深職業經理人老黃。
與老黃的相識,也被常姐歸結為緣分,在精舍剛剛開始營建的時候,常姐在招聘網站上寫下了簡單的招聘需求,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第一個前來應聘的老黃正是因為厭煩了標準化酒店中按部就班的格式和迎來送往的應酬,準備嘗試新的生活才來到了北山。幾人的理念一拍即合,精舍的樣子也在他們的手中勾畫完成,最終在2016年9月變成現實,成為如今我們所見到的模樣,老黃也被常姐的精神感召,自動入股客棧,成為了精舍的第二個投資股東。


對于常姐來說,這里不僅僅是一個客棧,更是一個安放心靈的地方,因為精舍,她能夠與黃麒、楊東方,與老黃結緣,也希望通過這里,吸引更多精神上契合的人前來。累積投資300多萬元的北山精舍,常姐和老黃卻從未過多的去思考盈利的問題,雖然老黃堅持以五星級甚至超五星的標準去要求這里的每一個細節,把他從事酒店管理多年,已經深入骨髓的客戶至上理念貫徹到了精舍每一個細微的角落。
得來不易,所以要學會感恩和分享。住在北山精舍的每一個人,都被給予了如家般的溫暖關懷。為此,以弘揚國學文化為主旨的精舍精心組織了書法、古琴等各類不定期活動,在房間呆膩了就可以前來參加,無需什么流程手續,碰上即是緣分。閑暇之余,你也可以來大廳里喝茶,以茶會友,同在一片屋檐下,此刻,大家是一家人。
賞花、喝茶、讀書、小憩、吟詩、彈琴、會友,遠離世間的紛紛擾擾,靜謐而又清心。一切,正如老黃在自己的帖子中所言:“讓趕路的人趕路,讓等人的人等人。讓所有的相遇,剛剛好。在這里滌盡了塵、囂、煩、燥、狂、熱、烈酒、花紅,在這個稍顯寂靜的院落里,除了一池水,千瓣蓮,幾只龜,還有一盞茶。”
“當清晨的露水覆上百年老祠堂的屋檐,微風吹開屋檐上石縫里多年來兀自長出的花草,墻上蒙著一層銹跡的雕花,在用繁復精細的紋理講述著古人虔誠雕琢的匠心。人們緩慢走在紅磚石板上,那踢踢踏踏的聲音都像在說著百年前的老故事。”
“我不要求賓客如云,我只是靜候有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