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與現代并不割裂
吳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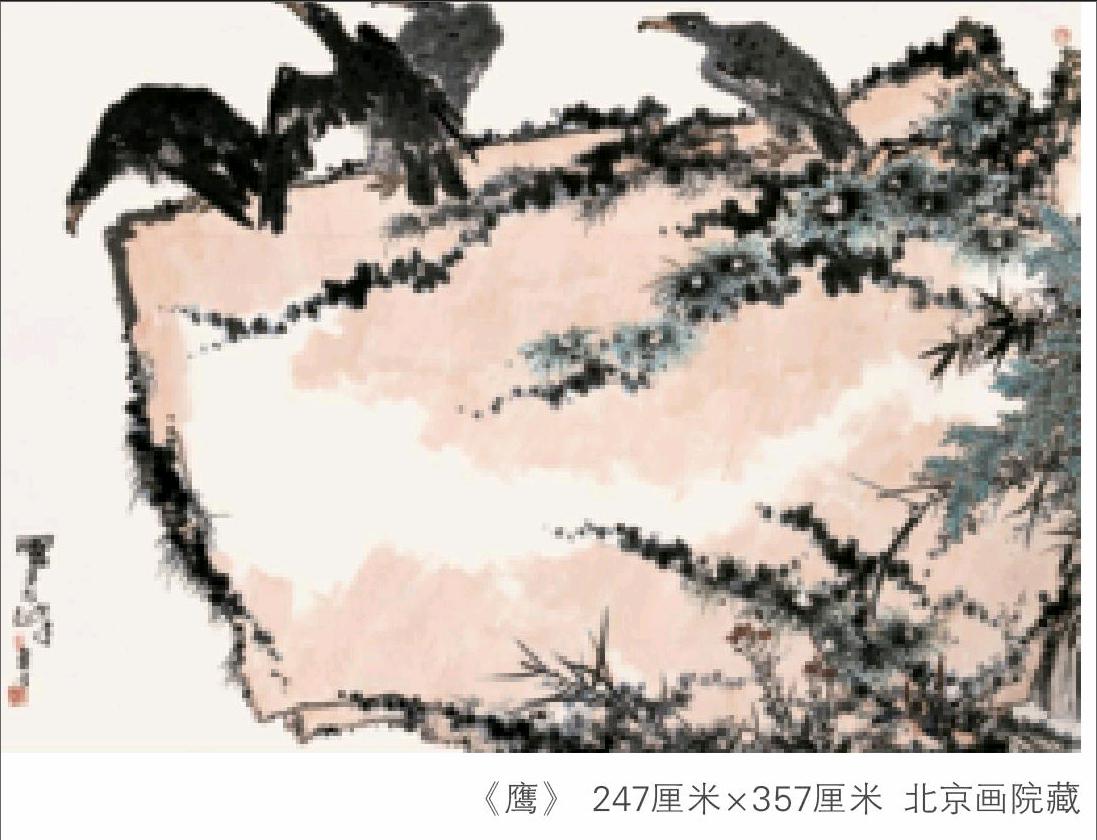
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人類的生存狀態發生了很多改變。而20世紀的藝術家,除了畫好自己的畫,還要面對各種新問題的出現,首先就要面對畫為誰服務的問題。古人的書畫創作是屬于中國文人的,其意并不在于解決與社會、群體有普遍關系的強烈訴求。而從民國時期開始,中國藝術家已經介于中國文人的理念和現代知識分子責任轉化之間的關系,這讓他們既保留著一定的傳統文人情懷,希望自我愉悅,又有對視覺效果等其他方面的追求。
民主制度和現代生活其實是一個社會公共化的過程,如北京中山公園、上海豫園等過去的皇家園林、私人空間,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成為公共空間。對于藝術品來說,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兩種展示空間,一種是公共交流空間,另一種是真正的美術館。例如陳師曾、張大千、黃賓虹等藝術家都曾在北京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水榭舉辦個人展覽,過去三五好友間欣賞手卷、冊頁的私密性交流演變成為面對公眾的開放性展示。
當整個社會對藝術品的存在方式要求不同了,空間的變化必須要求藝術家改變以往的創作思維。基于這樣的變化,所有的中國畫家都希望改變過去中國畫不適應大空間展示的特點。筆精墨妙的中國畫已經不適于案頭欣賞,尤其與西方油畫在一起展示的時候,國畫表現出來的視覺張力明顯不足。
那么,中國畫如何在展廳中被看到,就成了當時很多畫家急需解決的問題。經常有人用“霸悍”來形容潘天壽的筆墨,其實,對于空間的營造更能凸顯其霸悍的視野。李可染善于用造境的方法營造空間,一定給觀者制造一個空間邏輯,在一層一層地渲染中建立一個空間體系,又在這個空間中形成一種縱深關系,視覺上充滿體量感和豐富性。而潘天壽與李可染的構圖邏輯不同。為了讓掛起來的畫充滿不弱西畫的能量,潘天壽一直在平面系統里面尋找那種霸悍的張力。他在平面中并不講求透視關系,往往在一張紙上做一個撐滿畫面的角,讓人感覺整個空間都在膨脹,而畫面中其他內容的每一根線條也完全是向四周張開的,從而占滿整張紙的空間。潘天壽還會將畫面中的重要內容如鷹、青蛙、貓等安排在畫面的最上端,但由于整個畫面的張力,視覺上并不會感覺有失重感和壓抑感。
我們欣賞潘天壽的作品,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如果模擬一個300平方米的會議室,將潘天壽的大幅作品置于其中,你會發現無論從哪個角度欣賞,他作品中的主體都不會被遮擋。如果很多人站在一張作品前合影,很多畫家的作品畫面主體會從照片中消失,而潘天壽的作品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其實,潘天壽在教學中也注意讓學生在平面中突出構圖的能量。據張立辰先生回憶,潘先生上課時要求學生用最簡單的方式分割空間,而他所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畫蘭草,他認為以這種方式劃分的空間變化最為豐富。如果潘天壽有意完成中國畫在空間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的訴求,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會簡化作品的形象,將構圖更為清晰、明朗化,將筆墨更為霸悍作為追求的目標。但所謂筆墨的霸悍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筆墨完全是服務于這種結構關系。我們可以拿同樣曾在杭州國立藝專任教的李苦禪先生對比,看李苦禪的畫,可以很近地感受每一筆筆墨單純的能量,而潘天壽的筆墨能量是為結構服務的態度則更明顯。當然,李苦禪也對空間感有追求,但那是一種更含蓄的能量,而潘天壽則更富有張力。
潘天壽霸悍的視野還表現在他的指墨畫創作中。所謂的霸悍一定要有剛強的“澀”的感覺,而一味用筆去表現,到達一定程度后會變得熟且滑,指墨線條恰恰能解決這樣的問題。筆與人心的距離更遠一些,以指掌作畫更貼近人的控制范圍,線條也更生動、更富有心性,很多時候勝于用筆完成的效果。正是這樣的現代意識,使潘天壽能夠用傳統方式在傳統意識的延伸中達到現代的意愿。
對于潘天壽的研究應該放在20世紀國際藝術整體發展的邏輯中去看。因為如果僅僅是在同時代的比較中去看待一個藝術家,通常容易忽略其藝術成就;但如果將潘天壽放在一個國際藝術體系中去比照的話,我們會發現他確實做到了以中國方式與西方藝術拉開距離,所以他對中國藝術的發展是有重要作用的。而如果從教學方面講,當年杭州國立藝專明顯區別于其他美術院校的一點是,對于中國畫本體的傳統的保留還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說,是潘天壽這樣的大師留住了中國畫的根。
中國藝術在上世紀50年代所面臨的所謂危機,也不過是其自省與自我修復的一個過程。而潘天壽這一代人,以其自身的實踐回應著中國藝術在歷史中一時的失語與低落,也正是他們的努力,使這門藝術得以新的演進而不是真的斷裂。
(注:作者系北京畫院副院長、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