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川云 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
葉宏+程晨
一份不為眾人所熟知
卻為大眾所需的專業服務
一次次先於大爆發前的平息
一宗宗民事糾紛的和平解決
考驗的是每個專職人員的平衡把控
守護的是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
他是民眾的調解員
他將衝突與負能量
轉化為社會安定的力量
十年調解路,創下和平景
不平凡的十年調解路
一宗民事糾紛案件,如果走上法庭,少則數月多則數年,這是一個不斷消耗時間、精力和金錢的過程。在香港,民事糾紛在進入庭審之前,都會有專門的調解員進行溝通,盡量達成和解協議,愿意達成調解的案件都會通過更為簡化的方式得到解決,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為納稅人降低費用,節省了法院的資源,保障了彼此的利益。
如今的香港,調解已被有效及系統地應用於解決大廈管理建筑工程產生的糾紛、婚姻等爭議,而香港的調解制度中,調解員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在與鄧川云先生的交談中,我們才真正對此有了初步了解。“和事佬”雖是調解糾紛之人,但卻不像專業的調解員有明確的規則約束。一名合格的調解員,在處理糾紛之時必須堅持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則,不能判斷孰是孰非,只可以通過提問的方式,找出雙方的底線及要求,以求尋找到最大限度的維護當事人雙方利益之法。
鄧川云先生是一名資深註冊社工,自1978年以來,曾從事不同的社工領域,包括輔導和罪犯服務。在為選舉活動等作義工之時,因其別具一格的建議,得到了眾人的共鳴,便加入了最早期的調解服務中。
2006年,鄧川云先生取得註冊調解員後,便專注於該領域,積極參與調解工作,至今已走到第11個年頭,超過1240個小時的調和、80多個大小案件,目前擔任香港調解師協會會長、香港和解中心表列調解員、土地審裁處建筑物管理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表列調解員等職位,今年3月又被聘任為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委任學術顧問及民政事務總署大廈管理義務調解主任調解員之職。
同時,鄧川云先生也是一個調解課程的訓練導師和建筑物管理實務講座的講師,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獅子會、青年商會、區議員辦事處及香港調解服務有限公司提供講座服務。他於1989年起,便協助大廈業主組織成立互助委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幫助各業主推行大廈的維修工程,並作為8座分別位於香港島、九龍及元朗區的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顧問,是多個行業工會和社團,包括水務、交通運輸和家長教師會的顧問和成員,還參與了眾多與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的談判活動。
諸多的名目加身以及顧問諮詢,是大家對鄧川云先生的認可,也是作為一個調解員自我塑造之路的堅守,這一路走來,榮譽的另一面是不為人知的付出。他是民間“和事佬”,更是群眾的專業調解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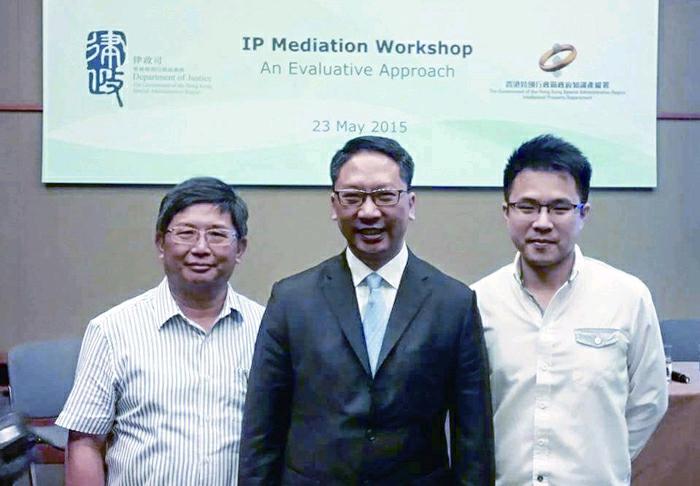
非典型性調解員的創新邏輯
香港自2010年實施“實務指示31”後,大部分民事訴訟需先透過調解解決爭議,因此對調解的需求量也日漸增多。據鄧川云先生介紹,雖然調解員的薪酬相當可觀,擁有個別專業資格的調解員時薪更是超出一般職業。但目前在港從事調解員學習的大概有一萬餘名學員,登記註冊的有兩千左右,但真正從事調解員工作的大概只有幾十個人。
由此不難想象,調解員並不像字面所理解的這般容易,他不僅僅是調和的中間人,更代表著其背後的專業、技能、積累甚至更多。
在採訪互動中,我們了解到鄧川云先生在作為社會工作者、調解員的同時,也在教育中心進行教學活動,並在修習法學碩士。他在提及他作為調解員的專業技能時,特別提到了有關創新與創意。這一點大大出乎了我們的意料,他為我們展現了調解員的另一面及其獨有的邏輯方式。
借此,他為我們介紹了一個因為物業施工拆除與清掃問題,導致業主與租客僵持了5年之久的民事糾紛。這期間雙方多次調解無果,甚至即將付諸法庭。要知道,在香港請律師進行法律公文式通知,是需要雙方各付費用,雖只是一封書面信箋,但花費不菲,如果鬧上法庭,那所需花費更是令人咋舌。
可正如鄧川云先生所說,99.9%的民事糾紛大都源於一時的氣憤,轉而困於鉆牛角尖式的思維之中,從而陷入迷局。當局者迷,旁觀者雖較為明晰,但如何勸解卻是一門學問,要不然雙方也不會執拗到如今。而他卻跳出框框,獨辟蹊徑,從雙方的租約入手,一句話的事情便將這個給雙方添堵了5年,甚至將損失雙方巨大利益的頑疾給摘除了,讓一眾同業者不得不佩服至極。
他還談到自己有一門絕招,但並不適用所有人。調解員擁有很明確的職業規范,公正平和的化解,卻不能憑借自己的專業資格直接給予建議,但他卻用獨特的“罵人方式”,以問題式的引導,去點醒陷入困局中的人群,讓人瞬間獲得釋然。
偏愛和諧之景
做一時的“和事佬”並不難,但十年如一日地不斷去為他人調解問題,並在群眾中擁有極好口碑的人,並不會太多,這門職業存在著太多的誤解,明面上的收入,往往容易讓人忽視背後為之付出的艱辛。
談到家人的時候,鄧川云先生略帶自嘲地表明,由於工作的原因導致他常年無法分出很多的時間去陪伴家人,導致愛人略有不滿情緒。我們了解到,他雖然已於社會工作退休,但仍時常會繼續其中的部分工作;他經常義務幫助業主進行維修工作,並免費普及相關法律知識以及合同審閱等;同時他還在香港理工大學做義工,為學生們講授理論與實務等相關課程內容。
在問及其有關遠大理想之時,他卻毫不猶豫地一口否決了,十分明確地說明自己並無鴻鵠之志,只不過是“能做多少做多少”盡力而為。作為調解員,他每次都會接收到很多的躁動與負面情緒,並不是說他不會受影響,也會有情緒囤積到想發泄的時候,但他會選擇用唱歌的形式去紓解,也不管是否好聽,自嘲道這種發傻唱歌的瘋癲之舉便是他最佳的緩壓途徑。
在我們認為樂觀積極如鄧川云先生,做調解員的話必然是得心應手之時,他卻說道做調解員最大的難處,便是理論與實際的差距,現實中總需要保持中立的態度,將個人的價值觀刻意拋開,時刻保持客觀的立場,其實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他卻十分享受矛盾被和平化解那一刻的和諧之景。
雖然鄧川云先生一再表明自己是個沒有大理想的小人物,可我們從他的工作中感受到了“為人民服務”“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胸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