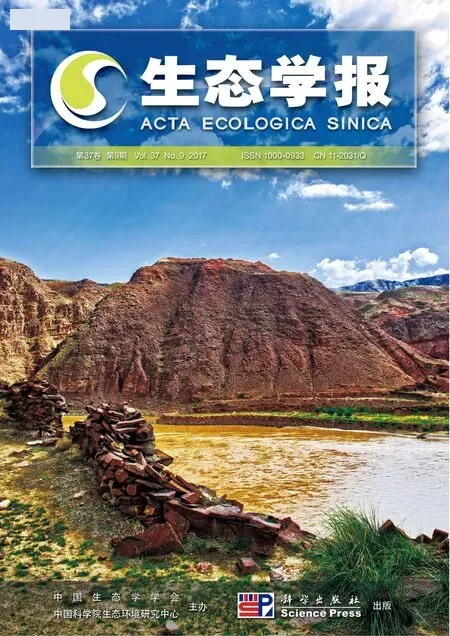放牧對鄂爾多斯高原油蒿草場生物量及植被-土壤碳密度的影響
高 麗,朱清芳,閆志堅,王育青,侯向陽,*,戴雅婷
1 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草原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10 2 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1
?
放牧對鄂爾多斯高原油蒿草場生物量及植被-土壤碳密度的影響
高 麗1,2,朱清芳1,閆志堅1,王育青1,侯向陽1,*,戴雅婷1
1 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草原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10 2 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1
以圍封保護(hù)和自由放牧油蒿草場為研究對象,通過野外調(diào)查與室內(nèi)分析,研究了圍封和放牧條件下沙地草場生物量和植被-土壤碳密度。結(jié)果表明:(1)自由放牧使油蒿群落中植物種類增加,但降低了植物群落蓋度。自由放牧不僅導(dǎo)致油蒿草場地上、地下總生物量降低,也使得油蒿地上、地下生物量占群落地上、地下總生物量的比例減小。生長季自由放牧樣地凋落物生物量顯著大于圍封保護(hù)樣地(P<0.05);(2)圍封保護(hù)樣地植被碳密度大于自由放牧樣地,土壤碳密度卻小于自由放牧樣地,但兩個樣地間差異不顯著(P>0.05);(3)油蒿草場90%以上的碳儲存于土壤中,圍封保護(hù)樣地和自由放牧樣地油蒿草場土壤碳密度占植被-土壤系統(tǒng)碳密度的91%、93%;(4)圍封保護(hù)油蒿草場碳密度為2.29 kg/m2,自由放牧油蒿草場碳密度為2.68 kg/m2,兩個樣地間差異不顯著,自由放牧對油蒿草場碳密度影響不大。
植物生物量;碳密度;油蒿;圍封;放牧
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儲量是估算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吸收和排放含碳?xì)怏w數(shù)量的關(guān)鍵要素[1],因而是全球氣候變化研究中的重要問題[2]。準(zhǔn)確評估不同類型植被和土壤的碳存儲能力,是制定合理政策措施,提高植被和土壤的碳吸收速度,增加陸地碳存儲量的基礎(chǔ)[3- 4]。生物量是反映群落或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強弱的重要指標(biāo)[5],其直接反映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chǎn)者的物質(zhì)生產(chǎn)量,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chǎn)力的重要體現(xiàn)[6],生物量是研究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儲量的基礎(chǔ)數(shù)據(jù)。
半灌木油蒿(Artemisiaordosica)草場是鄂爾多斯高原地區(qū)重要的沙地天然放牧場,主要分布在本區(qū)的毛烏素沙地和庫布齊沙地上,常見于固定、半固定沙地[7]。油蒿草場占整個鄂爾多斯高原總面積的47.3%,占鄂爾多斯高原沙地總面積的73.4%,其對鄂爾多斯高原的系統(tǒng)穩(wěn)定性起著關(guān)鍵的作用[8]。但是在21世紀(jì)之前,由于過度放牧、農(nóng)田開墾、大面積采薪等不合理利用,導(dǎo)致油蒿草場嚴(yán)重退化沙化[9]。2000年,國家“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以及后期的飛播造林、沙區(qū)封育等生物和工程措施加上地方政府的“禁牧、休牧、輪牧”政策的實施,使得沙地草場呈現(xiàn)“整體遏制,局部好轉(zhuǎn)”的局面[10- 11]。目前,關(guān)于油蒿草場碳儲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沙地類型植被和土壤碳儲量方面[12- 14],而有關(guān)圍封和放牧條件下油蒿草場碳儲量研究還未見報道。大量實驗觀測表明,退耕還草、圍封草場和人工種草等措施可以促進(jìn)退化草地土壤有機碳的恢復(fù)和積累,具有固定大氣CO2的能力[15]。本研究以圍封保護(hù)和自由放牧油蒿草場為研究對象,開展圍封和放牧條件下沙地草場生物量和植被-土壤碳密度的研究,為進(jìn)一步估算鄂爾多斯高原沙地油蒿草場的碳儲量及固碳潛力,更好地評價沙地草場在我國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循環(huán)中的作用提供參考數(shù)據(jù)。
1 研究地區(qū)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點和樣地概況
研究地點設(shè)在農(nóng)業(yè)部鄂爾多斯沙地草原生態(tài)環(huán)境重點野外科學(xué)觀測試驗站,位于鄂爾多斯高原北部庫布齊沙漠東段,地處40°19′N,109°59′E,海拔1036 m。該區(qū)屬于中溫帶大陸性季風(fēng)氣候,年平均氣溫6.5℃,最低氣溫-32.8℃,最高氣溫39.1℃,年平均降雨量350—380 mm,年蒸發(fā)量2093 mm,無霜期145 d。立地類型主要有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流動沙地和丘間低地。土壤類型為風(fēng)沙土。
20世紀(jì)90年代初,試驗區(qū)內(nèi)大部分為半流動沙地、流動沙地,植被以油蒿和沙米(Agriophyllumsquarrosum)為主,油蒿數(shù)量少,呈不均勻分布,沙米在雨季才能出苗[8]。1990—1994年,研究者們通過補播固沙耐牧草種沙打旺(Astragalusadsurgens)、中間錦雞兒(Caraganaintermedia)、羊柴(Hedysarumlaeve)和油蒿改良半流動沙地、流動沙地草場,形成了良好的打草場或放牧場。在植被恢復(fù)的過程中,沙打旺、羊柴逐漸衰退死亡,中間錦雞兒僅有少數(shù)留存,最終形成了以油蒿為建群種的固定沙地。本研究中,圍封保護(hù)樣地和自由放牧樣地是在實施補播后建立的。圍封保護(hù)樣地面積300 m×300 m,采取圍欄封育,不放牧;自由放牧樣地面積300 m×200 m,一直作為冬春放牧場,放牧牲畜以山羊為主,放牧?xí)r間為當(dāng)年生長季結(jié)束到次年植物返青期前。
兩個樣地均以油蒿為建群種,伴生種以霧冰藜(Bassiadasyphylla)、豬毛菜(Salsolacollina)、刺沙蓬(Salsolapestifer)、苦豆子(Sophoraalopecuroides)、達(dá)烏里胡枝子(Lespedezadavurica)等喜沙植物為主。
1.2 植物生物量測定與植物樣品采集及制備

圖1 樣方分布圖Fig.1 Location map of six 5m×5m quadrats
2011年5月,在圍封保護(hù)固定沙地樣地和自由放牧固定沙地樣地典型地帶,根據(jù)機械布點法自西向東按 1、2、3…順序依次標(biāo)號[16],選擇 1、13、25、29、41、53號6個5 m×5 m樣方作為測量樣方(圖1)。從5月到10月,每月對6個樣方進(jìn)行植物群落調(diào)查。灌木和半灌木采用標(biāo)準(zhǔn)叢法測定[16],依其叢幅和高度相對地劃分為大、中、小3個等級組,每一等級組內(nèi),選擇生長于固定觀測樣方外的3個標(biāo)準(zhǔn)叢,分別齊地面刈割。在6個5 m×5 m的樣方中分別作1個1 m×1 m的草本樣方,分種記錄蓋度、株樹、高度后,齊地面刈割。采集完地上活體部分后,將每個1 m×1 m的樣方中凋落物收集裝袋。在地上部分刈割后,取50 cm×50 cm×70 cm土方,分5層取地下部分植物樣品(0—10、10—20、20—30、30—50、50—70 cm)。
植物樣品帶回室內(nèi)后,迅速清除塵土。油蒿植株地上部分分老枝、新枝、葉、果實,稱量鮮重;油蒿根系地下部分帶回室內(nèi)用水洗分離法獲得根系樣品,分細(xì)根(<2 mm)和粗根(>2mm)分層裝入紙袋;草本層分種稱量鮮重;立枯物和凋落物分別稱量鮮重。所有植物樣品置于鼓風(fēng)干燥箱中65℃烘干至恒重后,稱量干重。稱量后的樣品,用粉碎粒度較大的植物粉碎機先粗碎,充分混合均勻,然后用細(xì)碎的不銹鋼植物粉碎機粉碎至100目,全部移入密封塑料袋中封好待測。
1.3 土壤樣品采集及制備
8月,在圍封保護(hù)樣地、自由放牧樣地各挖取3個土壤剖面,在每個剖面的3個不同位置分0—5、5—10、10—20、20—30、30—50、50—70 cm土層取樣,將每個剖面每層土樣混合,做為3次重復(fù),用于測定土壤有機碳。同時采用環(huán)刀取樣,用于測定土壤容重。
剖面土壤樣品取回室內(nèi)后,平鋪于干凈白紙上,捏碎大塊土粒,去除石塊和草根等雜物,自然風(fēng)干,過0.15 mm篩用以測定土壤有機碳。環(huán)刀中的土樣取出,裝入鋁盒中,置于鼓風(fēng)干燥箱中105℃烘干至恒重,稱量干重。
1.4 樣品分析方法
植物和土壤全碳含量測定采用重鉻酸鉀、硫酸氧化-外加熱法[17]。
1.5指標(biāo)計算1.5.1 油蒿地上生物量
以下計算公式均參照《陸地生物群落調(diào)查觀測與分析》[18]。
(1) 綠色部分的生物量BG:

(1)
式中,BG為綠色部分生物量(g/m2);Gl為大叢組油蒿每叢平均重量(g);Nl為大叢油蒿的叢數(shù)(叢);Gm為中等油蒿每叢平均重量(g);Nm為中等油蒿的叢數(shù)(叢);Gs為小叢組油蒿每叢平均重量(g);Ns為小叢油蒿的叢數(shù)(叢);A為樣地面積,25 m2。
(2) 木質(zhì)部分的生物量BV:

(2)
式中,BV為木質(zhì)部分生物量(g/m2);Vl為大叢組油蒿每叢平均重量(g);Nl為大叢油蒿的叢數(shù)(叢);Vm為 中等油蒿每叢平均重量(g);Nm為中等油蒿的叢數(shù)(叢);Vs為小叢組油蒿每叢平均重量(g);Ns為小叢油蒿的叢數(shù)(叢);A為樣地面積,25 m2。
1.5.2 植被碳密度
植株碳含量乘以單位面積生物量,即得出活體植被碳密度。用測得的凋落物碳含量,乘以凋落物生物量,計算出凋落物碳密度。
1.5.3 土壤有機碳密度
土壤有機碳密度是指單位面積一定深度的土層中土壤有機碳的儲量,由于排除了面積因素的影響而以土體體積為基礎(chǔ)來計算,土壤碳密度已成為評價和衡量土壤中有機碳儲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指標(biāo)[19]。
某一土層i的有機碳密度SOCi(kg/m2)計算公式如下:
SOCi=CiDiEi(1-Gi)/10
(3)
式中,Ci為土壤有機碳含量(%),Di為容重(g/cm3);Ei為土層厚度(cm);Gi為大于2 mm的石礫所占的體積百分比(%)。本研究中土壤為風(fēng)沙土,Gi=0,所以公式(1)可以簡化為:
SOCi=CiDiEi/10
(4)
如果某一土體的剖面由k層組成,那么該剖面的有機碳密度SOCt的計算公式為:
(5)
1.6 數(shù)據(jù)分析
應(yīng)用Microsoft Excel 2003對植物生物量、植被碳密度、土壤碳密度等數(shù)值計算和曲線圖繪制。利用線性混合模型原理和SAS軟件Proc mixed程序?qū)蓚€樣地植物生物量、植被碳密度、土壤碳密度進(jìn)行比較分析。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物種組成
圍封保護(hù)樣地植被蓋度60%,共有植物26種。灌木種類有油蒿、白沙蒿和小葉錦雞兒共3種;草本植物共23種,占圍封保護(hù)樣地總種數(shù)的88.46%,其中藜科8種,菊科5種,豆科4種,禾本科2種、蘿藦科2種、大戟科1種、唇形科1種、紫葳科1種、旋花科1種、蒺藜科1 種(表1)。

表1 植物群落物種組成特征
Ⅰ:圍封保護(hù)樣地 Enclosed plot;Ⅱ:自由放牧樣地 Grazed plot
自由放牧樣地植被蓋度45%,共有植物28種,占總種數(shù)的84.85%,灌木種類有油蒿、白沙蒿和中間錦雞兒共3種;草本種類共25種,占自由放牧樣地總種數(shù)的89.29%,其中藜科8種,菊科5種,豆科4種、禾本科4種、蘿藦科3種,大戟科1種、唇形科1種、紫草科1種、旋花科1種。放牧使群落中草本植物種類增加,但卻降低了植物群落蓋度。

圖2 生長季大氣溫度和土壤質(zhì)量含水量 Fig.2 Air temperature and soil gravimetric water content in the growing season
2.2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地上生物量
圍封保護(hù)樣地和自由放牧樣地油蒿群落地上生物量季節(jié)動態(tài)呈雙峰型。5月,水分條件為生長季最好(圖2),但溫度較低,但兩個樣地油蒿群落地上生物量處于較低水平;6月,兩個樣地地上生物量均出現(xiàn)一個微弱的小峰,由于受土壤水分較低的影響,兩個樣地地上生物量增幅不大;在植物生長旺盛的7月,高溫低濕的環(huán)境條件,使得兩個樣地地上生物量較6月大幅下降,尤其是自由放牧樣地生物量降到季節(jié)最小值;8月,土壤含水量增大,自由放牧樣地地上生物量大幅增加,達(dá)到季節(jié)最大值,而圍封保護(hù)樣地地上生物量降到季節(jié)最低值,分析原因是圍封保護(hù)樣地油蒿地上生物量占群落總地上生物量83.10%(表2),所以群落生物量大小由油蒿種群生物量大小決定,而油蒿在7月干旱條件下,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光合產(chǎn)物積累減少,導(dǎo)致8月生物量出現(xiàn)最小值,而自由放牧樣地油蒿地上生物量只占群落總地上生物量的61.74%,群落生物量由油蒿和草本層共同決定,草本層生物量通常在8月達(dá)到最大,加上8月較好的水分條件,因此自由放牧樣地地上生物量最大值出現(xiàn)在8月;9月,自由放牧樣地大多數(shù)草本層植物枯萎,造成地上生物量驟降,圍封保護(hù)樣地受益于8月相對較高的土壤含水量,油蒿光合產(chǎn)物積累增加,使得地上生物量在9月達(dá)到最大值;10月,溫度降到生長季最低,油蒿生長減緩,并逐漸枯黃,地上生物量減小(圖3)。
5月、7月、9月、10月圍封保護(hù)樣地地上生物量顯著大于自由放牧樣地,8月自由放牧樣地顯著大于圍封保護(hù)樣地,6月兩個樣地差異不顯著。兩個樣地地上生物量生長季均值為:圍封保護(hù)樣地((237.40±50.49) g/m2)極顯著大于自由放牧樣地((165.96±47.55) g/m2)(P<0.01)。自由放牧不僅導(dǎo)致油蒿草場地上總生物量降低,也使得油蒿地上生物量占地上總生物量的比例減小。

表2 兩個樣地油蒿地上生物量占群落總地上生物量的比例/%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異顯著(P<0.05)
2.3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地下生物量
圍封保護(hù)樣地地下生物量從5月到8月一直在下降(圖4),9月出現(xiàn)小幅增加,10月又降低;自由放牧樣地地下生物量從5月到7月處于下降狀態(tài),8月大幅增加,達(dá)到季節(jié)最大值,9月地下生物量驟降,10月又有小幅增長。圍封保護(hù)樣地地下生物量最大值出現(xiàn)在5月,最小值出現(xiàn)時間與地上生物量最小值出現(xiàn)時間一致;自由放牧樣地地下生物量與地上生物量最大值、最小值出現(xiàn)時間相同。

圖3 兩個樣地生長季群落地上生物量 Fig.3 Aboveground biomass of communities in the growing season in two plots

圖4 兩個樣地生長季群落地下生物量 Fig.4 Belowground biomass of communities in the growing season in two plots
7月、9月圍封保護(hù)樣地地下生物量顯著大于自由放牧樣地,其余月份兩個樣地差異不顯著。地下生物量生長季均值圍封保護(hù)樣地((113.36±34.22) g/m2)顯著大于自由放牧樣地((73.37±27.35) g/m2)(P<0.05)。圍封保護(hù)樣地油蒿地下生物量占群落總地下生物量98.71%,自由放牧樣地油蒿地下生物量占群落總地下生物量89.94%(表3)。自由放牧不僅導(dǎo)致油蒿草場地下總生物量降低,也使得油蒿地下生物量占地下總生物量的比例減小。

表3 兩個樣地生長季油蒿地下生物量占群落總地下生物量的比例/%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異顯著(P<0.05)

圖5 兩個樣地生長季群落凋落物生物量 Fig.5 Litter biomass of communities in the growing season in two plots
2.4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凋落物生物量
圍封保護(hù)樣地和自由放牧樣地凋落物生物量季節(jié)動態(tài)呈雙峰曲線(圖5),圍封保護(hù)樣地曲線較平緩,自由放牧樣地曲線起伏較大。兩個樣地峰值均出現(xiàn)在7月和10月。通常凋落物生物量在生長季末期(10月)出現(xiàn)峰值。而本項研究中在植物生長旺期(7月)出現(xiàn)一個小的峰值,分析其原因是7月環(huán)境條件呈現(xiàn)出高溫低濕的特點,植物在干旱條件下出現(xiàn)萎蔫甚至死亡現(xiàn)象,導(dǎo)致凋落物生物量增加。生長季,自由放牧樣地凋落物生物量(243.72±76.68)均值顯著大于圍封保護(hù)樣地(181.11±19.43)(P<0.05)。
2.5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植物碳含量
植物碳含量是計算植物碳儲量的基本參數(shù),其反映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固定貯存碳元素的能力。不同植物種類、不同植物構(gòu)件碳含量不同。本研究于植物生長旺盛期(8月)采樣測定了油蒿和主要草本植物的地上和地下部分碳含量(表4)以及凋落物碳含量(37.86%)。
2.6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植被碳密度
由圍封保護(hù)樣地和自由放牧樣地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凋落物生物量及植物碳含量計算得出圍封和放牧條件下油蒿草場植被碳密度。
由圖6可以看出,兩個樣地油蒿草場植被碳密度季節(jié)動態(tài)與地上生物量季節(jié)動態(tài)(圖3)一致。8月,自由放牧樣地油蒿草場植被碳密度顯著大于圍封保護(hù)樣地,其它月份差異不顯著。兩個樣地油蒿群落植被碳密度生長季平均值差異不顯著(P>0.05),分別為:圍封保護(hù)樣地(0.21±0.03) kg/m2,自由放牧樣地(0.19±0.03) kg/m2。

表4 油蒿和草本層主要植物地上和地下部分碳含量/%
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異顯著(P<0.05)

圖6 兩個樣地植物群落碳密度Fig.6 Carbon density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two plots
2.7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土壤有機碳密度
由公式(4)、(5)和表5中的數(shù)據(jù)計算得出圍封保護(hù)樣地和自由放牧樣地0—70 cm深度土壤有機碳密度分別為(2.08±0.41) kg/m2,(2.49±0.36) kg/m2,兩個樣地間差異不顯著(P>0.05)。
2.8 圍封和放牧油蒿草場植被-土壤系統(tǒng)碳密度
表6可以看出,圍封保護(hù)樣地和自由放牧樣地油蒿草場土壤碳密度占植被-土壤系統(tǒng)碳密度的91%、93%,可見,油蒿草場90%以上的碳儲存于土壤中。圍封保護(hù)樣地植被碳密度大于自由放牧樣地,土壤碳密度卻小于自由放牧樣地。圍封保護(hù)油蒿草場碳密度為2.29 kg/m2,自由放牧油蒿草場碳密度為2.68 kg/m2,兩個樣地間差異不顯著。自由放牧對油蒿草場碳密度影響不大。
3 討論和結(jié)論
放牧作為人類對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管理和利用的主要手段,是影響草地的最主要的人為干擾方式[20]。放牧通過牲畜的啃食、踐踏和物質(zhì)歸還過程干擾草場環(huán)境,一方面使群落在結(jié)構(gòu)上出現(xiàn)破口,生境異質(zhì)性增加;另一方面也使優(yōu)勢種群的競爭勢受到抑制,為新物種的侵入創(chuàng)造了條件[21]。在本項研究中自由放牧樣地中植物種數(shù)多于圍封保護(hù)樣地。自由放牧樣地中,牲畜的采食相對降低了優(yōu)勢植物油蒿的競爭勢,為其他植物種類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了條件。一般認(rèn)為,隨著放牧率的增加,植物的再生能力降低,植物的葉量、分蘗數(shù)、株高、生長速度、單株干物質(zhì)和總生物量均下降[22- 23]。通常圍封禁牧草地生物量要大于放牧草地。本項研究中圍封保護(hù)樣地地上、地下生物量顯著大于自由放牧樣地,自由放牧不僅導(dǎo)致油蒿草場地上、地下總生物量降低,也使得油蒿地上、地下生物量占群落地上、地下總生物量的比例減小。油蒿之所以能在鄂爾多斯高原沙地成為主要建群種,除了其本身具有耐干旱、耐貧瘠,根系發(fā)達(dá)等生理特性外,植物體內(nèi)所含有的化學(xué)成分對其他植物有抑制作用也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24]。自由放牧樣地中的放牧采食行為,不僅抑制了油蒿的生長,而且降低了油蒿對草本植物的化感作用,所以導(dǎo)致自由放牧樣地中油蒿種群生物量低于圍封保護(hù)樣地,而自由放牧樣地中草本層植物生物量大于圍封保護(hù)樣地。草地凋落物生物量的主要控制因素分別為地上生物量、土壤碳貯量和降水量[25],所以通常圍封樣地凋落物生物量大于放牧樣地,而在本研究中生長季自由放牧樣地凋落物生物量顯著大于圍封保護(hù)樣地。不同生境的植被組成差異是導(dǎo)致凋落物量及凋落物組成差異的重要因素[26]。本研究中放牧?xí)r間為當(dāng)年生長季結(jié)束到次年植物返青期前,在自由放牧樣地中,生長季草本層植物基本未被采食,生長季結(jié)束后,草本層一年生植物整株轉(zhuǎn)化為凋落物,而圍封保護(hù)樣地中,草本層植物較少,凋落物主要來自于脫落的油蒿葉、果實及嫩莖。因此,自由放牧樣地中較高的立枯量所形成的較強的凋落物截獲能力可能是導(dǎo)致自由放牧樣地凋落物生物量顯著大于圍封保護(hù)樣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5 兩個樣地土壤容重、土壤有機質(zhì)、土壤有機碳含量
同行同一指標(biāo)不同字母表示差異顯著(P<0.05)

表6 兩個樣地植被-土壤系統(tǒng)碳密度
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異顯著(P<0.05)
植物的碳含量相對比較穩(wěn)定,所以放牧主要通過生物量的改變而影響植被的碳密度,通常放牧導(dǎo)致生物量及植被碳密度降低。本研究中自由放牧導(dǎo)致地上總生物量降低,從而降低了植被碳密度。放牧對土壤有機碳含量的影響仍存在較大爭議。目前,放牧與土壤碳密度的關(guān)系,尤其是在不同區(qū)域(受植被類型、土壤本底和放牧牲畜種類)表現(xiàn)很不一致[27]。通常,輕度放牧對草地土壤的影響相對較小[28-32],而過度放牧將顯著降低土壤碳氮貯量[29-30,33-34]前者主要通過促進(jìn)草地營養(yǎng)循環(huán)和植被更新來提高草地干物質(zhì)生產(chǎn)、營養(yǎng)循環(huán)、碳氮貯存[27]。在內(nèi)蒙古典型草地,我國學(xué)者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輕度放牧將提高典型草地和荒漠草地土壤碳和氮貯量、而重度放牧將降低土壤碳氮貯量[30-31,33]。加強草地管理,恢復(fù)退化草地可以有效地增加草地土壤有機碳儲量[35-38]。在本項研究中,圍封保護(hù)樣地植物碳密度大于自由放牧樣地,土壤碳密度卻小于自由放牧樣地。圍封保護(hù)油蒿草場碳密度為2.29 kg/m2,自由放牧油蒿草場碳密度為2.68 kg/m2,兩個樣地間差異不顯著,所以自由放牧對油蒿草場碳密度影響不大。已有研究表明,適度的放牧是保持沙地油蒿群落穩(wěn)定的關(guān)鍵,即一方面要限制過度放牧的情況發(fā)生,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封閉保護(hù),使固定沙地油蒿群落向下一個演替階段發(fā)展,導(dǎo)致油蒿群落的衰敗[39]。所以,無論是從可持續(xù)利用角度還是碳固持方面來看,適度放牧是固定沙地油蒿草場最佳利用方式。
[1] Valentini R, Matteucci G, Dolman A J, Schulze E D, Rebmann C, Moors E J, Granier A, Gross P, Jensen N O, Pilegaard K, Lindroth A, Grelle A, Bernhofer C, Grünwald T, Aubinet M, Ceulemans R, Kowalski A S, Vesala T, Rannik ü, Berbigier P, Loustau D, Guδmundsson J, Thorgeirsson H, Ibrom A, Morgenstern K, Clement R, Moncrieff J, Montagnani L, Minerbi S, Jarvis P G. Respiration as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carbon balance in European forests. Nature, 2000, 404(6780): 861- 865.
[2] 李克讓, 王紹強, 曹明奎. 中國植被和土壤碳貯量. 中國科學(xué)(D輯), 2003, 33(1): 72- 80.
[3] 呂超群, 孫書存. 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碳密度格局研究概述. 植物生態(tài)學(xué)報, 2004, 28(5): 692- 703.
[4] White R P, Murray S, Rohweder M. Pilot Analysis of Global Ecosystems: Grassland Ecosystems. Washington D C: 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2000.
[5] Odum E P. Base of Ecology. Beijing: People Education Press, 1971.
[6] 張峰, 上官鐵梁, 李素珍. 關(guān)于灌木生物量建模方法的改進(jìn). 生態(tài)學(xué)報, 1993, 12(6): 67- 69.
[7] 李博. 內(nèi)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自然資源與環(huán)境研究. 北京: 科學(xué)出版社, 1990.
[8] 李博, 桂榮, 王國賢. 鄂爾多斯高原沙質(zhì)灌木草地絨山羊試驗區(qū)研究成果匯編. 呼和浩特: 內(nèi)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5.
[9] 王慶鎖, 陳仲薪, 史振英. 油蒿草場的保護(hù)與改良. 生態(tài)學(xué)雜志, 1995, 14(4): 54- 57.
[10] 王玉華, 楊景榮, 丁勇, 寧爭平, 張宏林. 近年來毛烏素沙地土地覆被變化特征. 水土保持通報, 2008, 28(6): 53- 57.
[11] 閆峰, 吳波, 王艷姣. 2000—2011年毛烏素沙地植被生長狀況時空變化特征. 地理科學(xué), 2013, 33(5): 602- 608.
[12] 李春萍. 內(nèi)蒙古毛烏素沙地不同生境油蒿(ArtemisiaordosicaKrasch.)灌叢地碳動態(tài)研究[D]. 北京: 中國科學(xué)院植物研究所, 2006.
[13] 丁越巋, 楊劼, 宋炳煜, 呼格吉勒圖, 張琳. 不同植被類型對毛烏素沙地土壤有機碳的影響. 草業(yè)學(xué)報, 2012, 21(2): 18- 25.
[14] 黃奇. 烏審旗區(qū)域植被碳儲量估算[D]. 呼和浩特: 內(nèi)蒙古大學(xué), 2014.
[15] 郭然, 王效科, 逯非, 段曉男, 歐陽志云. 中國草地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固碳現(xiàn)狀和潛力. 生態(tài)學(xué)報, 2008, 28(2): 862- 867.
[16] 中國生態(tài)系統(tǒng)研究網(wǎng)絡(luò)科學(xué)委員會. 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物觀測規(guī)范. 北京: 中國環(huán)境科學(xué)出版社, 2007.
[17] 鮑士旦. 土壤農(nóng)化分析. 北京: 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 2002.
[18] 董鳴. 陸地生物群落調(diào)查觀測與分析. 北京: 中國標(biāo)準(zhǔn)出版社, 1996.
[19] 解憲麗, 孫波, 周慧珍, 李忠佩. 不同植被下中國土壤有機碳的儲量與影響因子. 土壤學(xué)報, 2004, 41(5): 687- 699.
[20] Rowe R J. Environmental and geometric drivers of small mammal diversity along elevational gradients in Utah. Ecography, 2009, 32(3): 411- 422.
[21] 楊利民, 韓梅, 李建東. 中國東北樣帶草地群落放牧干擾植物多樣性的變化. 植物生態(tài)學(xué)報, 2001, 25(1): 110- 114.
[22] 賈子毅. 毛烏素沙地定居放牧草場植物群落分類與退化梯度分析[D]. 北京: 中國林業(yè)科學(xué)研究院, 2008.
[23] 趙哈林, 張銅會, 趙學(xué)勇, 周瑞蓮. 放牧對沙質(zhì)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組分的影響. 應(yīng)用生態(tài)學(xué)報, 2004, 15(3): 420- 424.
[24] 于鳳蘭, 馬茂華, 孔令韶. 油蒿揮發(fā)油的化感作用研究. 植物生態(tài)學(xué)報, 1999, 23(4): 345- 350.
[25] 溫丁, 何念鵬. 中國森林和草地凋落物現(xiàn)存量的空間分布格局及其控制因素. 生態(tài)學(xué)報, 2016, 36(10): 1- 9.
[26] 羅永清, 趙學(xué)勇, 丁杰萍, 馮靜, 蘇娜, 周欣, 岳祥飛. 科爾沁沙地不同類型沙地植被恢復(fù)過程中地上生物量與凋落物量變化. 中國沙漠, 2016, 36(1): 78- 84.
[27] 何念鵬, 韓興國, 于貴瑞. 內(nèi)蒙古放牧草地土壤碳固持速率和潛力. 生態(tài)學(xué)報, 2012, 32(3): 844- 851.
[28] Frank D A, Evans R D. Effects of native grazers on grassland N cycling i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Ecology, 1997, 78(7): 2238- 2248.
[29] He N P, Zhang Y H, Yu Q, Chen Q S, Pan Q M, Zhang G M, Han X G. Grazing intensity impacts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storage of continental steppe. Ecosphere, 2011, 2(1): 1- 10.
[30] Han G D, Hao X Y, Zhao M L, Wang M J, Ellert B H, Willms W, Wang M J. Effect of grazing intensity on carbon and nitrogen in soil and vegetation in a meadow steppe in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8, 125(1/4): 21- 32.
[31] Li C L, Hao X Y, Zhao M L, Han G D, Willms W D. Influence of historic sheep grazing on vegetation and soil properties of a Desert Steppe in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2008, 128(1/2): 109- 116.
[32] 陳銀萍, 李玉強, 趙學(xué)勇, 羅永清, 尚雯. 放牧與圍封對沙漠化草地土壤輕組及全土碳氮儲量的影響. 水土保持學(xué)報, 2010, 24(4): 182- 186.
[33] Cui X Y, Wang Y F, Niu H S, Wu J, Wang S P, Schnug E, Rogasik J, Fleckenstein J, Tang Y H. Effect of long-term grazing on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in semiarid steppes in Inner Mongolia. Ecological Research, 2005, 20(5): 519- 527.
[34] Elmore A J, Asner G P. Effects of grazing intensity on soil carbon stocks following deforestation of a Hawaiian dry tropical forest.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6, 12(9): 1761- 1772.
[35] 王瑋, 鄔建國, 韓興國. 內(nèi)蒙古典型草原土壤固碳潛力及其不確定性的估算. 應(yīng)用生態(tài)學(xué)報, 2012, 23(1): 29- 37.
[36] Maia S M F, Ogle S M, Cerri C E P, Cerri C C. Effect of grassland management on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Rondnia and Mato Grosso states, Brazil. Geoderma, 2009, 149(1/2): 84- 91.
[37] Wu G L, Liu Z H, Zhang L, Chen J M, Hu T M. Long-term fencing improved soil properties and soil organic carbon storage in an alpine swamp meadow of western China. Plant and Soil, 2010, 332(1/2): 331- 337.
[38] Jones M B, Donnelly A.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emperate grassland ecosystems and the influence of management, climate and elevated CO2. New Phytologist, 2004, 164(3): 423- 439.
[39] 郭柯. 毛烏素沙地油蒿群落的循環(huán)演替. 植物生態(tài)學(xué)報, 2000, 24(2): 243- 247.
Effects of grazing on plant biomass and the carbon density of vegetation and soil in theArtemisiaordosicashrubland of the Ordos Plateau
GAO Li1, 2, ZHU Qingfang1, YAN Zhijian1, WANG Yuqing1, HOU Xiangyang1,*, DAI Yating1
1GrasslandResearch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Hohhot010010,China2GraduateSchool,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
Plant biomass and the carbon density of vegetation and soil in enclosed and grazedArtemisiaordosicashrubland of the Ordos Plateau were studied in the field and in the laborator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grazed plots supported plant communities with a higher the number of species yet lower vegetation coverage than did the enclosure plots. Grazing, moreover, reduced the overall above-and below-ground biomass of plant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proportion of above-and below-ground biomass consisting ofA.ordosica. Nevertheless, during the growing season the grazed plots produced significantly more litter biomass than did the enclosure plots (P< 0.05). When protected by enclosures, however, the carbon density of the vegetation was higher, whereas that of the soil was lower, than that under grazing; although their seasonal average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plot treatments (P> 0.05). Ninety percent of carbon storage was in the soil inA.ordosicashrubland. The percentages of carbon density of soil accounting for the vegetation-soil system were 91% in enclosed plot and 93% in grazed plot, respectively. The carbon density ofA.ordosicashrubland was 2.29 kg/m2in enclosed plot and 2.68 kg/m2in grazed plot. Grazing had little impact on carbon density of vegetation-soil inA.ordosicashrubland.
plant biomass; carbon density;Artemisiaordosica; enclosed; grazed
國家重點基礎(chǔ)研究發(fā)展計劃(973計劃)項目(2014CB138806);“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2012BAD13B07);國家國際科技合作專項項目(2013DFR30760);中央級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專項資金(1610332015008);農(nóng)業(yè)部鄂爾多斯沙地草原生態(tài)環(huán)境重點野外科學(xué)觀測試驗站項目
2016- 01- 14; 網(wǎng)絡(luò)出版日期:2016- 12- 19
10.5846/stxb201601140091
*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houxy16@126.com
高麗,朱清芳,閆志堅,王育青,侯向陽,戴雅婷.放牧對鄂爾多斯高原油蒿草場生物量及植被-土壤碳密度的影響.生態(tài)學(xué)報,2017,37(9):3074- 3083.
Gao L, Zhu Q F, Yan Z J, Wang Y Q, Hou X Y, Dai Y T.Effects of grazing on plant biomass and the carbon density of vegetation and soil in theArtemisiaordosicashrubland of the Ordos Plateau.Acta Ecologica Sinica,2017,37(9):3074- 3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