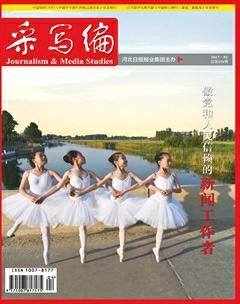以精神分析批評理論淺析《乘風破浪》
姜瑤
內(nèi)容提要:本文采用精神分析批評理論來分析《乘風破浪》這部電影。用弗洛伊德關于夢的理論和本我、自我到超我的兩個理論來分析導演創(chuàng)作動機以及人物角色自我成長過程。主演通過穿越這種近于做夢的方式,回到了父親的年輕時代,實現(xiàn)了自己與父親的和解,也實現(xiàn)了本我到超我的自我成長。
關鍵詞:精神分析批評; 乘風破浪;弗洛伊德;夢;超我
精神分析批評領域的代表人物有弗洛伊德、榮格等,主要在文學批評、電影批評等研究領域,探討無意識學說對人的行為和人性的影響。它對無意識心理對文學、文化活動、審美意識和人性觀念的影響進行研究,試圖揭示人性構成最深層的動因,并據(jù)此對社會、歷史文化做出解釋。
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講,誕生于19世紀末的電影,是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產(chǎn)物,可同時它也是一種藝術形式,與精神分析批評理論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
2017年的電影春節(jié)檔中,定義為文藝片的《乘風破浪》相對于其他三部主打“合家歡”風格的影片來講,可以說是春節(jié)檔的一股清流。《乘風破浪》主要講述的是作為賽車手的徐太浪從小非常不滿意自己父親的棍棒教育和陳舊的思維,堅持著自己所向往的賽車職業(yè)。當他比賽獲得成功的那一刻,對父親說:“終于證明了你是錯的。”志得意滿的他帶著父親駕車飛馳,突如其來的車禍,讓他穿越回了父親的年輕時代。在一系列故事中,慢慢地也見到了父親年少時的熱血和其他美好的品質(zhì),使他逐漸放下了心中的嫌隙。最后醒來,實現(xiàn)了自己與父親的和解。
一、一場“白日夢”,追尋兄弟、父子情
弗洛伊德認為,夢其實“就是一種愿望的滿足”,從這個角度上來看,《乘風破浪》可以說是導演韓寒自己的一場“夢”。在這個“夢”里,他紀念了他的好兄弟徐浪。這部電影本來預計在2018年上映,而2018年正好是中國車手徐浪離世十年祭。徐浪是一名賽車手,更是中國唯一一個在國際越野拉力賽中取得最好成績的賽車手。韓寒和徐浪兩個同樣向往賽車激情的男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這部電影就是為了紀念他,是韓寒給自己圓了一個好兄弟的夢。
在這場“夢”里,《乘風破浪》還使用了穿越的手法,使男主角穿越回了父親年輕的時代。24歲的他遇到了23歲的父親,在現(xiàn)實中和父親關系緊張的徐太浪在穿越后和年輕的父親成為了朋友。在男主角的印象中,現(xiàn)實中的父親古板、保守甚至還有些暴戾,但年輕時的父親卻是個熱愛冒險、講義氣、愛開玩笑的大男孩。也許,這也正是徐太浪心底的一個夢,他夢中的父親,就應該是這樣一個正義、開朗的大男孩。但無論是“白日夢”抑或是藝術作品,始終源于現(xiàn)實,源于內(nèi)心的動機。這也是韓寒導演內(nèi)心的一個投射,他高中退學,一度和父親關系緊張,這也是韓寒通過“白日夢”的方式,回到青蔥時代,伴隨著那時的父親,穿越時間的界線,達到了內(nèi)心與父親的和解。
二、角色自我成長之后的自我超越
影片中,徐太浪出于本能,反抗父親對他的壓制與管教,甚至將父親看作為站立在對立面的敵人,他在自己功成名就的那一刻,挑釁地望向父親,大聲說:“我就是要證明你是錯的。”他與社會主流所傳承的“孝道”背道而馳,他不顧父親的身體狀況、不顧父親眼中有些欣慰的目光,當他回顧起父親,只有種種的不好,他只遵從于自己的內(nèi)心,反抗父親的執(zhí)念,這是人的本我,父親在他心中,就是出于本能的反抗。而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超乎于本我,自我屬于人的精神中較高的一層,它是本我和社會現(xiàn)實之間沖突的調(diào)解者,其活動服從于“現(xiàn)實的原則”,在與年輕時的父親相處時,徐太浪從一開始的仇恨父親,到他們一起經(jīng)歷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后,慢慢地他卻成了認同父親的好哥兒們。而當他從昏迷中醒來,面對父親的那一刻,眼中已沒有了責備和怨恨,有的只是對父親的理解和愛,此時他與父親達到了和解,他也實現(xiàn)了自己從自我到超我的過程。
而《乘風破浪》整部電影的結構、角色、布景與情懷都讓人可以聯(lián)想到影片《新難兄難弟》,兩部電影都是源于導演內(nèi)心的愿景,都是對過去的人、事、景的追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導演的自我成長亦或是影片中角色的自我成長,都實現(xiàn)了對自身的自我超越。
(作者系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