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少年,眼望藍(lán)天
薛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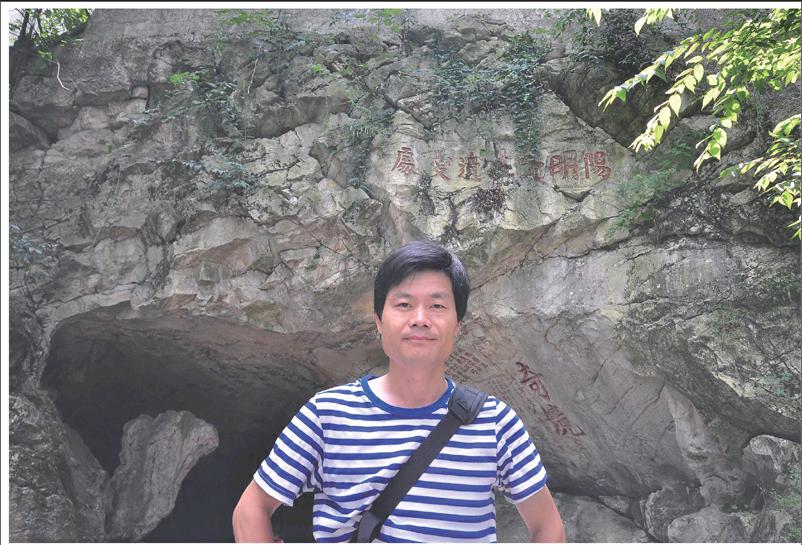
那年經(jīng)濟(jì)的強(qiáng)風(fēng)吹遍了祖國(guó)大地,那年我們祖祖輩輩種麥子的土地上長(zhǎng)出了陌生的經(jīng)濟(jì)作物——煙葉,那年父親因?yàn)榭緹熑~技術(shù)出色而被別的村莊請(qǐng)去當(dāng)“老師”。烤煙葉五天一個(gè)周期,父親五天才能回來(lái)。
有一天,我想父親了,母親便鼓勵(lì)我騎著自行車(chē)去找他。這在今天看來(lái)真是匪夷所思,那畢竟是我從未走過(guò)的二十里山路啊。我一路打聽(tīng),一路忐忑,將近日暮時(shí)分終于趕到了那個(gè)名叫“蘆家河”的小村莊。
回想童年和少年的分野,我的回憶里似乎只有這次的出發(fā)顯得有些莽撞。第一次獨(dú)自走出村莊,第一次爬上高高的山梁俯視鄰村,第一次感受到公路的神奇,翻山越嶺又走街過(guò)巷,彎彎曲曲又不停不歇,它要通往哪里,它能通向哪里?
忘了是1989年,還是1990年,是世界在變化,或者是我在變化,又或者是我和世界的關(guān)系在變化?我茫然不知。原來(lái)我是多么沉迷于打尜(gá,把木棍刻成兩頭尖、中間粗、長(zhǎng)約4厘米的形狀,再用木板敲擊,比賽誰(shuí)打得遠(yuǎn))、甩寶、跳房子之類(lèi)的游戲,好像是忽然之間,童年時(shí)代的游戲?qū)ξ也辉儆形α恕T?jīng)的小伙伴們也都有了些焦灼的模樣,有的已經(jīng)輟學(xué),有的開(kāi)始下地干活,再玩那些游戲都很難湊齊人手了。我想著站在山頂望不到盡頭的公路,開(kāi)始想象外面的世界。
想象沒(méi)有翅膀也不行,而我能借助的工具實(shí)在有限,只有書(shū)。
我開(kāi)始親近愛(ài)讀書(shū)的小伙伴了,睜大渴望的眼睛到處找書(shū),每次發(fā)下新鮮的課本,也被我早早地翻了個(gè)遍,還是不夠。鄰居家的哥哥不知從哪里弄來(lái)幾本雜志,看得我如癡如醉,干脆要回了家。后來(lái)又聽(tīng)說(shuō),五里路外的村莊有家小書(shū)店,專(zhuān)賣(mài)那個(gè)時(shí)代流行的小人書(shū),也就是連環(huán)畫(huà)。這個(gè)消息無(wú)異于旱地驚雷!于是,我們循著雷聲找去,毫無(wú)抵抗力地把自己淹沒(méi)在美妙的故事里,貪婪地翻看著一本本或彩色或黑白的圖畫(huà)書(shū),感覺(jué)那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一經(jīng)入口便終生不忘。《西游記》《封神榜》《楊家將》《岳飛傳》,還有《鐵道游擊隊(duì)》《平原槍聲》……有些故事早已通過(guò)家里的廣播聽(tīng)得滾瓜爛熟,然而當(dāng)腦海中的形象和畫(huà)面中的人物對(duì)上了號(hào)后,心里感覺(jué)特別親切和痛快。翻啊看啊,恨不得把所有的故事都裝進(jìn)心里,可是書(shū)店老板坐在旁邊,老是翻看不買(mǎi)也不好意思。盡管那個(gè)年代的書(shū)非常便宜,只要一兩毛錢(qián),可口袋里真的沒(méi)有錢(qián),鋼镚也不多見(jiàn)。
等到太陽(yáng)快要落山了,我和伙伴才戀戀不舍地放下書(shū),悻悻地回家。我們走過(guò)河灘,熟悉的回家路變得漫長(zhǎng)了,雙腿竟有些疲憊,仿佛我們是從地里干活回來(lái)。不過(guò),說(shuō)起剛剛讀過(guò)的小人書(shū),交流著書(shū)里的故事和人物,還是滿(mǎn)心的歡喜。我們熱切地討論著“水滸”“三國(guó)”里的大英雄,真像“雪夜訪戴”說(shuō)的那樣,我本乘興而來(lái),盡興而歸,何必非要買(mǎi)書(shū)呢。哪怕遠(yuǎn)遠(yuǎn)看上一眼,也就心滿(mǎn)意足了。
東邊鄰居家的三姐正在參加函授(如果記憶沒(méi)錯(cuò),她學(xué)的應(yīng)該是中文系)。有一天,我在她們家發(fā)現(xiàn)了一部短篇小說(shuō)集,愛(ài)不釋手,便借了回來(lái)。一篇名叫《人到中年》的小說(shuō)看得我熱淚盈眶。其實(shí),那時(shí)我才多大啊,竟也被成年人的世界感動(dòng)得不行,很久以后我都背得出小說(shuō)里引用的那首名詩(shī):“我愿意是廢墟/在峻峭的山巖上/這靜默的毀滅/并不使我懊喪/只要我的愛(ài)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著我荒涼的額/親密地攀援上升。”
這樣的文字不同于小人書(shū),沒(méi)有美好的結(jié)局,沒(méi)有神奇的魔法,充滿(mǎn)矛盾和無(wú)奈,看得人心酸卻又充實(shí)。縱然我沒(méi)有切身經(jīng)歷,卻也有著強(qiáng)烈的真實(shí)感。這樣的文字神秘而不可避免地觸動(dòng)了我的心弦。難道,難道這就是文學(xué)嗎?
胡亂地搜尋,胡亂地閱讀,我在小小的村莊里完成了最早的文學(xué)啟蒙,記住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巴爾扎克等“大神”的名字。一扇大門(mén)緩緩向我開(kāi)啟,大門(mén)里面是另一個(gè)世界,放射出瑰麗的光芒。我神不知鬼不覺(jué)地拿起筆來(lái),記下腦海里浮現(xiàn)出的想法。我寫(xiě)下人生中的第一篇童話(huà),裝進(jìn)信封,一個(gè)人悄悄地跑到鎮(zhèn)上,投進(jìn)了郵筒。然后,我就等啊盼啊,期待收到回信。當(dāng)回信輾轉(zhuǎn)交到我手中的時(shí)候,心臟似乎都停止了跳動(dòng)。我想撕開(kāi)信封,又怕打擾了里面的消息,急匆匆找到剪刀,顫抖著剪開(kāi)信封。哦,一封退稿信!不過(guò),回信的老師還是給了我莫大的鼓勵(lì),并且隨信寄來(lái)了精美的卡片。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那卡片都像小小的翅膀,等著安在我想象力的肩頭。
小學(xué)高年級(jí)和初中前兩年是在姥姥家旁邊,一座半山腰上的學(xué)校里度過(guò)的。這里風(fēng)氣不太好,大家都不怎么愛(ài)學(xué)習(xí),我幸運(yùn)地找到一個(gè)趣味相投的同學(xué)。他也愛(ài)看書(shū),還喜歡謅幾句詩(shī)歌(他父親是我們的語(yǔ)文老師),于是我們合伙辦了張手抄報(bào),很薄很薄,只容得下我們兩個(gè)人的“作品”。小報(bào)也沒(méi)什么讀者,其實(shí)是我們不敢讓老師知道,害怕被說(shuō)成“不務(wù)正業(yè)”。我們兩個(gè)互相吹捧,滿(mǎn)足小小的虛榮心和發(fā)表欲,至于報(bào)紙叫什么名字,具體辦了幾期,我已經(jīng)忘記了。
早起晚睡地過(guò)了三年,鳳山學(xué)校被取消,想要繼續(xù)讀書(shū)的同學(xué)被安排到鎮(zhèn)中學(xué)。從家到學(xué)校有十幾里路,沒(méi)有公交車(chē),沒(méi)有家長(zhǎng)接送,我需要自己騎自行車(chē)上學(xué)、放學(xué)。那時(shí)候,鄉(xiāng)村公路上汽車(chē)還很罕見(jiàn),跑來(lái)跑去的是拖拉機(jī),噗哧噗哧,煙囪里直冒黑煙。每當(dāng)有拖拉機(jī)跑過(guò),我和同學(xué)們便猛踩腳蹬,呼嘯著追趕。
這正是我去尋找父親的公路,只不過(guò)方向相反,通往更遙遠(yuǎn)的縣城。
薛 舟 詩(shī)人、翻譯家,生于山東,現(xiàn)居北京,曾獲第八屆韓國(guó)文學(xué)翻譯獎(jiǎng),著有《不一樣的中國(guó)歷史故事》等。

